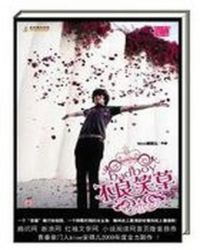花小意只是哭,不能自制的哭。
她只是一个劲地摇头再摇头。再一次推开希浩,大喊起来:“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最清楚!可是我没有办法啊。我好喜欢他,从第一次看见他开始,我就疯狂地喜欢着他了!我也好想忘记他,可是不行啊,我办不到。我从小就喜欢羽希哥哥了,我是因为他才考进这所学院的,我曾经问过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傻,这么笨,这么白痴!但没有办法,这就是爱情,爱情使得任何人,都变得没有理智可言,变得像个傻子般的卑微,卑微到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我不止是喜欢羽希哥哥这么简单,我爱他!我是深爱着他的,这份爱,太深了,深得我把自己伤得体无完肤。我是心甘情愿的!即使他拒绝我,不理睬我,躲避着我,我都不能阻止自己的心去疯狂地思念着他!我不能忘记他的神态,他的一举一动,连他轻轻皱眉的样子,他微笑的样子,我每天都要像温习功课一样复习几遍,我爱他的这种感觉,你是不会明白的!”
花小意站起身,握紧拳头,全身凝着一股气,止不住的轻微发颤着,哭腔撕裂地说:“我爱他已入骨,病入膏肓,要把他的影子从我的血液中剥离,除非把我的骨头一块又一块从血肉中剔出!”
安希浩,呆愣了,任由她在大雨中哭泣地发泄着。
而安羽希,只能隔着一条街,透过一家商店的玻璃门这样远远的凝视着她。
安羽希,渐次地抬高手,想伸手触摸她,但显得好遥远,好奢侈。能抓在手中的,除了雨滴以外,还有一片凄清的寂寥,心不那么痛了,但好像更滚烫得让他不能去呼吸了。
他要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伤口?
他要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
他的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又该怎么收拾?
能救自己的唯有自己,这是安羽希从小到大就明白了的道理。
安羽希抱紧怀中的小提琴,他看了看手心上的生命线。
突然想起外国作家考琳写的《荆棘鸟》——传说中有一种荆棘鸟,一生只唱一次,那歌声比世界上所有一切生灵的歌声都更加优美动听。从离开巢窝的那一刻起,它就在寻找荆棘树,直到如愿以偿。
然后,它把自己的身体扎进最长、最尖的刺上,在那荒蛮的枝条之间放开歌喉。在奄奄一息的深刻里,它超脱了自身的痛苦,那歌声使云雀和夜莺都黯然失色。这是一曲无比美好的歌,曲终而命竭,然而,整个世界都在静静地谛听,上帝也在苍穹中微笑。 校草之威廉古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