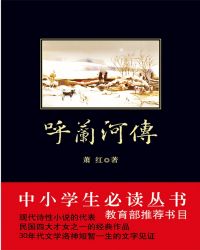何乐安觉得自己刚稍微复原那么一点点的心情,又悲催的悲剧了,可她又不能告诉谁,只好拿出一空师父送给她的《静心经》来背,一遍不行,就背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非把自己心里那点不该发芽的,但又已经发芽的种子给连根拔起,直到梦里梦见那抹鲜红,她亦能淡然处之为止。
到了去志逸伯府煮宴席那日,她为防万一,还是在太阳穴的地方点了一颗需要用菜油才能抹去的黑痣,换上惯常穿的小厮男装才去的富贵酒楼与大伙儿集合,同去伯府后门,一个类似管事的婆子将他们领进后厨,便冷着脸警告道:
“这儿是志逸伯府,不是什么低等的商贾富户,除了厨房,别的地方都不是你们可以踏足的,我在这儿也告诉你们,你们的底细我们一清二楚,若哪个敢手脚不干净,坏了宴席,便怪不得我们主子要你们整个富贵酒楼填命,到时候连你们的家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小的明白。”何乐安紧随曹掌柜他们低头弯腰应道。
进到偌大奢华的后厨,大伙儿各自在熟悉的领域里分工合作地忙碌,曹掌柜对于后厨事,素来不懂,他主要在旁监督,而何乐安便专门做一些细致的活,例如雕花与摆盘,她手脚利索又不慌乱,偶尔在大厨们需要切片或切丝的时候,也会帮忙打打杂。
一桌酒席有十二道菜,前八道菜都做好时,伯府的宴席便开了,府内的丫鬟们过来端菜,可就在他们刚做好第十道菜时,鱼贯而入的丫鬟竟变成了凶神恶煞的侍卫,二话不说便将他们所有人抓了起来,接着领他们进来的婆子气急败坏地冲进来道:
“你们!你们竟敢在菜里下药!”
“怎么可能,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了——”啪!
曹掌柜解释的话音还未落,婆子已恶狠狠地扇出一巴掌,也不知她究竟用了多大的力气,曹掌柜微胖的脸瞬间就红肿起来了,婆子道:“老爷和夫人说了,拖下去严审严惩!”
“大娘,这不可能的,定是有什么误会,我们酒楼素来干净,绝对不会——”何乐安见曹掌柜被打懵了,挣扎侍卫的钳制急声解释,可婆子直接喷了她一脸口水,恶声打断道:
“呸!若不是你们手脚不干净,贵客们怎会吃了你们的菜后,便上吐下泻不止!来的时候已一字一句警告过你们,一人犯错,全部人同罪,如此你们竟也敢给婆子闹此等幺蛾子,都拖出去好好审!”
何乐安的挣扎换来侍卫更加粗鲁的钳制,熊叔他们都是小老百姓,从没有遇到过这种阵仗,基本已经吓傻了,等反应过来时,人已经被压在长凳上了,那板子一下下打下来,只剩下嘶声的喊叫,曹掌柜的解释被痛呼淹没,婆子质问道:
“说!到底是谁下的药!”
“我知道我们都没有下药!谁也不要认!认了就更洗不清这份罪了!”即使屁股的痛意叫脸色一下子就变得惨白,叫面容扭曲,何乐安也死死地咬着牙拼尽全力吼道。
“对!我们没有做过!”曹掌柜被她的理智惊了惊,也死扛着吼道,“没有做过的事,你们就是把我们打死了,我们也不会认的!”
“好呀你们,还能嘴硬是吧,给我用力打!”婆子似是被何乐安和曹掌柜气着了,冷笑着吩咐道,“尤其是这两个,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便打死了!”
噬骨的疼意,一点一点地从屁股蔓延至全身,不过七八下,何乐安纤瘦的身子就熬不住了,可她依然死死地咬住嘴唇,不叫自己将痛苦泄露出来,也不叫意识更快地流失,冷汗与唇角的血,在地上砸开一朵朵清脆的水花……
何乐安想起上一世无恶不作的自己,被万蛇啃咬,被仗责,被掌掴,被轮暴,甚至被反复摁进冰湖,种种折磨之下仍然活至三十岁,这一世无善不为,却要死在这样的误会里,想到出门前还叮嘱自己小心的何老太太,鼻子一酸,眼眶就凝聚出一片片雾气……
耳边痛苦的惨叫已渐渐低下去,忽然水声哗啦啦地泼了过来,皮开肉绽的屁股顿时如被腐蚀般钻心刺骨地痛起来,身旁响起一阵比一阵还高的撕心裂肺的喊叫!
几乎要失去意识的何乐安知道,泼下来的是浓盐水,如此猛烈的刺激,叫咬着唇的她,也难以忍受地哀叫出声,“呜——!!”泪一滴滴地滑落,却见眼角余光闪过一抹熟悉的鲜红,而这时,便听不太熟悉,又好像在哪儿听过的男声命令道:
“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