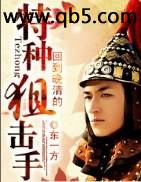“够了!”
李璟一声怒喝,殿中的众人神色俱都变得不能淡然,原本涌到嘴边的话语也不敢出口,或是将头垂得更低,或是略有不满的望向殿中的正在慷慨陈辞的大臣。
“除了开战,卿等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李璟的冷笑道。
他何尝不想直接开战,派遣大军去剿灭那忘恩负义的留从效,但是南唐目前的国力已经不允许他这样做了,福州的那一场大败直接将南唐拖进了战争漩涡,长达一年的围攻,无论是人力还是钱粮都消耗巨大,南唐已经没有能力两线作战了。
殿中的这些人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又不用他们去打仗,当然就乐得在这殿中慷慨激昂地痛骂留从效,并要求立即出兵讨伐。
在座的多是只会诗词歌赋却不善处理政务的人,这会儿更不知该要说什么去为他们的陛下排忧解难了。而以往这种时候,都是冯延巳等朝廷重臣出声化解陛下的诘问。但今天冯延巳告病在家,只好由太傅宋齐丘出面了。
感受到众人目光,宋齐丘心中也是暗恨,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留从效不过是王继勋手下一匹夫,窃居泉州已是非分,如今更是私自发兵攻打漳州,自称泉、漳二州留后,如此忘恩负义之人,其势绝难长久!陛下若是出兵讨伐,天下必定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宋齐丘越说越小声,因为他的陛下正死死的盯着他,嘴角挂着一抹冷笑。
见状,宋齐丘忙不迭地住嘴不敢再多说话。至于其他人,神态则更加拘谨。
“先帝若在,留从效安敢如此放肆!”
李璟蓦地长叹一声,眉目之间满是追忆缅怀。
听到这话后,殿中垂首的众人神态俱都略有异变。而其中宋齐丘的两手更是蓦地攥起,视线陡然厉色几分。
这是什么意思?
是在说留从效放肆还是在说我们这些做大臣的放肆?
李璟的意思很明显,大臣还是那些大臣,只是换了个皇帝而已,为什么就没有了原来的能力呢?是在欺负我这个新登基的皇帝治不了你们?
宋齐丘立即避席而起,深拜道:“臣等不能攘忧于外,以致陛下深忧至此,实在是臣等之过!”
其他几名朝廷重臣见状,也都纷纷避席请罪,几名将领更是声色俱厉的踊跃请战,发誓要将留从效的贼首奉于君前。
李璟眼见此状,只是冷笑一声,继而便不乏感慨道:“往年卿等不过是乡中一文人,苟全性命于乱世。杨氏失德,自弃其众。徐氏骄横,自取其咎。先帝乘势而起,披襟斩棘数十载,惨淡经营,朕方能坐享天下,诚是天命在我,但也多赖众卿之力。”
“先帝与众卿,相识于微末,共进此时,社稷分享,寄望悠远。但天不遂人愿,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江南虽定,吴越未平。我大唐(这里指南唐)北有石晋虎视眈眈,东有吴越枕戈待旦,南有刘汉引而不发,西有荆楚厉兵秣马,这些俱是心头尖刃,稍有懈怠,诸贼即要厉行,剜我血肉,割我疆土!王闽虽灭未平,实乃心腹大患,我是旦夕忧虑,唯恐有失。但众卿扣心自问,是否此心同我?”
“奸贼李仁达,不忠不义之辈,仍能固守福州,却我军于城门之外!陈觉、冯延鲁之徒,俱负才名,如今竟大败于吴越之手,究竟是他们名不符实,才不堪用?还是气骄志堕,狂妄自大?诸卿谁能道我?”
讲到这里,李璟已是厉态毕露,额角甚至都有青筋露出,可见心情之恶劣。实在是太窝火了,登基之前,他的人生可谓是一帆风顺,身为父亲的长子,父亲的名位迟早都是他的,他既不用忧心柴米油盐,又不用应付阴谋诡计,可以整天游山玩水,吟诗作画。
等到父亲建国称帝,他更是一跃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齐王,后来更被册封为皇太子。他的身边从来不缺乏阿谀奉承之人,自己想要什么,只要一句话,身边的人立即就会帮自己办妥。
但是登基之后,除了一开始攻破了虔州,成功抓拿妖贼张遇贤外,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心的。
先是自己好心写信给王延政,劝他们不要兄弟相残,结果好心没好报,王延政回信大骂自己父子篡夺了杨氏的天下,罪该万死!
自己为了维护大国尊严,愤而发兵,讨伐王延政。历时近一年,终于灭亡闽国。
怎料闽国虽灭,但当地将领的反抗不断,先是李仁达据守福州,勾结吴越,让自己损兵折将。接着这留从效更是过分...... 糊涂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