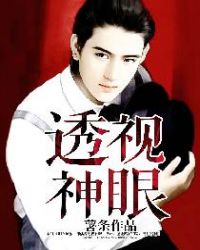再见到临亦风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这种家庭出生的孩子自小就陪父母周旋于各种宴会。觥筹交错间的买卖轻易几分真几分假,谁都不会在意。
陆昔临和我交好,这是我俩从幼孩时就培养起来的革命友谊。
西藏之行我只说与他听了,并相信他不会告知旁人。果然,十几年的交情不是盖的。
在酒会上,我异样的表情成功引起了他的注意。
“维安,他就是那人?”陆昔临的眼光像啐了毒的利刃,迫近咽喉,让我无法遁形。
我只说过在西藏遇到了一个惊艳的男人,再无二话,可他却有本事洞悉得如此透彻,想来段位不低。
“没想到,世界真小呵......”世伯家的公子,圈内人,兜兜转转,从藏区的天空到了G市的土地,可不是真小么!
再然后,我们结婚了。
可笑,我一个初入大学的新生在婚姻状况那一栏居然得填“已婚”。
但,对于这一结果,我接受得很平静——平静到让爸妈害怕。
“安安,爸爸妈妈这样做也是为你好。亦风那孩子是真不错,虽然大学刚毕业,但已经成功参与到“水寒实业”的运作中,初露锋芒。而且世伯和阿姨又那么喜欢你,你一定会幸福的。”
他们苦口婆心的说辞在我看来很敷衍。其实只消他们说我们家需要临家的注资才能度过眼前的债务危机,我没有拒绝的立场。
但,我内心无比清楚,我之所以会答应是因为一个不被允许的理由——我爱上了临亦风,这个意外且荒唐出现在我生命中的男人。
我们俩的第一次谈话,开诚布公。
“我喜欢你的身体。”比起一个月前,他收敛了许多,没有了呛人的烟草味道,眸子也比天上的星子亮。
西藏的那个夜晚,他眼里有雾,浓重得化不开,几欲将人吞噬。
我想,那一晚的自己很荣幸成为了他的陪葬品,带着孤注一掷的勇气和破釜沉舟的决心,任由他操纵生死。
而今晚,他是陌生的。扑面而来的强势将我生生湮灭。在他面前,我的骄傲自尊全数失守。
“真巧,我也是。”为了维护最后一丝体面,我用近乎傲慢的语气回应他,将再见到他的欣喜掐死在无人的角落。
只有在身体的忘情契合中,我才敢承认,我爱他,我的丈夫。
婚后的生活很平淡,毕竟我还是个大学生,排除“配偶栏”会比同龄人多出一个人名外,其他方面与旁人无异。
周一到周五,我选满了所有的课,于是,爸妈见不到我,公婆见不到我,他也见不到我。
但,似乎,不同于四个父母,他并没有刻意见我的欲望。
每周六回娘家,每周日回婆家,这是我见到他的唯二机会。
友人们歆羡我有“体贴帅气”的男友接我回去过周末,可她们哪里知道,如果他不爱我,我宁愿两人老死不相往来。
人前,他是孝顺的儿子、合格的女婿和称职的丈夫。他们家的家庭氛围很好,非名门不得出。公婆也真如女儿般待我,不亚于我的亲生父母。
大人们把他的体贴照顾看在眼里,认为我俩是天作之合,以至于我常常产生假象,没准他是真的如此。
可,理智又总会在我飘飘然忘乎所以时,给我一记闷锤——你们俩怎么可能有“爱”?
是呵!
我们只有对彼此身体的迷恋。尽管我知道他是我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男人,而我却不知是他的第几个女人,更遑论最后一个了。
由于诸多现实原因,两方家长决定等我大学毕业后再举办婚礼。我以为,我等不到那一天。
如果没有那一次变故,也许我们会维持这种讽刺的关系直到他单向终止为止。
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我再一次去到了西藏。
我用沾满欲念的、自私的手拂过沉重的经桶,我在风转经、水转经的圣洁之处许下宏远。
神明在上,我用一辈子的运势换他一次的怜惜。一次之后,我心甘皈依。
他找到我时,兵荒马乱。
“藏独”分子的猖獗已经让我失去了思考的理智。人群中瞥见他的那一刻,我几欲昏厥过去。
他怎么在这里?他会不会有危险?如果他受伤了,我该怎么办?
万幸,他没事。在我被劫持打晕之前,我竟看到了他惊愕的脸。
是在为我担心,好么?求你......
等我再次醒来后,已经回到了G市。
听说,我昏迷了三天三夜;听说,两家人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听说,他衣带不解地守候,寸步不离。
所以,我的愿望灵验了?
至此,我从学校搬了出来,住进了他的公寓。
公婆说,日后结婚会为我们准备新房。我不甚在意地笑笑,如果,有那一天的话......
他开始对我好,一如友人们的恋人那样,我感觉得到。
是不是今日得到的越多,以后就会越痛?如果真是那样,我甘之如饴。
我怀着诚惶诚恐的念头过活,每一个二十四小时,度日如年。
可是,度日如年怎么够?也许,死在他怀里我才会安心。
我们像每一对正常的情侣,白天热恋着,晚上热爱着。他若不忙,便会陪我上课;我若有空,就去他的办公室自习。
这样的日子维持了近半个月,他要出国继续他的课程和事业。
“和我一起过去?”意乱情迷过后,他的声音慵懒,带着致命的诱惑。
我差一点就以为这是爱到浓时的分不离了,毕竟,他的占有欲从未表现得如此明显过。
可,如若不是因为爱呢?我害怕被他弃之如履。
于是,我拒绝了,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第二天,他就走了,我也搬回了学校。
我们没有任何联系,他所有的近况我从公婆父母那里得知,还得装出一副万事如常的样子。
好累,真的,好累...... 头条隐婚枕上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