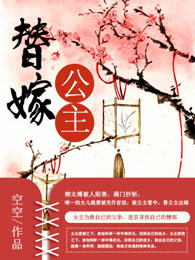曾停将长勺搁下。
不置一言。
烛火晃动,墙上映着几个人的剪影。
这种突然卷进的穿堂风,掀起了一阵战栗。
曾停的两撇小胡子正在上下移动着。
但他没有说出任何话来。
唇瓣儿嚅动,几次欲开口又咽回了他那鼓鼓的肚子里。
“叶大人,有时候耳听为虚眼见也为虚。”
想了良久,他从布满黄渍的牙齿缝里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曾老板是个妙人儿。”
叶惊阑不会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尤其是对曾停这种将“精明”写在了脸上的人。
“贼丫头,邀你到茶坊,是为了告诉你……舍得,有舍才有得。”曾停垂眸,他又从袖袋里拿出了一个素色荷包,与云岫赠予蒙络的那个很像。
云岫知晓,这是花钿亲手做成的,一共六个。
“看看吧,花钿姑娘曾告诉我,若是劝不住你,就将这个交予你。”曾停叹口气,将那个密密缝了口的素色荷包放到了云岫的掌心,“望你慎思慎行。”
平日里总是笑脸迎人的曾停在此时的表情极为严肃。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一本正经。
“曾老板你这是为了什么?”云岫攥紧了那一个荷包。
指腹在荷包面上摩挲着。
曾停往椅子上一靠,那两撇上蹿下跳的小胡子在这一瞬间失了灵动。
“我是不会害花钿姑娘的。”
“但你会害我。”云岫又执起小剪子剪去了一小截灯芯,摇曳的火光在剪子上跳动两下,归于平寂。
穿堂风来得有些急了。
吹得曾停的袍子飘飞。
他正了正脑袋上的帽子。
“不会。”他咯出了一口带血丝的唾沫,仿佛那唾沫里面暗藏着他的精气,甫一落地,他就失了魂儿。
“我该如何信你?”
她捏着陶杯,目光落在杯口上残留的一滴晶莹上。
许是曾停洗了杯子后忘了沥干吧。
曾停听了这话,沉默半晌。
“信与不信全在姑娘一念之间。”话音一落,他拂袖离去。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
“我……终是信你的。”
云岫拾起他落在木椅上的一张泛黄的纸,尽管这张纸看上去饱经沧桑,但没有卷起一点毛边。
是曾停有意或是无意?
云岫不得而知。
她将纸叠起,同素色荷包一起放入袖袋中。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是无论成败都要去坚持的。
叶惊阑只瞧一眼,却不问。
“雪球儿。”云岫抱起那只如高山之雪簇成团的白猫,她触了触雪球儿的耳朵,微凉的触感在夏季异常舒坦,雪球儿的耳朵抖抖。
名作琥珀的黑猫瞪着双眼,目送他们离去。
它对同伴的离开没有一丝一毫的不舍,甚至还满足地叫唤了两声。
它在大堂里来回踱步。
……
出了曾停的院子。
只听得“哗啦”一声。
虞青莞泼出了盆中之水。
她一抹额上细汗,这个天儿闷热难耐,一动即是牵扯全身。
矮篱笆上攀着的是与曾停院子里截然不同的植物——牵牛花。
“叶……叶公子。”虞青莞仍是怯怯地唤着,“云姑娘。”
她手中的盆儿跌落在地,她赶忙跨出一小步,蹲身捡起。
这种两只脚一前一后,压着裙摆蹲下身的姿势,正是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们习以为常的。
“见笑了。”她将手背到身后,拉扯了一下衣裙,担心着衣裙上有皱褶,会落入他们的眼中成为笑话。
站在高枝上俯瞰众生的人陡然没入尘埃时,会不自觉地在意起自己的仪态是否跌了身份。
实际上,这只是强烈的自尊心在作祟。
没有人会在意,你是否曾立在高枝上以婉转的歌喉歌颂这个人世间,用鄙夷的眼光看向路过的乞儿,更没有人在意你如今的生活是否落魄,是否失了体面。
因为,大多数人只能看见三寸之内的自己。
虞青莞上前一步拉开了小院的矮门。
“既是路过,不如喝一杯淡茶再走吧。”
“也好,刚巧说过渴了,便能讨到一杯茶水喝,实属幸事。”
叶惊阑没有拒绝虞青莞的好意。
月色朦胧。
偶过的风吹得牵牛花的枝条儿发颤,枝条上挑着的花朵翩翩而动。
院子里的石桌前,三人捧着茶水,静默不语。
雪球儿趴在云岫的膝上,打着浅浅的呼噜。
圆滚滚的曾停脚下生风,他是一刻也不愿歇着的人。
“曾老板的生意当真是蒸蒸日上。”叶惊阑呷一口茶,感叹道。
虞青莞沉吟片刻,说道:“承蒙曾老板收留,让我在锦衣巷安了家,不然……早就曝尸荒野。”
她似回想起了沉重不堪的往事,神色不豫。
紧锁的眉头像是一个解不开的结。
“他是一个好人,很好的人。”虞青莞在“好人”二字上咬重了音,她的嗓音本就如大小玉珠滚落,温润而明亮,“叶公子……我知你是此次查案的钦差,我也知我无权要求你放过谁,可我依旧想说,曾停,是无辜的。”
晚风很凉。
自云岫的指缝间缠绕过后消散。
“我是罪臣之女,本不该再以原名出现在这世上……只有曾停不计后果予我一个遮蔽风雨之所。”虞青莞提及陈年旧事时眼底的痛楚是无法伪装出来的。
她的嘴角一酸,无法再维持那抹淡笑。
缄口不言才是当下最适宜的做法。
她看向叶惊阑时,眼里荡漾着水光。
“我会权衡。”叶惊阑面无表情地答着。
诉苦的人多了去了,难不成每一个诉求他都得听?
官场上的老油子的共同爱好便是打太极。
这年头不会打太极,不会把话兜圆了的官,是保不住头上那顶乌纱帽的。
叶惊阑自然不属于保不住之流。
云岫的杯子空了。
虞青莞见机替她满上了。
她道了一声谢,抬眸看定虞青莞,“虞姑娘这次可没有凭借自己的直觉来定论。”
虞青莞挤出一个平素在台子上面对众人时的笑,“我的直觉告诉我,叶公子值得相信。”
“那薛将军呢?”云岫挑起了话茬儿,那天夜里她本是想将虞青莞问个一清二楚,没想到被她一句“全凭云姑娘定夺”给糊弄过去了。
薛漓沨这根横亘在心间的刺,可不是想拔出就能拔出的。
果不其然,在听见他的名字之后,虞青莞再一次沉默了。
她长长的睫毛投下一片阴翳。
在某一瞬轻轻一颤,泫然泪下。
可是这泪珠儿仅是淌了那么几串,虞青莞很快便打住了。
她捏着手绢拭去眼角残余的晶莹,扬起一个笑容,“薛将军哪有时间理会一个平头百姓。”
“你不是一般人。”
虞青莞笑至花枝乱颤,眼尾弯出了很明显的弧度,“那我是什么人?薛将军的故人?本该死在火场之中的故人?”
“可我问的是你相信与否,而非你们之间。”
虞青莞上扬的唇角僵在了某个点上,她一听到薛漓沨的名儿就乱了心神,哪管云岫问的是什么。
思来想去,她做出回答:“不相信。”
“嗯……”
想不到云岫没有追着答案往深处挖。
虞青莞试探着说道:“云姑娘,当时在巷子里……”
“多谢虞姑娘的盛情款待,夜深了,便不叨扰了。”云岫起身作礼。
她并不想回答虞青莞的相关问题。
她还没能破了整个局,不能落了有心人的口实。
叶惊阑会意,也抱拳一礼,“滴水之恩,来日定报。”
虞青莞仰起头,望望已是漆黑一片的天幕,拉扯着唇角,怎么会笑不出了……
而抱着白猫的云岫和叶惊阑走在冷清的街上。
那一户过生辰的人家也熄了烛火。
“叶大人,你觉着虞青莞的用意是什么?”云岫的手指不住地拨着怀中雪球儿的耳朵。
叶惊阑不假思索地答:“转移目标。”
他们想到一处去了。
越是强调的东西,也许越是不在乎。
反倒是一句带过的,才更是有用。
但摸不准虞青莞想要转移的目标是真是假,此时只能凭借揣测。
锦衣巷小住的这几日,想来不会太难熬。
曾停让步妥协了,虞青莞投诚了,锦衣巷里的奇怪黑影只要不主动找上门来,一切的一切看上去都是正常的。
“失了几日的消息,对你来说,不大有利。”云岫轻声说着,要是只为了将养她的身子,大可不必。
叶惊阑睨她一眼,“请云姑娘大胆猜测一下,若是我不按照那人的要求在这里多待几日,怎能给他留出时间来?”
云岫轻笑一声,“原来是这样。”
“不然……”他滞住脚步,稍稍俯身,在她耳边说着,“你以为是为了你这副身子骨吗?”
见云岫耳根子微红,他清了清喉咙,“有的人学会了自作多情,就爱胡思乱想。”
“有的人学会了揣摩别人心思,就添上了主观臆断。”
被反咬一口的叶惊阑眯着眼。
云岫瞪着他,冷笑着说:“被戳中心事的人,就爱暗自伤神。”
“那我怎没见你伤神?”
“因为这本不是我的心事。”
云岫坦然的回答使得叶惊阑不得不感慨脸皮厚的重要性。
脸皮一旦厚实起来,便能从容应对很多事儿。
脸皮厚的云岫与脸皮更厚的叶惊阑在锦衣巷里赖了好几日。
某日,吃饱喝足的云岫与叶惊阑遛弯。
“一不小心”碰倒了长木桌。
血色馒头沾了灰。
蛇虫鼠蚁和各类奇怪的东西混作一团,一时间挑拣不清。
扫地人的黑斗篷不翼而飞,从此长街一望到头,空无一人。
再一日,茶坊失窃。
丢了一只名叫“琥珀”的黑猫。
当天夜里,曾停的茶坊里热闹非凡,瓶瓶罐罐碎裂声,桌椅板凳掀倒声,曾停气得站在院中叉腰,破口大骂。
没有杀伤力的话语在云岫听来就是挠痒痒,这种程度还解不了她的痒。
叶惊阑却觉得琥珀应当和雪球儿做个伴,不用再回到茶坊里。
又过一日,虞青莞的竹篱笆上的牵牛花剩了几根光秃秃的藤。
两个小偷不止带走了开得正好的小喇叭,更薅光了藤蔓上的叶子。
当天夜里,虞青莞收到了一个花环,正是她种的牵牛花编成的。
她从老柳树下的井里打回的水,连着木桶一齐不翼而飞。
披着黑斗篷的某人端了个木盆在街边泡脚,极为放松地赞道:“水源好,自然什么都好。”
那里的水果然是沙城最干净的。
另一人坐在小板凳上看着月亮每一日比前一日更圆。
“薛漓沨本就见不惯你,你还不收敛些。”她头也不偏地说。
泡脚的人饶有兴味地打量着她的侧脸,“不过是用他喝的水泡个脚罢了。”
“奢靡之风。”
当然,没人听到他们的对话。
直到曾停送来的药材熬不出浓醇的药汤,便是要出锦衣巷的那一日。
曾停早早地到了云岫的小屋外。
手持金算盘,忍受着乱走的黄沙贴面亲吻。
“日上三竿!”他怒道。
“还未起!”他的声调抬高,中气十足。
门内没有任何动静。
门前放着一篮子鲜果儿,是虞青莞来过了。
虽然不合礼数,他还是决定推开这扇门。
金算盘碰上木门,虚掩的门猛地打开。
他站在门槛前张望,里面空空荡荡,像从未住过人一般。
他一愣神,这两人先行出了锦衣巷?不应该啊……
曾停只觉内心焦躁不安,他们不会寻到了如何出去吧?那为何要等到今日?
满腹的疑问凝成一团,蕴结在一块儿,堵得曾停一口气快要接不上来,闷在胸腔里很是不痛快。
有人曾说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越想越亏。
吹着两撇小胡子的曾停像极了那种心态,他抓了抓帽子,往巷子外走。
而那两人一大早就回到了沧陵县。
出乎云岫意料的是……
本该是她的房间里多出了一个人。
一个瞎子。
暮涯一手端着茶碗,一手用茶碗盖别开茶叶,瑶鼻轻动,缓缓地说:“鹿贞,今日的茶水缺了点火候。”
“我这就去给小姐换。”鹿贞立即应声。
“不用了,就这样,有时带有遗憾才更美。”暮涯一如她以往那般温柔。
“我也喜欢这种遗憾的美。”云岫大剌剌地坐下,不客气地端起她准备的第二碗茶水。 倘若对云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