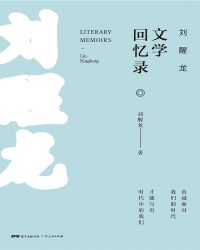第57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57节·
长篇小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成熟与不成熟反差最大的文体。即使20世纪90年代那些堪称典范的样板之作,也有显而易见的诸多问题。相比而言,这类粗疏的缺憾反映在长篇小说中,就没有中短篇小说那么刺眼了。有时候,还会让人觉得粗疏只是长篇小说中不成问题的问题,是长篇小说的某种组成部分。因为粗疏所相伴的一定是宏大,如同海啸只会发生在大海里。《圣天门口》出版之后,我有些后悔。虽然经历了文化快餐时代不可思议的六年闭关,但我还是觉得出手快了,假如能再放上一两年,然后再用一两年来修改,如此花上十年时间,那些让我后悔的地方,肯定就不会有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仍然信奉,长篇小说用不着写得太精致。在一些重大纪年与事件的连接处的粗疏,是长篇小说必不可少的艺术特点。
长篇小说结构本来就是见仁见智,有喜欢倒叙插叙地将历史与现实扭曲在一起变成语言迷宫的,有喜欢用“我奶奶、我爷爷”等全知全觉第四人称的,还有娓娓道来喜欢追忆似水年华的,然而,这些都写不下我想写的。汉民族从创世纪开始的历史,通过说书形成一种古往今来的氛围,这种氛围又将天门口时下的人事引入历史当中。如果将那种常见的为追求普通阅读效果的戏剧化因素,用在这样一部作品,就会因为过于刻意而变得见小的。
对方言的运用,我只选择相比普通话规范的用语有所超越的那些。比如相对“知道”的“晓得”,相对“聊天”的“挖古”等等。作为母语的汉语,文学界应该有种危机感,现在来看,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日益确定,汉语热在全世界持续升温,所谓语言的“全球化”问题也变得不那么突出了,反而是汉语自身的过分口语化,加上语声含糊、组词难看的“京腔”,使得我们的母语越来越烂。在我所主编的《芳草》文学杂志的扉页上,我有感而发,撰写了两句话:汉语神韵,华文风骨。的确,我喜欢听台北人讲的“国语”,感觉上那种优雅古典的言说方式,才是我们的正统母语。真正的方言,往往是经历了长久的历史选择后存留下来的母语精髓。时下的许多被称为方言的,其实是俗语。多半是汉语在白话化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垃圾物,如果不明就里将其塞进文学作品中,会有损文学品位。
文学的存世与种庄稼的原理一样,试来试去,还是“绿色食品”最受欢迎。在信息时代,不要以为一个人掌握了互联网就掌握了一切。互联网只是个工具,使用不当可能干的是错事。实际上,生活中很多流传的都是假象,是以讹传讹的东西,很多问题一定要现场解决。曾经听北京的朋友讲,南水北调的水到北京后变成“浑水”了,他家自来水管确实流过“浑水”。2015年夏天,参加“南水北调人文行走”活动,听专家解释,这是因为北方长期用地下水,水管里形成了一层水垢,丹江口水库的水是弱碱性,流到北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后,将水管里的弱酸性水垢溶解了,变成浑水从水龙头里流出来。等到自来水管里的水垢完全溶解后,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所以,我相信,长篇小说中的缺欠是不可避免的,是为了衬托其不可替代的独一无二性质。在长河一样的流水中,漂过一些枯枝败叶,臭鱼烂虾,也是其势力范围之内能有效控制的现象。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