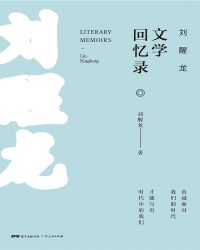第134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134节·
按照习惯的说法,里程碑是从零公里开始计算,每一公里就标示一个。1998年夏天第一次到西藏,在日喀则城外的公路边见到一块里程碑,上面铭刻的数字表明,从上海到此地共有3128公里。也就是说,沿途共有3128个里程碑。作家将一部作品写完了,也就等于竖起一个里程碑,成为这个阶段的标志物。用里程碑作为形容词很有趣,一边写作,一边前进,来的路可以摸得着,回去的路能够看得见。若是论起作用来,日常生活中对里程碑的理解可能夸大了一些,好像只适合对应某些大事件。实际应用起来,并没有那么夸张。比如日历,人做没做什么,这一天都会翻过去。里程碑的意义在于,告诉一个人他在这条路上走过多远了,如果停下来不动了,就不会再有里程碑出现。
后来,又有两次机会到日喀则,在我心里,还记得那块竖在一棵大柳树下的里程碑,不过我没有痴迷到非要找到那棵大柳树,看看那块里程碑,照相留念。这种发自内心的纪念,提醒了我,作家也需要找机会回顾一下,看看自己用文字创造的那个里程碑,是不是还在原来的地方,有没有显出新的意味?
短篇小说抓住一个灵感,抓住一个人物,抓住一个细节就可以。长篇不行,得有层出不穷的灵感,一批成熟的人物,一批鲜活的细节。在厚度,广度,深度上必须有更充分的东西,仅仅靠幽默,仅仅靠俏皮,仅仅靠抒情,都是不够的,必须是这几个方面的成熟结合和建构,才能写出一部出色的长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写作,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算心里琢磨的那些年月,仅仅从有了写作欲望到开始动手写,正常跨度和时间至少在五年以上。如此看来,在文学这条路上,一个个短篇小说的完成更像是一个个里程碑,长篇小说应当是长途跋涉过程中难得一见的车站。
一个背着背包的独行客,终归要到达某个车站,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依赖日积月累,也是为了能在学养上达成阶段性成果,或者说是理想中的目的地。在2000年以后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圣天门口》《蟠虺》《黄冈秘卷》中,可以言说的东西很多,从抒情的角度来判断,《天行者》要浪漫一些。是对自己青春时代的和盘托出。那些在心里放了很长时间的东西,终于写出来了,这才发现,一个人的心灵之痛,也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痛,一个人的精神荣耀,更是一个民族的光明未来。从难度来说,当然是《圣天门口》,具体来看,这样的写作俨然是自己几十年人文积蓄的集中爆发,往深处看,也是一个时代人文元素重新聚合。从个人心理情绪,到身体机能,再到生活环境,各方面不谋而合地共同做了充沛饱满准备。正确的写作必须仰仗多方面的保证,保证越靠谱,走得就越来越远,发掘越来越广。轮到写《蟠虺》,求实求真的心态在起着主导作用。二十年时光,就这样在《天行者》《圣天门口》《蟠虺》之间交替流逝。如此一场漫长的旅行,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到最后,也是最高境界,还是刀枪不入、水火不避和宠辱不惊的超然。新作《黄冈秘卷》似乎在往这方面靠拢了。
人在某一行当中做久了,就会像俗话所说的,变成精怪了!
文学这一行,精明的人反而成不了精,笨到不懂得回头的人想不成精也难。
小时候去大山中砍柴,路过的那棵大樟树就是最好的例证。大樟树孤零零巨大的样子,几十里不见第二棵相同的,说它是超然肯定没错。仔细看来,仔细想来,从一颗种子落地生根开始,它就没有挪动地方。春夏秋冬四季在变,东西南北风向在变,冰火旱涝在变,它那绿色叶片一直不变。由此来看,所谓超然,也可以就是自然。
文学创作也是如此,超然本性就是自然,自然到头定是超然。1984年发表的小说处女作《黑蝴蝶,黑蝴蝶……》中,通过作品中人说,机遇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1994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开头就讲了一个分明是牧师犯错,想惩罚牧师的上帝,却失手用雷电劈头盖脸地打中纯洁无辜的修女的小故事。2005年出版的《圣天门口》和2014年出版的《蟠虺》,三十年中,每部作品差不多都是相隔十年,一方面是个体文学人生的不断积累,另一方面是自己对自己的醍醐灌顶。
可以说,小说是写给自己的敕书!
还可以说,小说是写给自己的诏书!
与诗歌和散文不同,诗歌和散文可以将自身彻底虚化,全部文字也跟着虚化得与写作主体相去甚远。也与戏剧和电影不同,戏剧和电影要求有强烈的戏剧性,处处必不可少的表演性让创作主体变成了局外人。这些在经典小说中是无法做到的,经典小说的各种要素,从人性到人文,从家长里短中的贤良方正,到历史命运中的春秋大义,稍有做作就会被人看出破绽,贻笑大方。这种全方位的文学性求证,迫使作者本人,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本真泄露在小说文本中。在作品中,一个坏人如何慢慢地变得不那么坏,一个好人如何做出不那么好的事,还有如何让读者读得泪流满面,如何让读者读过后掩卷长思,这些都需要作家本人通过自己的信仰,自己的理想,自身的价值判断,自身的心理健康程度,形成一套只能属于个人的极具个性的完整的经验和理论体系,只有这种体系,才能保证个人写作的与众不同。偏偏就是这样的个性,这样的与众不同,在造就一部作品的同时,也将作品背后的人心与人品暴露无遗。
在别人的教科书里,成语二桃杀三士是在传播一种邪恶的权术与阴谋。我从这本书里,读到的是三位勇士身上顶天立地的浩然正气。在别人的教科书里,“不可半渡击之”是在嘲讽食古不化的愚蠢腐笨。我从这本书里,读出了人对信义忠良的神圣捍卫,宁可置一时成败于不顾,也不可以因苟且而小人。这些想法,也是我在《圣天门口》中完成并读出来的。
在心里和文章里,读得最多,使用最多的有三句话。第一句出自《圣天门口》:用人的眼光去看,满世界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满世界全是畜生。第二句也是出自《圣天门口》,但这话来自日常生活中的口口相传:如果被一只疯狗咬了,难道还要反咬它一口吗?第三句是《蟠虺》中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
小说还没有问世,自己就已经相信了。
只有自己相信,才有可能让别人相信。
换言之,小说的本意是让别人读的,让别人读后照着去感怀和思索的。
本来像是诏书一样的文字,真正对照检验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写作者,以及作为第一读者的作家本人。就算当成敕书,也是通过领悟文学,回过头来点化自己。李清照用诗感叹,山盟虽在,锦书难托。作家与自我之间,也有山盟海誓之约。任何一部作品,都是作家写给自己的锦书,相送相托,都在方寸内里。除非人格分裂,才会无法托寄。相比诏书和敕书,小说更适合做自己写给自己的锦书。
所以,闲来无事,我会不时地翻一翻自己的旧作,与自己创作的那些人物隔空相望。在本质上,这种隔空相望,正是与另一个自己相爱相杀,互为表里。
2018年10月24日定稿于斯泰苑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