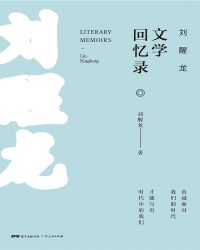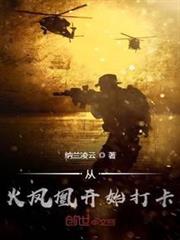第105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刘醒龙文学回忆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105节·
《青年文学》出版两百期时,我将柜子上的两本《青年文学》取来叠在一起,又找来一根尺子量了量它的厚度,刚好9毫米。然后又迟疑地算出200期就该有900毫米厚。照中国人的身高来比画,也就是两条腿那么高。想想也蛮好,两条腿长成了,就可以自己满世界去奔跑。在成长的规律中,能跑能走才能有自由。
自由多好!时常翻看这熟悉的杂志,其中滋味似乎越来越浓。
从很早开始,我就喜欢《青年文学》,有了自己认为不错的小说,首先便往那儿寄。其中一篇被那时还在《青年文学》的一位女作家署名退回,并告知她认为不错,上面没通过。1991年,我去北京参加青创会。一下火车大家都去卖彩券的地方试运气,结果别人都得到袜子之类的奖品,唯有我不见丁点回报,我当即说了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北京不欢迎我。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整个北京,除了在新闻联播中天天出现一些人物以外,只认识一个李师东。开会期间,曾同他人一道被困在二十一世纪饭店的电梯里出不去。大家怎么弄也弄不开。我待在角落里,心里本来想着,这地方轮不到自己上场。眼看着别人都泄了气,齐刷刷地站在各自的位置上发呆,我才忍不住想试试,毕竟自己是在工厂干过十年的车工师傅。按照修理工在电梯门边的提示,我伸手在一个地方按了一下,电梯门便就开了。大家往外涌时,一位很明媚的女作家还朝我说了声谢谢。
在北京时,专门到饭店来看我的,只有《青年文学》的李师东。
实际上,我和他认识也只有两个月时间,3月份,他从北京到黄州同我讨论那部名为《威风凛凛》的中篇,因为这是他们有史以来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的最长的一部作品,编辑部才特别重视。李师东当时穿着一身油兮兮的牛仔服,据他自己说,下车后找到第一个人问路,那人竟然知道我。这一点让我很惊讶,虽然我一直相信自己与文学有缘。那时,我从山里回到黄州不久,全黄州城认识我的人不到20个,能够在这种嘈杂小城的最嘈杂的车站门口,遇上认识我的人,不是奇遇也是奇遇了。李师东全然不是京城名刊名编的样子,他后来要我好好练练普通话,其实他自己也说得不是十全十美。不过我很喜欢他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的样子,这一点我们很相像。单就作品构架来说,《威风凛凛》的小说情节,我最满意。我们在北京开会时,这部作品正被他们送去印刷厂喂油墨。李师东来看我时,还说它出来后会有影响的。
对我来说,李师东以及后来正式代表编辑部的黄宾堂的出现,其重要性肯定大于先来接见我们的几位首长。
那时尚且没有策划一说,但《青年文学》为我所做的就是策划。在《威风凛凛》之后,他们要我连续给他们来两部中篇,接下来就在北京召开作品讨论会。
我写了《村支书》。
我又写了《凤凰琴》。
迄今为止,我的小说名被编辑改过三次。第一次就是《村支书》,原先叫《水闸》。第二次是《中国作家》上的《合同警察》,原先叫《白菜萝卜》,我后来又用这个名字写了另外一篇小说。第三次改变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就是《迷你王八》变成《分享艰难》。小说内容被修改的只有《村支书》,将其中村支书同妇联主任关系暧昧的那条线隐去了。还有一段机敏的对话:村支部开会,民兵连长与妇联主任开着不荤不素的玩笑,村支书不高兴,借故要他们注意群众影响。民兵连长回应说,这里只有党员,没有群众。这些也被删了去。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几年后,因为《分享艰难》的连累,这部小说的结尾被当成画蛇添足。那被批评为故意留下光明的尾巴,成了我背后的靶心。那些瞄准者显然不知其中用心之良苦。不是过来人不知过来累。
1992年4月底,《青年文学》在北京召开创刊十周年纪念会。十年间他们已培养了三代青年作家,他们还让我做了刚刚形成的第三代作家的代表,并在会上发言。几句话下来,自己已被憋得满头大汗。没过多久,就到了夏天,三篇小说的讨论会真的在北京召开了。
几年以后,我同一帮人来北京开会,岁月无多,人却油滑了不少,吆喝着要《青年文学》请吃饭。就在东四十二条旁的小酒馆里,前主编陈浩增举着酒杯问谁给他敬酒,想着自己同他们的关系,我迎上去打了头阵,一口就下去二两,接下来又有几个二两。尔后独自乘出租车去机场,一觉睡到候机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上了飞机在大家的敌视中,我继续醉酒,似乎只过了一会儿,飞机猛地震了一下,睁开眼睛人已回到武汉了。好时光不要多,只需一刻便值千金而终生受用。我有些不像青年了,不会再在尴尬前面茫然,不过我仍然愿意为文学还是这么年轻,这么有活力而心醉! 刘醒龙文学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