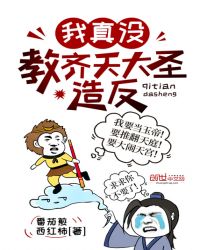由三藩市到天津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老舍作品集·散文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由三藩市到天津
到三藩市(旧金山)恰好在双十节之前,中国城正悬灯结彩,预备庆贺。在我们侨胞心里,双十节是与农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
常听人言:华侨们往往为利害的,家族的,等等冲突,去打群架,械斗。事实上,这已是往日的事了;为寻金而来的侨胞是远在一八五〇年左右;现在,三藩市的中国城是建设在几条最体面,最重要的大街上,侨胞们是最守法的公民;械斗久已不见。
可是,在双十的前夕,这里发生了斗争,打伤了人。这次的起打,不是为了家族的,或私人间利害的冲突,而是政治的。
青年们和工人们,在双十前夕,集聚在一堂,挂起金星红旗,庆祝新中国的诞生。这可招恼了守旧的、反动的人们,就派人来捣乱。红旗被扯下,继以斗殴。
双十日晚七时,中国城有很热闹的游行。因为怕再出事,五时左右街上已布满警察。可惜,我因有个约会,没能看到游行。事后听说,游行平安无事;队伍到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致敬,并由代表们献剑给蒋介石与李宗仁,由总领事代收。
全世界已分为两大阵营,美国的华侨也非例外:一方面悬起红旗,另一方面献剑给祸国殃民的匪酋。
在这里,我们应当矫正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华侨们都守旧,落后。不,连三藩和纽约,都有高悬红旗,为新中国欢呼的青年与工人。
就是在那些随着队伍,去献剑的人们里,也有不少明知蒋匪昏暴,而看在孙中山先生的面上,不好不去凑凑热闹的。另有一些,虽具有爱国的高度热诚,可是被美国的反共宣传所惑,于是就很怕“共产”。
老一辈的侨胞,能读书的并不多。晚辈们虽受过教育,而读不到中国的英文与华文书籍。英文书很少,华文书来不到。报纸呢(华文的)又多被二陈所控制,信意的造谣。这也就难怪他们对国事不十分清楚了。
纽约的《华侨日报》是华文报纸中唯一能报道正确消息的,我们应多供给它资料——特别是文艺与新政府行政的纲领与实施的办法。此外,也应当把文艺图书、刊物,多寄去一些。
十月十三号开船。船上有二十二位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每天举行讨论会,讨论到祖国应如何服务,并报告自己专修过的课程,以便交换知识。
同时,船上另有不少回国的人,却终日赌钱,打麻将。
船上有好几位财主,都是菲律宾人。他们的服饰,比美国阔少的更华丽。他们的浅薄无知,好玩好笑,比美国商人更俗鄙。他们看不起中国人。
十八日到檀香山。论花草,天气,风景,这真是人间的福地。到处都是花。街上,隔不了几步,便有个卖花人,将栀子、虞美人等香花织成花圈出售;因此,街上也是香的。
这里百分之四十八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里的经济命脉却在英美人手里。这里,早有改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之议,可是因为东方民族太多了,至今未能实现。好家伙,若选出日本人或中国人做议员,岂不给美国丢人。
二十七日到横滨。由美国军部组织了参观团,船上搭客可买票参加,去看东京。
只有四五个钟头,没有看见什么。自横滨,到东京,一路原来都是工业区。现在,只是败瓦残屋,并无烟筒;工厂都被轰炸光了。
路上,有的人穿着没有一块整布的破衣,等候电车。许多妇女,已不穿那花里胡哨的长衣,代替的是长裤短袄。
在东京,人们的服装显得稍微整齐,而仍掩蔽不住寒伧。女人们仍有穿西服的,可是鞋袜都很破旧。男人们有许多还穿着战时的军衣,戴着那最恨的军帽——抗战中,中国的话剧中与图画中最习见的那凶暴的象征。
日本的小孩儿们,在战前,不是脸蛋儿红扑扑的好看么?现在,他们面黄肌瘦。被绞死的战犯只获一死而已;他们的遗毒余祸却殃及后代啊!
由参观团的男女领导员们(日本人)口中,听到他们没有糖和香蕉吃——因为他们丢失了台湾!其实,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止糖与香蕉。他们之所以对中国人单单提到此二者,倒许是为了不忘情台湾吧?
三十一日到马尼拉。这地方真热。
大战中打沉了的船还在海里卧着,四围安着标识,以免行船不慎,撞了上去。
岸上的西班牙时代所建筑的教堂,及其他建筑物,还是一片瓦砾。有城墙的老城完全打光。新城正在建设,还很空旷,看来有点大而无当。
本不想下船,因为第一,船上有冷气设备,比岸上舒服。第二,听说菲律宾人不欢喜中国人;税吏们对下船的华人要搜检每一个衣袋,以防走私。第三,菲律宾正要选举总统,到处有械斗,受点误伤,才不上算。
可是,我终于下了船。
在城中与郊外转了一圈,我听到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前两天由台湾运来大批的金银。这消息使我理会到,蒋介石虽在表面上要死守台湾,可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银分给士兵,而运到国外来。据说,菲律宾并没有什么工业;那么,将自己的与他的走狗的财富,便可以投资在菲律宾;到台湾不能站脚的时候,便到菲律宾来作财阀了。依最近的消息,我这猜测是相当正确的。可是,我在前面说过,菲律宾人并不喜欢中国人。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中国人的经营能力强,招起菲律宾人的忌妒。那么,假若蒋匪与他的匪帮到菲律宾去投资,剥削菲人,大概菲人会起来反抗的,一旦菲人起来反抗,那些在菲的侨胞便会吃挂误官司。蒋匪真是不祥之物啊!
舟离日本,遇上台风,离马尼拉,再遇台风。两次台风,把我的腿又搞坏。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难行。
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
在这二十四天里,我看见了天津帮、山东帮、广东帮的商人们,在抢购抢卖运各色的货物。室内室外,连街上,入耳的言语都是生意经。他们庆幸虽然离弃了上海天津青岛,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机者的乐园。
遇见了两三位英国人,他们都稳稳当当的说:非承认新中国不可了。谈到香港的将来,他们便微笑不言了。
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我并不愁暂时没有生意;可虑的倒是将来中外贸易的路线!假若路线是走‘北’路,我可就真完了!”
我可也看见了到广州去慰劳解放军的青年男女们。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确有纪律、有本事、有新的气象!我们还想再去!”
好容易,我得到一张船票。
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猪入圈。码头上的大门不开,而只在大门中的小门开了一道缝。于是,旅客、脚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这缝子里钻进去。嚷啊、挤啊、查票啊,乱成一团。“乐园”吗?哼,这才真露出殖民地的本色。花钱买票,而须变成猪!这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船啊!
挤进了门,印度巡警检查行李。给钱,放行。不出钱,等着吧!那黑大的手把一切东西都翻乱,连箱子再也关不上。
一上船,税关再检查。还得递包袱!
呸!好腐臭的“香”港!
二十八日夜里开船。船小(二千多吨),浪急,许多人晕船。为避免遭遇蒋家的炮舰,船绕行台湾外边,不敢直入海峡。过了上海,风越来越冷,空中飞着雪花。许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
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准登岸,怕携有共产党宣传品,到岸上去散放。美国防共的潮浪走得好远啊,从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鲜!
九日晨船到大沽口。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离开华北已是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
因为潮水不够,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点才又开动;到天津码头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税关上的人们来了。一点也不像菲律宾和香港的税吏们,他们连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我心里说:中国的确革新了!
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几件行李,怎么下船呢?幸而马耳先生也在船上,他奋勇当先的先下去,告诉我:“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还有一位上海的商人,和一位原在复旦,现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过来打招呼:“你在这里等,我们先下去看看。”
茶房却比我还急:“没有人来接吗?你的腿能走吗?我看,你还是先下去,先下去!我给你搬行李!”经过这么三劝五劝,我把行李交给他,独自慢慢扭下来;还好,在人群中,我只跌了“一”跤。
检查行李是在大仓房里,因为满地积雪,不便露天行事。行李,一行行的摆齐,丝毫不乱;税务人员依次检查。检查得极认真。换钱——旅客带着的外钞必须在此换兑人民券——也依次而进,秩序井然,谁说中国人不会守秩序!有了新社会,才会有新社会秩序呀!
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
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所去。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
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彷徨歧途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载1950年《人民文学》第4期 老舍作品集·散文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