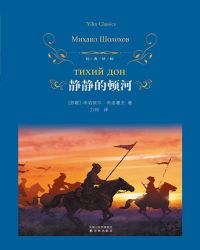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八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八章
在离杜尔诺尔镇不远的地方,维奥申乡的哥萨克团第一次参加了拦击后退的红军部队的战斗。
格里高力·麦列霍夫率领的一个连,快到晌午时候占领了一个杂树丛生的小村子。格里高力命令哥萨克们在一条流过村子、冲出一道浅沟的小溪旁边的柳荫里下了马。不远处,有几股泉水从黑黑的烂泥中咕咕地向外冒着。泉水冰凉,哥萨克们用制帽舀起泉水不要命地喝了一阵子,然后得意洋洋地咯咯叫着把制帽扣在汗淋淋的脑袋上。太阳升到了村庄的当头,村庄热得好像昏迷了似的。大地晒得滚烫,冒着腾腾的热气。青草和柳树叶子被毒热的阳光晒得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可是在溪边柳荫下却是一片阴凉,牛蒡草和潮湿的土地滋润着的另外一些茂草翠绿翠绿的;小水湾里的浮萍亮闪闪的,就像心爱的姑娘的笑靥;一处大水湾过去,有几只鸭子在泅水和拍打翅膀。马匹打着响鼻,吧唧吧唧地踩着烂泥,扯着人手里的缰绳,拼命往水里跑,一直跑到小溪中心里,把溪水搅得浑浑的,又用嘴去寻找清凉的水流。热风从垂着的马嘴上吹下一大滴一大滴晶莹的水珠儿。马踩得乱糟糟的淤泥和绿肥苔发出一股硫磺气味,那溪水泡烂的柳树根也发出一股又苦又甜的气味……
哥萨克们刚刚说着话和抽着烟,在牛蒡草丛里躺下来,侦察班就回来了。大家一听到侦察班报告说有红军,一齐从地上跳了起来。紧了紧马肚带,又朝溪边走去,把水壶灌满了,又喝了一阵子,看样子每个人心里都在想:“这样清清亮亮、像小孩子眼泪一样的泉水,也许还能喝到,也许喝不到啦……”
哥萨克们顺着大路跨过小溪,停了下来。
村外一俄里远处,长满野艾的灰色沙土岗上出现了红军的侦察班。八名红军骑兵正小心翼翼地朝村子方向走来。
“咱们逮他们去!行吗?”米佳·柯尔叔诺夫向格里高力建议说。
他带着半个排绕路出了村子,但是红军侦察班一发现哥萨克,就掉转马头往回走了。
过了一个钟头,同团的另外两个骑兵连一来到,就一齐出发了。侦察兵报告说,红军大约有一千条枪,正迎着他们开来。维奥申团这三个连和在右方前进的第三十三叶兰乡、布堪诺夫乡联合团失去了联系,但是这三个连还是决心迎战。翻过岗头,就都下了马。看守马匹的哥萨克把马都牵到了面向村子的一片宽敞的洼地里。右边不知什么地方,双方的侦察队发生了接触。一挺手提机枪气势汹汹地响着。
不久就出现了红军的稀疏的散兵线。格里高力命令自己的连队在洼地上边散了开来。哥萨克们在长满了像马鬃一样的小树棵子的斜坡顶端卧倒下来。格里高力在一棵矮矮的野苹果树下,用望远镜观察着远处的敌军散兵线。他清清楚楚地看到,在前面前进的是两排散兵线,两排散兵线后面,是黑压压的大队人马拉开阵势,在已经割倒、然而尚未运走的小麦堆中间前进着。
令他和哥萨克们很吃惊的是,在第一排前面骑着一匹高高的白马前进的那个人,看样子是一位指挥官。第二排前面也有两个指挥官各自走着。第三排也由一位指挥官率领着,他的旁边是一面猎猎飘舞的军旗。军旗鲜红鲜红的,在灰黄色的麦茬地衬托下,就像一个小小的血点子。
“人家的委员都打头阵哩!”一个哥萨克叫道。
“呵!真有种!”米佳·柯尔叔诺夫赞赏地哈哈大笑起来。
“伙计们,瞧!红军他们热头不小哇!”
差不多全连的人都欠起身来,互相呼喊着。一个个都把手掌搭到眼睛上遮住太阳。说话声听不到了,于是面临死亡时的肃穆与寂静就像一片云彩影子一样,及时地、悄悄地来到草原和洼地上。
格里高力朝后面看了看。一丛灰灰的柳树后面,村子的一旁,扬起一股尘土;第二连飞跑着朝敌军的侧翼冲去。一道山沟暂时掩护着第二连的行动,但是第二连跑了有四俄里,就散了开来,朝岗头上爬去,于是格里高力在心里判断着距离和第二连能够冲到敌军侧翼的时间。
“卧倒——倒!”格里高力急忙转过身去,把望远镜放进皮套子,命令道。
他走到自己的队伍跟前。哥萨克们那落满灰尘、晒得黑油油、红彤彤的脸一齐朝他转了过来。大家面面相觑,卧倒下去。喊过“预备”的口令以后,枪栓咔嚓咔嚓地响了一阵子。格里高力在上面只能看见一双双叉开的腿、一顶顶制帽的帽顶和一个个穿着沾满尘土的军便服的脊背,还看得清那汗湿透了的脊梁沟和肩胛骨。哥萨克们爬来爬去,寻找可以隐蔽的地方,选择更妥当的地方。有的人在用马刀挖掘干硬的土地。
这时候,一阵微风从红军那边吹来,送来隐隐约约的歌声……
红军的散兵线前进着,曲曲弯弯,有前有后,晃晃悠悠。隐隐约约、在炎热而辽阔的大地上显得很孤单的歌声就从那边传了过来。
格里高力觉得,自己的心一震,然后就猛烈地、时断时续地跳了起来……他以前也听到过这种沉痛的歌声,他在格鲁博克就看见赤卫队的水兵像祷告一样摘下无檐帽,慷慨激昂地闪动着眼睛,唱起一支歌,唱的就是这支歌。格里高力心中突然涌起一种模模糊糊的、很像是恐怖的慌乱不安心情。
“他们喊叫什么呀?”一个年老的哥萨克慌慌张张地转悠着脑袋,问道。
“好像是在念经。”另外一个躺在右边的哥萨克回答说。
“哪儿是他妈的念经,”安得列·卡叔林笑道,他很不客气地望着站在他旁边的格里高力,问道:“潘捷莱耶维奇,你在他们那边干过,你想必知道他们这会儿唱这种歌儿干什么吧?你恐怕也跟他们一起唱过吧?”
“……夺取土地!” ——因为距离太远还是有些含混不清的这一句忽然像欢呼一样高了起来,接着又是一片寂静笼罩住原野。哥萨克们冷笑起来。阵地中心有人放声哈哈大笑。米佳·柯尔叔诺夫沉不住气了:
“喂,你们听见吗?!他们想夺取土地哩!……”他又破口大骂了一阵子。“格里高力·潘捷莱耶维奇!让我把那个骑马的家伙打下马来!让我放一枪吧?”
不等同意,他就开了一枪。这一枪惊动了那个骑马人。他下了马,把马交给别人,挥舞着出鞘的马刀,带领队伍朝前冲来。
哥萨克们开枪了。红军卧倒了。格里高力命令机枪手开火。机枪打过两梭子以后,第一排的红军站起来,往前跑了一截路。跑了有十来丈,又卧倒了。格里高力看见,红军用铁锹挖起掩体。一团团的灰尘在他们头上升起,阵地前面出现了许多小小的土堆,就像是土拨鼠打洞掏出来的。那边也响起长长的齐射声。双方交火了。大有变成持久战之势。一个钟头之后,哥萨克一方受到了损失:第一排有一个哥萨克被打死,三个受伤的被送到洼地里看守马匹的人那里。第二连在红军的侧翼出现,发起了冲锋。冲锋被机枪火力打退。可以看见,哥萨克们十分狼狈地往后逃窜,时而挤成一团一团的,时而像扇子一样散了开去。第二连退回来以后,整了整队形,不再呐喊,一声不响地又往前冲。又是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就像疾风扫落叶一样,把第二连赶了回来。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动摇了红军的坚定性,前面几排乱了,往后退去。
格里高力一面射击,一面命令连队起立。哥萨克们朝前冲去,不再卧倒。起初他们感觉到的那种犹豫和重重的顾虑现在好像消失了。迅速开上阵地的一支炮兵连更加鼓舞了他们的斗志。炮兵第一排准备就绪,开火了。格里高力派人去传达他的命令,叫看守马匹的人把刀带过来。他准备发起冲锋。就在战斗开始他观察红军的那棵野苹果树旁边,第三门炮也从炮车上卸了下来。一个穿着窄腿马裤的高个子军官,一面朝大炮跟前跑,用鞭子抽打着靴筒,一面粗声粗气、恶狠狠地骂着那些动作迟缓的炮手们。
“快点!嗯?!你们他妈的都该打!……”
一位观测员和一位校官,在离炮兵连半俄里的地方下了马,站在坟头上用望远镜观察退却的红军队伍。电话兵在跑着拉电线,连接炮兵连和观测点。炮兵连连长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尉,他用粗大的手指急急忙忙地旋转着望远镜的镜头,有一个手指头上的结婚戒指闪着金光。他无所事事地在第一门大炮旁边转悠着,有时候歪一歪脑袋,躲避嗖嗖飞过的子弹,他每歪一下脑袋,挂在腰侧的旧军用袋都要晃悠几下。
咔啦啦一声响过之后,格里高力观察了一下发射出去的炮弹落下的地方,又回头看了看:炮手们俯着身子,正呼哧呼哧地在移动大炮。第一颗榴霰弹在没有运走的小麦堆上炸了开来,白色的硝烟像棉花团一样,被风吹得飘飘荡荡,在蓝天的背景上飘荡了很久才散去。
四门大炮轮流朝割倒的小麦堆那边发射着炮弹,但是出乎格里高力意料的是,炮火并没有在红军队伍里造成明显的混乱——他们不慌不忙、很有秩序地往后退着,而且已经渐渐走出视线以外,正翻越一处隘口,朝山沟里走去。格里高力明知冲锋毫无意义,但他还是决定和炮兵连长商量商量。他一摇一摆地走过来,用左手摸着被太阳晒得发烫的、红红的、拳曲的胡子尖儿,很亲热地笑了笑,说:
“我想发动一次冲锋。”
“还冲什么锋呀!”大尉执拗地摇了摇头,用手背擦了擦从帽子底下流出来的汗水。“您看,狗崽子们是怎样退的?他们不会输的!而且说起来也是笑话——他们这些队伍里的军官全是正规军的军官。我的老同事谢洛夫中校就在他们这里面……”
“您怎么知道的?”格里高力很惊异地眯起眼睛,问道。
“有人跑过来……停止射击!”大尉发过命令,似乎是要解释一下。“打炮也没有用,炮弹又太少……您是麦列霍夫吧?咱们认识认识:我是波尔塔福采夫。”他把一只汗津津的大手一杵,塞到格里高力的手里,匆匆握了握,就很麻利地把手伸进敞着口的图囊里,掏出纸烟。“请抽烟!”
炮队轰轰隆隆地从洼地里爬了上来。大炮都挂到了前车上。格里高力命令连队上马,就带着自己的连队去追已经翻过岗头的红军。
红军占领了前面的一个村庄,但是又毫不抵抗地退了出去。维奥申乡的三个连和一个炮兵连就在这个村子里驻扎下来。老百姓都吓得不敢出门。哥萨克们挨门挨户地串,寻找可吃的东西。格里高力在村外一户人家门前下了马,走进院子,把马拴在台阶旁边。房东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瘦长的哥萨克,正躺在床上,哼哼着,像鸟头一样的小头在肮脏的枕头上不住地滚动着。
“怎么,你病了吗?”格里高力向他打了个招呼,笑着问道。
“病啦——啦……”
房东是装病,而且他从格里高力那滴溜溜乱转悠的眼神上猜出来,格里高力是不相信他的话的。
“给弟兄们弄点饭吃,好吗?”格里高力正色问道。
“你们几个人?”房东老婆从灶边走过来,问道。
“五个人。”
“那好吧,请这边来,尽家里有的给你们吃点儿吧。”
格里高力和几个哥萨克一同吃过饭,走了出来。
仍处于充分战备状态的炮兵连停在水井旁边。没有卸套的马摇晃着草米袋,正在吃大麦。驭手和炮手们在大炮旁边坐着或躺着,在炮弹箱的凉阴里躲避太阳。一个炮手交叉着两腿,趴在地上睡着了,在睡梦中还不住地抽动肩膀。看样子,他原来是躺在凉阴里的,可是太阳移动了阴影,所以这会儿太阳晒到了他那落了一层草屑的、完全露在外面的鬈发上。
马身上,宽宽的皮马套旁边,鬃毛湿漉漉、亮闪闪的,冒着黄黄的汗沫。军官和炮手们骑的马都拴在篱笆上,无精打采地蜷着腿站着。哥萨克们都满身灰土,汗流浃背,都一声不响地在休息。几个军官和炮兵连连长背靠着井栏杆,在抽烟。在离他们不远处,有几个哥萨克扎煞开两腿,像六角星一样趴在晒干的滨藜上。他们一个劲儿地舀罐子里的酸牛奶喝,偶尔地有人往外吐一吐喝进嘴里的大麦粒儿。
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村子里的几条街道向山冈伸去,街道上几乎没有人影。谷仓旁边,敞棚底下,篱笆脚下,牛蒡草的黄黄的阴影里,到处都有哥萨克在睡觉。没有卸鞍的战马密密层层地站在篱笆旁边,热得难受,也困得难受。一个哥萨克懒洋洋地把鞭子举得和马背一般高,骑着马走了过去。于是街道又像是被人遗忘的草原路,那漆成绿色的大炮,那跑累了、晒乏了、已沉沉入睡的人们,好像都是偶然出现、毫不相干的东西。
格里高力闲得无聊,正要朝住的房子里走去,但是街上出现了别的连的三个骑马的哥萨克。他们押着一小伙被俘的红军。炮兵们都忙活起来,站起身来,拍打着军便服和裤子上的尘土。军官们也站了起来。附近院子里有人高高兴兴地喊道:
“伙计们,押俘虏来啦!……不信吗?快来看看吧!”
睡眼惺忪的哥萨克们急急忙忙从各家院子里跑了出来。俘虏来到跟前——这是八个浑身冒着汗臭气、满脸灰尘的年轻小伙子。大家把他们密密层层地包围了起来。
“在哪儿捉住他们的?”炮兵连连长带着冷峻而好奇的神情打量着俘虏们,问道。
一个押解的哥萨克带着逞能的意味回答说:
“简直是脓包!我们是在村边葵花地里捉住他们的。他们躲在那儿,就像小鸡躲老鹰一样。我们看见他们,放马就追!打死了一个……”
八个红军士兵吓得挤成了一堆。显然,他们是害怕随意摧残。他们的目光失神地在哥萨克们的脸上扫着。只有一个红军士兵,看样子年纪大一些,脸晒成了棕色,颧骨高高的,穿着油糊糊的军便服,打着破烂的裹腿,微微斜着两只黑眼睛从人们头上鄙夷地望着远方,并且紧紧闭着被打出了血的嘴唇。他矮墩墩的,肩膀宽宽的。在他那硬得像马鬃一样的黑黑的鬈发上,扣着一顶军帽,就像一张绿色的饼子,军帽上还留着帽徽的印子,大概,这帽子在对德战争的时候就戴着了。他稍息站着,用黑黑的、指甲上沾着干血的粗手指头摸着敞开的衬衣领口和尖尖的、生满黑毛的喉结。看样子他好像满不在乎,但是他那条稍息站着、因为打了破裹腿直到膝部都粗得很难看的腿,却像打寒战一样轻轻哆嗦着。其余的几个都脸色灰白,面无人色,只有这个人的肩膀那雄壮的姿态和他的鞑靼型的虎虎有生气的脸格外引人注意。也许就因为这样,炮兵连连长朝着他问道:
“你是什么人?”
这个红军士兵的小小的、黑得像煤炭一样的眼睛活动起来,而且他的全身不知不觉地、然而很敏捷地收敛起来。
“我是红军。是俄罗斯人。”
“你是什么地方人?”
“是奔萨人。”
“坏蛋,你是自愿干的吗?”
“才不是呢。我是旧军队的上士。从一九一七年当了红军,一直到现在……”
一个押解的哥萨克插嘴说:
“就是他朝我们开枪的,该杀的!”
“你开枪了吗?”大尉很不满意地皱起眉头,他碰到站在对面的格里高力的眼神,就用眼睛瞟着俘虏,说:“坏蛋!……开枪了吗,嗯?你怎么,没有想到会被捉住吧?现在如果为这事儿把你枪毙,你有什么说的?”
“我是想自卫呀。”那打破的嘴唇撇了撇,露出遗憾的笑容。
“坏家伙!你为什么没有自卫到底呢?”
“子弹打光啦。”
“是——这——样……”大尉的眼神一下子凉了下来,但他带着掩饰不住的满意神情打量了一遍这个士兵。“那你们呢,狗崽子们,是哪儿的?”他已经用快活的眼睛瞟着其余的红军士兵,换了一种腔调问道。
“我们是被抓来当兵的,大人!我们有的是萨拉托夫人……有的是巴拉绍夫人……”一个长脖子、高个子小伙子不住地眨巴着眼睛,挠着红红的头发,很伤心地说。
格里高力异常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身穿绿军装的年轻小伙子,打量着他们那一张张朴实的庄稼汉的脸和那不起眼的步兵装束。只有那个高颧骨的士兵激起他的仇恨。他用讥笑和痛恨的口吻对那个红军士兵说:
“你为什么招认呢?你大概在他们那儿领着一个连吧?是连长吧?是共产党员吧?你不是说,你把子弹打光了吗?我们要是为这事把你砍了,又怎样呢?”
那个红军士兵翕动着被枪托子打扁了的鼻子眼儿,更大胆地说:
“我招认也不是为了逞强,我有什么好瞒的呢?既然开了枪,就要承认……我说的对吗?要杀……就杀吧。我不指望……”他又笑了笑,“不指望你们宽待,因为你们是哥萨克嘛。”
周围的人都赞赏地笑起来。格里高力听了这番理直气壮的话,无言对答,就走开了。他看见,俘虏们朝井边走去,要去喝水。有一连哥萨克步兵成排纵队从胡同里开出来。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