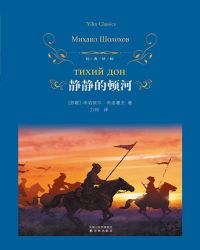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二十一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十一章
一年的工夫,麦列霍夫家的人口减少了一半。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有一次说死神看上了他们家,这话说对了。刚刚把娜塔莉亚埋葬过,麦列霍夫家宽敞的上房里又散发出神香和矢车菊的气味。格里高力离家上前方以后十来天,妲丽亚在顿河里淹死了。
星期六,她从地里回来,就和杜尼娅一同去洗澡。她们在菜园边上脱掉衣服,在柔软的、被脚踩倒的青草上坐了半天。还是从清晨起,妲丽亚就心神不定,说是头疼,身子不舒服,偷偷地哭了好几次……在下水以前,杜尼娅把头发挽成一个鬏儿,用头巾包起来,侧眼朝妲丽亚看了看,很心疼地说:
“妲什卡,看你瘦成什么样子啦,所有的青筋都露出来啦!”
“很快就要胖起来了!”
“你的头不疼了吗?”
“不疼啦。嗯,咱们下水吧,天不早啦。”她在头里跑着下了水,连头扎进水里,后来又钻出水来,打着响鼻,朝河中心游去。急流卷住了她,冲着她往前漂去。
杜尼娅欣赏着妲丽亚那像男人一样大划着两臂的游泳姿势,她也走进齐腰深的水里,洗了洗脸,泡了泡胸膛和晒得黑黑的、结实而丰润的两条胳膊。在旁边的菜园里,奥布尼佐夫家的两个儿媳妇在浇白菜。她们听见杜尼娅笑着在唤妲丽亚:
“回来吧,妲什卡!别叫鲶鱼把你拖走了!”
妲丽亚掉转身来,洑了有三丈远,后来从水里跳出半截身子,把两只手举起来,喊道:“姊妹们,我走啦!”然后就像石头一样沉入水里。
过了有一刻钟,脸色煞白的杜尼娅只穿着一条衬裙,跑回家里。
“妈妈,妲丽亚淹死啦!……”她气喘吁吁地说。
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用大鱼网的钩子把妲丽亚捞了上来。鞑靼村最有经验的老渔夫阿尔希普·皮司科瓦特柯夫黎明时候在妲丽亚淹死的地方的下游,下了六张大鱼网,然后和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一同去检查鱼网。岸上站着一大群孩子和妇女,其中也有杜尼娅。当阿尔希普用桨柄挑着第四根网绳,离开河岸有十丈远的时候,杜尼娅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小声说:“大概,这就是……”于是他使劲拉着直往下坠的网绳,小心翼翼地把网往上提。后来有一个白白的东西出现在右岸边,两个老头子就弯下身去,小船的边上进了一点儿水,于是安静下来的人群听见尸体低沉地响了一声,上了小船。人群里齐声出了一口气。有一个娘们儿低声抽搭起来。站在不远处的贺里散福大声吆喝孩子们:“喂,你们都滚远点儿!”杜尼娅含着眼泪,看着阿尔希普站在船尾,熟练而无声地划着桨,朝岸边划来。小船沙沙地、咯吱咯吱地轧着岸边的石灰质砂石,靠了岸。妲丽亚软绵绵地弯着腿躺着,一边腮帮子贴在水漉漉的船底上。她那白白的身体微微有些发青,泛着一种淡紫色,身上有几处很深的窟窿,那是钩子钩的。在一条又瘦又黑的腿肚子上,膝盖下面一点儿、在洗澡前忘记解下的袜带旁边,有一条新鲜的红印子,还隐隐渗着血。那是鱼网钩子的尖儿在腿上划了一下,划出了一道斜斜的血印子。杜尼娅哆哆嗦嗦地揉着围裙,头一个走到妲丽亚跟前,用一条拆开来的麻袋把她盖上。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急急忙忙一本正经地挽起裤腿,把小船往上拖了拖。很快就来了一辆大车,把妲丽亚拉到麦列霍夫家里。
杜尼娅克制着害怕和厌恶的心情,帮着母亲擦洗还保留着河底深水凉气的冷冰冰的死人身子。妲丽亚那微微肿起的脸上,那被河水泡得失去光彩的眼睛的暗淡反光中,有一种陌生而严肃的神气。她的头发里夹杂着不少银光闪闪的河底流沙,脸上粘着一条条潮湿的青苔,而那两条摊了开来、软软地从板床上耷拉下来的胳膊,却显出心灰意冷的样子,杜尼娅看了一眼,就连忙离开她,因为又惊愕又害怕,觉得这死去的妲丽亚简直不像那个不久前还有说有笑、热爱生活的人了。后来有很长时间,杜尼娅一想到妲丽亚那冰凉的乳房和肚子,一想到那软绵绵、动也不动的四肢,就浑身打哆嗦,希望能快些忘掉这一切。她很怕夜里会梦见死去的妲丽亚,有一个星期都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而且临睡前要祷告上帝,在心里央告:“主啊!别叫我梦见她呀!保佑我吧,主啊!”
如果不是奥布尼佐夫家的两个儿媳妇说出她们曾经听见妲丽亚喊叫:“姊妹们,我走了!”就会顺顺当当地把淹死的人埋葬掉的,但是维萨里昂神甫一听说妲丽亚死前曾经这样喊叫,而这种喊叫显然表明妲丽亚是有意寻死的,所以神甫就毅然决然声明,他不能为寻死的人念经祈祷。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气忿地说:
“你怎么能不给念经呢?怎么,她不是教徒吗?”
“我不能给寻死的人举行葬仪,照规矩不能这样。”
“那又怎样来葬她呢?照你说,把她像狗一样埋掉吗?”
“照我说,你愿意怎样埋就怎样埋,愿埋在哪儿就埋在哪儿,只是不能埋在公共坟地里,因为那儿葬的都是清白的基督教徒。”
“不行,请你做做好事吧!”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换成哀求的语气,“我们家还从来没出过这种丢脸的事呢。”
“我不能答应。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我很尊敬你,你是个模范教民,但是我不能答应。要是有人报告到教区监督司祭那里去,我就免不了倒霉。”神甫很固执地说。
这是很丢脸的事。于是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想方设法来劝说倔犟的神甫,答应多给一些钱,而且要给顶可靠的尼古拉票子,还说要送一只刚生过一胎的母羊,但是到末了,看到劝说无效,就威胁说:
“我不能把她埋在坟地外面。她不是和我不相干的人,是我的亲儿媳妇。她的丈夫是和红军作战牺牲的,他是军官身份,媳妇本身也得过十字章,可是你要给我找麻烦吗?!不行,神甫,你办不到,想不叫下葬呢,怪事!就让她躺在屋里好啦,我这就去报告乡长。他会和你说话的!”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从神甫家里走了出来,临走不但没有道别,甚至还气呼呼地把门摔了一下。不过吓唬生效了:过了有半个钟头,维萨里昂神甫派人来说,他马上就来念经。
按照常规,把妲丽亚葬到了坟地里,跟彼特罗挨着。在挖坟的时候,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也给自己看好了一块地方。他一面挖坟,一面张望,心里估量,比这儿好的地方再也找不到了,也用不着再去找了。不久前才栽的一棵白杨树在彼特罗的坟头上沙沙地摇晃着嫩枝儿;即将来临的秋天,已经把杨树顶上的叶子染成凄凉的枯黄色。小牛跨过倒塌的围墙,在坟墓之间踩出一条条的小路;围墙外面有一条路通向风磨;关切死者的亲人们栽种的树木,有枫树、杨树、槐树,还有茂密的刺花李,都碧绿碧绿的,显得又亲切,又有生气;树旁生长着一丛丛的牵牛花,晚芥菜开着黄花,燕麦草和冰草都结了穗儿。一个个十字架,从上到下都缠满了可爱的、蓝蓝的旋花儿。这地方实在很舒服,很干爽……
老头子挖着坟,常常扔下铁锹,坐在潮乎乎的黄土上,抽着烟,想着死的事情。但是,看样子,年头不对了,恐怕很难平平安安地老死在自己家里,安葬在祖祖辈辈长眠的地方了……
安葬了妲丽亚以后,麦列霍夫家里更加冷清了。收割庄稼,打场,采摘瓜地里的丰收的瓜。天天盼望格里高力的消息,但是他一去就没有音讯。伊莉尼奇娜不止一次说:“也不写封信来问问孩子们好不好,该死的东西!老婆一死,他根本不问我们的事啦……”后来当兵的哥萨克回鞑靼村探望的多了起来。带回来一些传闻,说是哥萨克在巴拉绍夫打败了,所以往顿河上撤退过来,为的是利用顿河为屏障,固守到冬天。可是到冬天又怎么样呢?关于这一点,所有的老兵都毫不隐讳地说:“等顿河一结冰,红军就把咱们赶进海里啦!”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勤勤恳恳地在打场,似乎不怎么理会流传在顿河两岸的消息,但是他对于局势并不是无动于衷。他听说快要打过来了,就常常对伊莉尼奇娜和杜尼娅吵骂,火气更大了。他常常修理一些农活儿上用的东西,但是只要一不顺手,他就怒冲冲地把活儿扔下,一面啐着、一面骂着跑到场院上去,到那里去冷一冷自己的火气。杜尼娅不止一次看见他发这种脾气。有一次他修牛轭,干得不顺手,突然发起火来的老头子就抓起斧子,把牛轭砍成了一堆碎木头片。有一次修马套也是这样。那一天晚上,老头子在灯下纫上麻线,就缝起裂了口的马套来;不知是麻线霉烂了,还是老头子太性急,反正麻线接连断了两次,这就不得了啦:老头子狠狠地骂了两声,跳了起来,把凳子踢翻,又一脚踢到灶前,又像狗一样呜噜呜噜叫着,用牙齿撕咬起马套上的皮贴边,然后把马套扔到地上,像公鸡一样跳着,用脚踩起马套来。伊莉尼奇娜早已睡下,听见喧闹声,吓得跳了起来,但是一看是这么回事儿,就忍不住骂起老头子:
“该死的东西,都这么大年纪了,你疯啦?!马套哪儿得罪你了?”
老头子拿发了疯的眼睛瞪了瞪老伴儿,吼了起来:
“你住嘴——嘴,浑蛋娘们儿!”又抓起破马套,朝老伴儿扔过来。
杜尼娅笑得喘不过气来,赶快跑到过道里去了。老头子发过一阵子疯,就安静下来,请老伴儿原谅他在火头上说的一些气话,并且要搔着后脑勺子嘟哝上老半天,望着已经撕成碎片的倒霉的马套,心里盘算着:这玩意儿还能派什么用场?他这样发火已经不止一次了,但是伊莉尼奇娜却从痛苦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采取了另外一种对策:等老头子一开口大骂,毁坏起什么家什,伊莉尼奇娜就很温顺然而十分响亮地说:“砸吧,老头子!砸得烂烂的!咱们还能挣回来嘛!”并且还做样子要帮他砸一砸。这么一来,老头子马上就没有了劲儿,用发呆的眼睛对着老伴儿看上一会儿,然后就把哆哆嗦嗦的手伸到口袋里,掏出烟荷包,很不好意思地坐到一边去抽起烟来,平息平息激动的神经,心里咒骂着自己的脾气,估计一下这一次的损失。一只三个月的小猪跑进菜园子里,也成了老头子发泄怒气的对象。他用铁棍打断了小猪的脊梁骨,可是过了五分钟,他一面用钉子帮着拔宰掉的小猪身上的鬃毛,一面用讨好的目光歉疚地看着愁眉苦脸的伊莉尼奇娜,说:
“这小猪简直是祸害……反正他妈的是要死。这会儿正是流行猪瘟的时候;宰了吃掉最好,免得白白糟蹋掉。老婆子,你说是吗?嗯,你干吗愁眉苦脸呀?这该死的小猪,坏透啦!小猪不像小猪,简直像个猪妖怪!一点儿都经不住打!可是又拼命祸害人!一下子就刨了四十窝土豆!”
“园子里的土豆总共不过三十窝嘛。”伊莉尼奇娜小声反驳说。
“哼,要是有四十窝的话,它会糟蹋四十窝的,就是这种东西!谢天谢地,这一下子叫它糟蹋不成啦!”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连想都不用想,就回答说。
孩子们送走了父亲以后,非常想念他。伊莉尼奇娜忙于家务,没有很多时间照应他们,于是两个没人管的孩子就整天在园子里或者场院上玩耍。有一天,吃过午饭米沙特卡就不见了,直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才回来。伊莉尼奇娜问他上哪儿去来,米沙特卡回答说,跟孩子们在河边玩来着,但是波柳什卡马上就揭了他的底:
“他扯谎呢,奶奶!他上阿克西妮亚婶婶家去啦!”
“你怎么知道的?”伊莉尼奇娜听到这件事很惊愕,很不痛快,就问道。
“我看见他从他们家爬篱笆过来的。”
“怎么,你是上她家去了吗?嗯,说嘛,乖孩子,怎么脸红啦?”
米沙特卡对着奶奶的眼睛看了看,回答说:
“奶奶,我说谎啦……是的,我不是在河边玩儿,是上阿克西妮亚婶婶家去啦。”
“你干吗上她家去?”
“她叫我去,我就去了。”
“那你为什么撒谎,说是和孩子们一块儿玩呢?”
米沙特卡踌躇了一会儿,但是后来抬起诚实的眼睛,小声说:
“我怕你要骂……”
“我干吗要骂你呀?不骂……她干吗叫你去呀?你在她家干什么来?”
“什么事也没干。她看见我,就喊:‘上我这儿来!’我就走过去,她把我领进屋里,抱我坐在椅子上……”
“怎么样?”伊莉尼奇娜细心地掩饰着激动的心情,焦急地追问道。
“……她给我吃了几块凉饼子,后来又给我这个。”米沙特卡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糖来,很得意地舔了舔,又藏到口袋里。
“她对你说什么来?也许问你什么了吧?”
“她说,叫我常到她家去玩儿,要不,她一个人在家里很闷,还答应送我好东西……她叫我别说到她家去过。她说,奶奶知道了要骂的。”
“是这样啊……”伊莉尼奇娜因为憋着怒气,憋得气喘吁吁地说,“噢,她怎么,问你什么了吗?”
“问啦。”
“她问什么来着?你说说吧,乖孩子,别怕!”
“她问:你想不想你爹?我说:想。她又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有没有听说他怎样,我就说,我不知道,说他在前方打仗呢。后来她抱我坐在她的膝盖上,还给我讲了个故事。”米沙特卡的眼睛很兴奋地放起光来,他笑了起来。“故事才好听呢!说的是一个小瓦尼亚,骑着天鹅到处飞,还说了一个老妖婆。”
伊莉尼奇娜撇着嘴,听完了米沙特卡的自白,就很严厉地说:
“孩子,再别上她家去啦,不许去。她给你什么,你都别要,不许要,要不然,爷爷知道了,要打你!万一叫爷爷知道了,把你的皮都揭下来!好孩子,千万别去了!”
但是,尽管有严厉的禁令,过了两天,米沙特卡又上阿克西妮亚家去了。伊莉尼奇娜一看见米沙特卡的小褂子,就知道了这件事:小褂的袖子原来是破了,早晨起来她没有抽出工夫来补,现在却补得好好的了,而且领子上添了一颗崭新的白贝壳扣子。伊莉尼奇娜知道正忙着打场的杜尼娅白天是没有工夫给孩子补衣服的,就带着责备的口气问道:
“你又上她家去啦?”
“又去啦……”米沙特卡惊慌地说,并且马上又补充说,“我再也不去了,奶奶,你可别骂我……”
于是伊莉尼奇娜决意和阿克西妮亚谈谈,对她说清楚,叫她不要碰米沙特卡,不要拿送东西、讲故事来收买孩子的心。伊莉尼奇娜在心里说:“这该死的娘们儿,害死了娜塔莉亚,现在又在孩子身上打主意,想通过孩子把格里什卡缠住。哼,真是一条毒蛇!自己的男人还活着,就要当我们家儿媳妇……休想!再说,造下这样的孽以后,格里什卡还会要你吗?”
格里高力在家时避免和阿克西妮亚见面的情形,是逃不过当母亲的那敏锐而嫉恨的眼睛的。她明白,格里高力这样做,并不是怕人说闲话,而是他认为娜塔莉亚的死和阿克西妮亚是有关系的。伊莉尼奇娜暗下希望,娜塔莉亚的死能够使格里高力和阿克西妮亚一刀两断,希望阿克西妮亚永远不要成为麦列霍夫家的人。
就在这一天傍晚,伊莉尼奇娜在河边看见阿克西妮亚,就唤她说:
“喂,上我这儿来一下,我要和你谈谈……”
阿克西妮亚放下水桶,心平气和地走过来,问了一声好。
“是这样,他婶子,”伊莉尼奇娜用试探的目光看着女邻居那漂亮而可憎的脸,开口说,“你干吗要勾引人家的孩子呀?你把孩子叫到你家去干什么呀?谁请你给他补衣裳,谁请你送他这样那样东西来?你怎么,以为孩子死了娘就没人管了吗?没有你就不行吗?你的良心真好,真不要脸!”
“我做了什么坏事儿啦?大婶子,您骂什么呀?”阿克西妮亚红了脸,问道。
“什么坏事儿不坏事儿?你害死了娜塔莉亚,凭什么又来招惹她的孩子?”
“您怎么啦,大婶子!住嘴吧!谁害死她来?她是自个儿死的嘛。”
“不就是因为你吗?”
“哼,那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我知道!”伊莉尼奇娜激动地叫起来。
“您别嚷嚷,大婶子,我不是您的儿媳妇,用不着您来管。我有我的男人。”
“我把你看透啦!看透了你的心思!你不是儿媳妇,可是想做儿媳妇!你是想先勾引孩子,然后缠上格里什卡,是吧?”
“我可不想做你们家的儿媳妇。您疯啦,大婶子!我男人还活着呢。”
“就是你男人活着,你还要死乞白赖地缠别的男子汉呢!”
阿克西妮亚的脸一下子变得煞白,她说: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这样骂我、糟蹋我……我从来就没赖缠过什么人,而且今后也不想赖缠什么人,要说把您的孙子叫到我家来,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您也知道,我没有孩子,我喜欢别人的孩子,有别人的孩子也要好过些,所以我叫他来玩儿……你以为我是收买他呀!给孩子一块糖,这就是收买啦?我收买他干什么呀?天知道您胡说些什么!……”
“他娘活着的时候,你从来没叫他去过!娜塔莉亚一死,你就充起好人来啦!”
“娜塔莉亚活着的时候,他也常上我家里来玩儿。”阿克西妮亚微微笑了笑,说。
“你别胡说,不要脸的东西!”
“您先去问问他,然后再看是不是胡说。”
“哼,不管怎么样,你以后别再叫孩子到你家去了。你别以为,这样格里高力就更喜欢你。你做不了他的老婆,你记着吧!”
阿克西妮亚的脸气得都变了样子,她沙哑地说:
“你住嘴吧!他的事用不着问你!你少管闲事!”
伊莉尼奇娜还想说几句,但是阿克西妮亚一声不响地扭过身去,走到水桶跟前,猛地把扁担往肩上一搭,就顺着小路飞快地朝前走去,颠得桶里的水直往外泼洒。
从这时候起,她见到麦列霍夫家的任何人都不打招呼,而是鼓起鼻孔,带着又气又骄傲的神气从旁边走过去;但是她要是在什么地方看见米沙特卡,就慌慌张张地四下里望一望,如果附近没有人,她就跑到他跟前,弯下身去,把他搂在怀里,吻着他那晒得黑糊糊的小额头和阴郁的、麦列霍夫家的小黑眼睛,又是笑,又是哭,没头没脑地小声说着:“我的亲亲的小格里高力呀!我的好孩子呀!我是多么想你呀!你的阿克西妮亚婶婶真傻呀……唉,多么傻呀!”过后她的嘴唇还要哆哆嗦嗦地笑上很久,潮湿的眼睛放射着幸福的光芒,就像一个年轻的姑娘。八月底,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又被征集入伍了。鞑靼村里一切能拿起武器的人都和他同时上了前线。村里的男丁只剩下一些残废人、半大孩子和很老的老头子。这一次是普遍征集,除了严重残废者以外,没有一个人得到体检委员会的免征证明。
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从村长手里接到要他到集合点报到的命令,就匆匆地和老伴儿、孙子、孙女、杜尼娅道别,哼哧哼哧地跪在地上,磕了两个头,对圣像画着十字,说:
“我走啦,我的亲人们呀!看样子,咱们难见面了,恐怕要完啦。我要嘱咐你们的是:你们要连日连夜地打场,要在下雨以前打完。要是来不及,就雇个人,帮你们一下,要是到秋天我不能回来,你们别等我,就自个儿干吧;过冬地能耕多少就耕多少,大麦能种一亩也好。你记住,老东西,要好好干活儿,别松手!不管我和格里高力能不能回来,在你们来说,粮食总是顶要紧的。打仗是打仗,可是没有粮食还是没法活下去。好吧,主保佑你们!”
伊莉尼奇娜把老头子送到广场上,最后看了一眼,看见他正一瘸一拐地和贺里散福一起去追赶大车,然后她就用围裙擦了擦哭肿的眼睛,连头也不回,就朝家里走去。场上还有没打完的小麦,牛奶还在炉子上,孩子们从早晨起来还没有吃过东西,她的操心事还多得不得了,所以她急急忙忙朝家里走着,一停也不停,有时遇到妇女,她就一声不响地打个招呼,也不插嘴说话,如果有熟识的人很同情地问她:“怎么,你去送当兵的来吗?”她也只是点点头。
过了几天,伊莉尼奇娜天一亮就挤过牛奶,把牛赶到胡同里去,刚想朝家里走,就听见一阵低低的、沉沉的轰隆声。她四下里看了看,没看到天上有一点云彩。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轰隆声。
“大嫂子,听见这唱歌的声音了吗?”一个正在集合牛群的老头子问道。
“什么唱歌的声音?”
“就是这老粗的嗓门儿唱的。”
“我听是听见了,可是不明白这是什么声音。”
“你很快就明白了。等他们从河那边朝村子里一开炮,你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在放炮呀。要把咱们的老头子们的五脏六腑都打出来呢……”
伊莉尼奇娜画了一个十字,一声不响地朝家里走去。
从这一天起,炮声连续不停地响了四昼夜。到天亮时候声音特别清楚。但是在刮东北风的时候,就是在中午,也能听得见远处打仗的声音。场院上的活儿有时停一会儿,妇女们想起亲人,小声祷告着,画几个十字,重重地叹几口气,然后石磙又在场院上低沉地轰隆轰隆响起来,孩子们赶着马和牛,风车轧轧响着,一天的劳动照常进行着。八月底的天气分外晴朗,分外干爽。风吹得糠灰满村子乱飞,打过的黑麦麦秸散发着甜丝丝的气味,太阳还有些灼人,但是在各方面都已经可以感觉出,秋天快要到了。牧场上,开过花的灰蒿泛着暗淡的白色,顿河对岸的杨树叶子黄了,果园里的晚熟苹果香味更浓了,遥远的天边已经像秋天那样明朗起来,在割净了庄稼的田野上已经出现了第一批南飞的鹤群。
在将军大道上,天天有拉着军用物资的车队,从西往东,朝顿河的各个渡口奔去,顿河沿岸的许多村庄里已经出现了难民。难民们说,哥萨克边战边退;有些人却说,这种撤退似乎是有预谋的,为的是引诱红军深入,以便加以包围和消灭。鞑靼村里有人悄悄地准备逃难了。他们把牛和马喂得饱饱的,到夜里就挖坑埋粮食和装着金银细软的箱子。一度沉寂的炮声,又重新猛烈地响了起来,而且现在已经很清楚、很凶猛了。战事正在鞑靼村的东北方向进行着,离顿河有四十俄里。过了一天,在西方,在顿河的上游,也响起了炮声。战线以不可抗拒之势朝顿河上移动过来。
伊莉尼奇娜听说村子里大多数人都准备逃难,就叫杜尼娅也走。伊莉尼奇娜觉得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样处置这家业和房屋:是该把这一切都扔掉、跟大家一起逃难呢,还是该留在家里。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在上前线以前,谈到打场、耕地和牲口的事,可是一句也没有提到,如果打到了鞑靼村,家里人该怎么办。为了预防万一,伊莉尼奇娜就这样决定:叫杜尼娅带上孩子们和贵重东西跟着村里人去逃难,她自己留下来看家,即使红军进了村子,她也不离开。
九月十六日夜里,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突然回到了家里。他是从嘉桑镇附近步行回来的,又疲乏,情绪又坏。他休息了半个钟头,就坐上饭桌,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伊莉尼奇娜这一辈子还没见过他这种吃法:把能装半桶的一铁锅素菜汤全灌下去,然后就拼命吃起小米饭。伊莉尼奇娜惊愕得把两手一扎煞,说:
“主啊,你这是怎么吃法呀,老头子!你简直就像是三天没吃饭啦!”
“老东西,你以为我吃过吗?整整三天三夜连一颗米粒儿也没有进口!”
“怎么,不管你们吃饭吗?”
“管他妈的个屁!”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嘴里填得满满的,像猫一样呜噜呜噜地回答说。“搞到什么,就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学会做贼。年轻人干这种事儿都很拿手,他们的良心连两个铜板都不值啦……他们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把做贼的本事学到了家,我觉得稀奇,很稀奇,后来就不稀奇了。他们都是见什么,就拿什么,偷什么,抢什么……这不是打仗,是明火执仗!”
“你别一下子吃得太饱了,可别把肚子撑坏了。瞧你那肚子鼓的,简直像蜘蛛一样啦!”
“住嘴吧。拿牛奶来,用大钵子!”
伊莉尼奇娜看着饿得要死的老头子,都哭了起来。
“怎么,你回来不走了吗?”等老头子吃饱了,把身子向后一仰,她才问道。
“再看吧……”他含含糊糊地回答说。
“大概把你们这些老头子放回家了吧?”
“一个也没有放。红军眼看要打到顿河上来啦,还往哪儿放?我是自个儿跑回来的。”
“这事儿不会有什么麻烦吧?”伊莉尼奇娜担心地问道。
“要是叫他们抓到了,恐怕很麻烦。”
“那你是不是躲一躲呢?”
“你以为我会上游戏场,或者去串门子吗?呸,糊涂透了!”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气得啐了一口,但是老伴儿还是不肯罢休:
“唉,真造孽呀!他们要是把你抓住了,咱们又要大祸临门啦……”
“哼,就叫他们抓去坐监牢吧,比扛着枪在草原上到处跑要好得多,”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无精打采地说,“天天要跑几十俄里,又要挖战壕,又要去冲锋,又要在地上爬,又要躲枪子儿,我受不了!枪子儿他妈的怎么能躲得了呢?我有一个老同事,是曲河那边的人,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左肩下面,连腿也没动弹一下,就完了。干这种事儿实在没什么快活的!”
老头子把步枪和子弹盒都拿出去,藏到糠棚子里,后来老伴儿问他,那件粗呢褂子哪儿去了,他皱着眉头,很不高兴地回答说:
“丢啦。说实在的:扔啦。在叔米林镇外,红军来势很猛,我们把什么都扔掉,像疯子一样跑起来。那时候顾不上什么褂子啦……有的人还穿着小皮袄呢,连皮袄也扔掉啦……你问这干什么,褂子他妈的顶什么用?又不是一件好褂子,是一件叫花子行头……”
其实那是一件很结实的新褂子,但是,凡是他丢掉的东西,照他说来,都是毫无用处的东西。这已经成了他自己安慰自己的习惯。老伴儿知道这一点,因此也没有和他争论褂子的好坏问题。
夜里,在家庭会议上决定:老俩口带着孩子们留在家里,看守家产,把打好的粮食埋起来,叫杜尼娅套上两头老牛,拉着箱子,到旗尔河上拉推舍夫村一个亲戚家去避难。
这项计划没能够全部实现。早晨送走了杜尼娅,可是到了中午,就有一支萨尔斯克的哥萨克和加尔梅克人组成的侦缉队进了鞑靼村。大概,村子里有人看见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回家了;侦缉队进村后有一个钟头,就有四个加尔梅克人骑着马朝麦列霍夫家奔来。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一看见骑马的人,就又麻利又灵活地爬上了阁楼;伊莉尼奇娜出去迎接客人。
“你家老头子在哪儿?”一个上了年纪、身材挺拔、佩戴着上士肩章的加尔梅克人问了一声,就下了马,从伊莉尼奇娜身边朝大门口走来。
“在前线上呢。他还能在哪儿呀?”伊莉尼奇娜很生硬地回答说。
“上屋里去,我要搜一搜。”
“你找什么呀?”
“找你的老头子,哼,真不要脸!这么大岁数啦,还扯谎!”十分神气的上士摇着头说,并且龇出了密密的白牙。
“你别龇牙,脏鬼!告诉你没有,就是没有!”
“少废话,带我们进去!要不,我们就自个儿进去啦。”怒冲冲的加尔梅克人厉声说,并且毅然决然地迈着两只八字脚,大踏步朝台阶走来。
他们到各个房间里仔细看了看,用加尔梅克话商量了一阵子,然后有两个人到院子里去搜,有一个人,个头儿小小的,鼻子扁扁的,一张麻脸黑漆漆的,勒了勒带裤绦的肥大的裤子,走到过道里,伊莉尼奇娜从敞着的门洞里看见,这个加尔梅克人纵身一跃,两手抓住横木,很灵活地翻身上去。过了五分钟,他又很灵活地从上面跳了下来;满身灰土、胡子上粘满蜘蛛网的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也哼哧哼哧、小心翼翼地跟着他爬了下来。他看了看闭紧了嘴的老伴儿,说:
“找到啦,该死的东西!这么看,是有人告密……”
把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押往卡耳根镇,那儿有军事法庭。然而伊莉尼奇娜只哭了几声,就听见重新响起来的炮声和顿河那边清晰可闻的机枪声,便朝仓房里走去,想多多少少藏起一点儿粮食。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