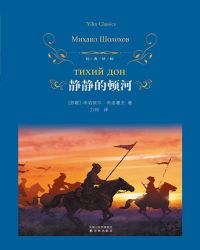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九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九章
战斗在大熊河河口镇附近进行。格里高力从夏天的小路上了将军大道,就听见低沉的炮声。
在大道上到处可以看到红军部队仓促撤退的迹象。扔掉的大小车辆非常多。在马特维耶夫村外的洼地里还扔下一辆炮车,炮轴已经被炮弹打坏,摇架也歪了。炮车上的马套被斜斜地砍断。在离洼地半俄里的一片碱地上,在矮矮的、晒得发烫的草丛里,密密麻麻地躺着许多战士的尸体,都穿着草绿色制服,打着裹腿、穿着笨重的、钉了铁掌的皮鞋。这都是被哥萨克的马队追上来砍死的红军。
格里高力从旁边走过,看到那皱起来的衣服上连成片的干血,看到尸体那横七竖八的样子,很容易就断定了这一点。这些尸体就像割倒的草一样。看样子,只是因为没有停止追击,哥萨克们才没有剥掉他们的衣服。
在一丛山楂树棵子旁边,仰面朝天躺着一个被打死的哥萨克。他那叉得宽宽的裤腿上镶着红红的裤绦。不远处躺着一匹被打死的浅棕色的马,身上还带着一副旧马鞍,鞍架子是上了赭黄色漆的。
格里高力和普罗霍尔的马都走累了。应该喂喂马了,但是格里高力不愿意在不久前发生过战斗的地方停留。他又走了有一俄里,走进一条小峡谷,勒住马。不远处有一个水塘,堤堰已经完全冲坏了。普罗霍尔走到边上的泥土已经干裂的水塘边,但是马上又转了回来。
“你又怎么啦?”格里高力问道。
“你去瞧瞧吧。”
格里高力夹了夹马,走到塘边。冲出的一条沟里躺着一个被打死的女子。她的脸用蓝裙子的下摆蒙着。两条丰满的白腿毫不害羞地叉得宽宽的,腿肚子晒得黑黑的,膝盖上还有窝儿。左胳膊被拧到了脊背底下。
格里高力急忙下了马,摘下帽子,弯下身去,把那女子的裙子拉拉好。那张黑黑的年轻的脸死后还是很美。在疼得弯起来的两道黑眉毛下面,半闭起的两只眼睛还闪着微弱的光。样子很温柔的嘴微微张着,咬得紧紧的两排细牙亮得像珍珠一样。细细的一绺头发遮住紧紧贴在青草上的一边腮帮子。死神已经在腮帮子上投下暗淡的橙黄色阴影,忙忙碌碌的蚂蚁正在上面爬。
“狗崽子们害死一个多么漂亮的娘们儿!”普罗霍尔小声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狠狠地啐了一口。
“我要把这些……得便宜的家伙都枪毙!天啊,咱们快离开这儿吧!我不能再看她。我心里受不了!”
“咱们是不是把她埋了?”格里高力问。
“咱们怎么,要包埋所有的死人吗?”普罗霍尔生气了。“在亚戈德庄上埋了一个老头子,到这儿又要埋这个娘们儿……咱们要是见了死人就埋,手上的趼子还不知要磨多厚呢!再说,拿什么来挖坟呢?老兄,马刀可是挖不出坟的,这土地晒硬有一俄尺厚。”
普罗霍尔急急忙忙上马就走,靴尖好不容易插进马镫。
他们又走上高地,这时候,一个劲儿想着心事的普罗霍尔问道:
“怎么样,潘捷莱维奇,流血还没有流够吗?”
“差不多啦。”
“你的意思是说,这仗快打完了吗?”
“等他们把咱们打败了,就算是打完啦……”
“这么一来,快活日子就到啦,就他妈的高兴高兴吧!就叫他们快点儿把咱们打败吧。以前在俄德战争时候,有人不愿当兵,砍断自己一根手指头,就把他放回家啦,可是如今,就是把一只手砍掉,还是要当兵。一只手的都要,瘸子也要,独眼龙也要,害小肠的也要,什么样的家伙都要,只要两条腿能走动就行。难道这场仗能随随便便结束吗?这些人他妈的统统都会被打死!”普罗霍尔灰心绝望地说;他走下大路,下了马,小声嘟哝着,动手解马肚带。
夜里,格里高力来到离大熊河口镇不远的河湾村。第三团布置在村边上的岗哨拦住了他,但是哥萨克们从声音上辨别出是自己的师长后,就回答格里高力的问话说,师部就驻扎在这个村子里,参谋长考佩洛夫中尉正在焦急地等着他呢。喜欢说话的哨长还派一个哥萨克送格里高力上司令部去;最后又说:
“他们筑的工事太结实啦,格里高力·潘捷莱维奇,恐怕咱们不能很快把大熊河口拿下来。以后,当然,谁又知道呢……咱们的兵力也很充足嘛。听说,好像英国军队从莫罗佐夫斯克开来啦。您没有听说吗?”
“没有。”格里高力夹了夹马,回答说。
师部占用的房子的所有护窗都关得紧紧的。格里高力以为房子里没有人,但是一进走廊,就听见低沉而热烈的说话声。他从黑漆漆的夜幕下走进上房里,天花板上的一盏大灯照得他的眼睛发花,浓烈呛人的黄烟烟气往鼻子眼儿里直钻。
“你到底来啦!”考佩洛夫从缭绕在桌子上方的灰色烟云中钻出来,高兴地说。“老兄,我们等你等得急死啦!”
格里高力和在场的人打过招呼,脱掉大衣,摘下帽子,朝桌边走去。
“瞧你们抽的这烟气!叫人连气都不能喘啦。你们把窗子关得死死的,哪怕开开一扇也好呀!”他皱着眉头说。
坐在考佩洛夫旁边的哈尔兰皮·叶尔马柯夫笑着说:
“我们闻惯了,就不觉得啦。”他用胳膊肘捣破窗玻璃,使劲把护窗推开。
一股新鲜的夜间空气冲进屋子。灯火亮了一下,就灭了。
“太不爱惜东西啦!干吗你要把玻璃捣破?”考佩洛夫不满意地说,一面在桌上摸索着。“谁有火柴?小心点儿,地图旁边有墨水。”
点上灯,又关上一扇护窗,于是考佩洛夫急急忙忙开口说:
“麦列霍夫同志,今天前线上的情况是这样:红军在坚守大熊河口镇,从三面掩护这个镇,兵力大约有四千人。他们的大炮和机枪都很多。他们在教堂附近和别的许多地方都挖了战壕。顿河旁边的一些高地全叫他们占住了。就是说,他们的阵地虽然不能说是铁打的,但无论如何也是很难攻破的。咱们这方面,除了菲次哈拉乌洛夫将军的一个师和两支军官突击队以外,全部开到的就是包加推廖夫的第六旅和咱们第一师了。不过咱们师还未到齐,步兵团还没有到,这个团还在霍派尔河口镇附近,骑兵倒是全到啦,不过各连的人数都差得太多。”
“比如说,我这一团的第三连只有三十八个哥萨克。”第四团团长杜达列夫准尉说。
“以前呢?”叶尔马柯夫问道。
“以前有九十一人。”
“你怎么能容许解散一个连呢?你算是个什么团长?”格里高力皱着眉头,用手指头敲着桌子,问道。
“谁他妈的能拦住他们?他们都回村子看自己的家去啦。不过现在正陆续归队,今天就回来三个。”
考佩洛夫把地图推到格里高力面前,用小指头指着各部所在的位置,继续说:
“咱们还没有发起进攻。只有咱们的第二团昨天在这个地段徒步进攻了一下,但是失败啦。”
“损失大吗?”
“根据团长的报告,他手下昨天共伤亡二十六人。要说双方的兵力,那我们是占优势的,但是我们的机枪少,炮弹不够,无法掩护步兵进攻。他们的军需处长答应过,只要一运到,就拨给咱们四百发炮弹、十五万发子弹。可是什么时候才能运到呀!但是明天就要进攻,这是菲次哈拉乌洛夫将军的命令。他要我们拨一个团去支援突击队。他们昨天冲锋了四次,受的损失很大。打得非常激烈!所以,菲次哈拉乌洛夫提出要加强右翼,把进攻的重点转移到这儿来,看见吗?这儿地势好,可以在一百到一百五十丈距离内接近敌人的战壕。哦,他的副官刚刚才走。他是来传达口头通知,叫咱们明天早上六点钟去开会,商谈共同行动的问题。菲次哈拉乌洛夫将军和他的师部现在就驻扎在大谢宁村。总的目的是,要在敌人的援军从谢布里亚科沃车站开到以前,迅速把敌人打垮。在顿河那边,咱们的军队推进得不怎么快……第四师渡过了霍派尔河,但是红军派出强大的阻截部队,死死地拦住去铁路线的道路。现在红军在顿河上搭了一座浮桥,正在匆匆忙忙从大熊河口镇往外运弹药和武器。”
“哥萨克们都在说,好像协约国的军队开来啦,是真的吗?”
“是有消息说,英国的几支炮兵连和好几辆坦克从车尔尼雪夫镇开来啦。不过有一个问题:他们怎么能让这些坦克渡过顿河呢?依我看,关于坦克的话是谣言!坦克的事已经说了很久了嘛……”
上房里静了老半天。
考佩洛夫解开深棕色的军官制服,用两手托住长满栗色胡楂子的鼓鼓的两腮,若有所思地衔着已经熄灭的纸烟吧咂了半天。他那两只离得很远的、圆圆的黑眼睛疲倦得眯缝起来,因为连夜不能睡觉,他那张很漂亮的脸显得十分憔悴。
考佩洛夫以前是教区小学的教员,星期天就到买卖人家里去串串门儿,和女主人调调情,和买卖人打打小牌,弹吉他弹得很好,是一个又风流又随和的年轻小伙子;后来和一个年轻女教员结了婚,本来可以这样在镇上生活下去,一直干到退休,但是战争一来,征集他去服兵役了。他在士官学校毕业以后,被派到西部战线一个哥萨克团里去了。战争没有改变考佩洛夫的性格和外表。他那矮矮的、胖乎乎的身材,那张和善的脸,那挎刀的姿势,他对待下级的态度,都流露着和蔼可亲和很容易接近的意味。他的声音中没有生硬的命令口气;说起话来不像很多军人那样干巴巴的;军服穿在他身上,显得又肥又大;他在战场上过了三年,一直都没有学会那种挺胸傲立的姿势;他身上的一切,都显示着他是一个偶然来到战场上的人。他不大像一个真正的军官,倒像一个穿了军官服的肥胖的普通人,但是,尽管是这样,哥萨克们却都很尊重他,在师部的会议上大家都很注意听他的话,暴动军的指挥官们都很看重他的清醒的头脑、谦逊的性格和那种平时不外露、但在战斗中不止一次表现出来的勇气。
在考佩洛夫以前,格里高力的参谋长是一个不识字也没有本事的少尉克鲁希林。他在旗尔河上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于是考佩洛夫担任了参谋长,把事情办得稳稳当当,清清楚楚,井井有条。他坐在师部里制订作战计划,就像当年批改学生作业那样,又认真又细致,但是在必要的时候,只要格里高力说一声,他就扔下师部的工作,骑上马去,指挥起一个团,带领这个团去作战。
格里高力起初对新参谋长有些偏见,但是过了两个月,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有一次打过仗以后,格里高力很直率地说:“考佩洛夫,我以前把你想得很坏,现在我看出来,是我错啦,请你多多原谅。”考佩洛夫笑了笑,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是他听了这粗率的表白,显然非常高兴。
考佩洛夫不想升官发财,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政治见解,他把战争看做无法逃脱的灾难,也不指望战争结束。就是现在,他也根本不考虑如何去攻占大熊河口镇,而是想起家里人,想起家乡,心想,能够请上个把月的假回家去看看,倒也不坏……
格里高力看了考佩洛夫半天,后来站了起来。
“好啦,各位长官弟兄们,咱们各自去睡觉吧。怎样拿下大熊河口的问题,用不着咱们伤脑筋。现在有将军们替咱们考虑和决定问题啦。明天咱们上菲次哈拉乌洛夫那儿去,叫他来教导教导咱们这些可怜虫呢……至于第二团,我是这样想的:既然咱们现在还有权,马上就把杜达列夫团长降级,取消他的一切军衔和勋章……”
“还要取消他的一份伙食。”叶尔马柯夫插嘴说。
“不行,别开玩笑,”格里高力继续说,“马上就把他降为连长,派哈尔兰皮去担任团长。叶尔马柯夫,你马上就去,把这个团接下来,明天早晨等候我们的命令。撤换杜达列夫的命令马上由考佩洛夫写好,你随身带去。我看,杜达列夫不干了。他妈的他什么都不懂,别叫他再带着哥萨克去挨打啦。步兵作战就是这么回事儿……如果团长是个饭桶,就很容易损失人。”
“很对。我赞成撤换杜达列夫。”考佩洛夫表示支持。
“你怎么,叶尔马柯夫,你反对吗?”格里高力看出叶尔马柯夫脸上有一点儿不高兴的神气,就问道。
“没有呀,我没有什么。我连眉毛都不能动动吗?”
“那就好。叶尔马柯夫不反对。他的骑兵团暂时交给里亚布契柯夫。米海依洛·格里高黎奇,你写好命令,就睡吧。六点钟就要起床。咱们上那位将军那儿去。我要带四名传令兵。”
考佩洛夫惊愕得扬起眉毛,说:
“干吗要带这么多传令兵?”
“壮壮声势呗!咱们也不是草包,也带领着一师人嘛。”格里高力笑着耸了耸肩膀,披上大衣,就朝门口走去。
他在棚子底下铺上马衣,没有脱靴袜,也没有脱大衣,就躺了下来。院子里有几个传令兵嚷嚷了很久,不远处有几匹马打着响鼻,有规律地咀嚼着。可以闻到干马粪的气味和白天晒热了、现在还没有冷下去的土地气味。格里高力矇眬中听见传令兵们的说话声和笑声,听见其中有一个,从声音上判断,是个年轻小伙子,一面上马鞍,一面叹着气说:
“唉,伙计们,真够戗啊!深更半夜里,还要送公文,觉又睡不成,又不得安宁……你给我站好,鬼东西!抬腿!把腿抬起来,鬼东西!……”
另外有一个传令兵用低沉的伤风嗓门儿小声唱了几句:
“当兵这事儿,叫我们厌透啦,烦透啦。把我们的骏马折腾够啦……”又改用普通的急促的央求腔调说:“普罗霍夫,给点儿烟末子吧!你真是小气鬼!我在别拉文还送你一双红军的皮鞋呢,你忘啦?你这家伙!要是别人得到这样的皮鞋,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是你连一把烟末子都舍不得!”
马嚼子在马牙齿当中丁丁当当直响。那匹马尽力吸了一口气,便朝前走去,马掌踩在像石头一样干硬的土地上,发出清脆的嘚嘚声。“大家都在说呢……当兵的事儿,叫我们厌透啦,烦透啦。”格里高力微微笑着,重复了一遍,马上就睡着了。他一睡着,就做起梦来,这样的梦他以前也做过的:红军的散兵线在褐色的田野上,踩着高高的庄稼茬子前进。最前面一道散兵线长得看不到头。后面还有六七道散兵线。在一片使人焦急的寂静中,进攻的人越走越近了。一个个黑色的人影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已经可以看见,许多头戴双耳皮帽的人一声不响地张着嘴,跌跌撞撞地快步往前进,前进,渐渐进入射程以内,就端着枪跑起来。格里高力躺在一个不深的掩体里,慌慌张张地扳着枪栓,不停地放枪;一个个的红军被他打得仰面朝天倒下去;他又压上一梭子,这时候朝两边看了一下子,就看见:哥萨克们纷纷从旁边的许多掩体里跳出来。他们转身就跑,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格里高力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厉害,他吆喝道:“开枪啊!浑蛋!往哪儿跑?!站住,别跑!……”他使足了劲儿吆喝,但是他的声音出奇地微弱,勉强能听见。他真吓坏了!他也跳起来,站着对一个一声不响地对直朝他冲来的不算年轻的黑脸膛红军放了最后一枪,他看到,这一枪打空了。那个红军的脸上一副激动而严肃的神情,毫无畏惧之色。他跑得十分轻快,几乎是脚不沾地,两道眉毛拧在一起,帽子戴在后脑勺上,掖着军大衣的下摆。格里高力对着跑来的敌人打量了一下子,看到他那炯炯的眼睛和生满拳曲胡楂子的苍白的脸,看到他那肥大的短筒靴子,看到微微朝下的黑黑的枪口和随着奔跑晃来晃去的枪上的黑黑的刺刀尖儿。格里高力害怕得不得了。他扳了扳枪栓,但是枪栓不灵了,卡住了。格里高力把枪栓拼命在膝盖上磕,一点用也没有!那个红军离他只有五步远了。格里高力转身就跑。在他前面,整个光秃秃的褐色田野上,到处是乱跑的哥萨克。格里高力听见在后面追赶的红军的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听见红军的冬冬的脚步声,他想跑快些,却跑不快。要想叫两条发软的腿跑快些,要拼命使劲才行。终于,他跑到一处破败的、凄凉的坟地边,跳过倒塌的围墙,在塌陷的坟堆、歪斜的十字架和神龛中间跑着了。再加一把劲儿,就脱离危险了。但是这时候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后面的红军喘的气吹得格里高力的脖子热乎乎的,就在这时候,他觉得红军揪住了他的军大衣的扣带和衣襟。格里高力低沉地喊了一声,就醒了过来。他仰面躺着。他的两只穿着瘦靴子的脚麻木了,额头上出了冷汗,浑身疼痛,就像挨了打一样。“呸,他妈的!……”他沙哑地说;很高兴地听着自己的声音,还不相信刚才他经历的一切是一个梦。后来他翻了一下身,侧着身子躺着,用军大衣连头蒙住,在心里说:“应该把他放到跟前来,给他一家伙,用枪托子把他打倒,然后再跑……”他把再度出现的梦境思索了一会儿,感到一阵高兴,因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噩梦,而在现实中目前他还没有受到什么威胁。“真怪,为什么梦里的情景要比现实可怕十倍?虽然过去多次遇到危险,但是还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可怕呢!”他心里想着,舒舒服服地伸了伸麻木的腿,渐渐睡着了。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