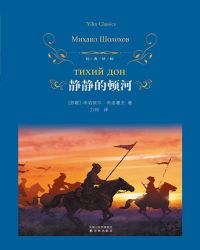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一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卷五|
第一章
一九一七年深秋,哥萨克们陆续从前方回家来了。苍老了的贺里散福和跟他一起在五十二团当兵的哥萨克一同回来了。炮兵托米林·伊万和“马掌”亚可夫、依旧是光脸蛋子的安尼凯回来了,他们纯粹是退伍回来的;紧跟着回来的是马尔丁·沙米尔、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查哈尔·柯洛列夫和高得出格的鲍尔晓夫;十二月里,米佳·柯尔叔诺夫突然出现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十二团的哥萨克回来了一大帮,其中有米沙·柯晒沃依、普罗霍尔·泽柯夫、卡叔林老汉的儿子安得列·卡叔林、叶皮番·马克萨耶夫、叶戈皮·西尼林。
有点像加尔梅克人的菲多特·包多甫斯柯夫行军中掉了队,就骑着一匹从奥地利军官手里夺来的非常漂亮的黄骠马,直接从沃罗涅日回家来了,后来他夸马夸了很久,说是全亏了这匹马跑得快,才从已经闹起革命的沃罗涅日省的一个个村子里跑了过来,才从一支支赤卫队的鼻子底下逃脱了。
在他之后,梅尔库洛夫、彼特罗·麦列霍夫和尼古拉·柯晒沃依也从卡敏车站上回来了,他们是从布尔什维克化了的第二十七团里跑出来的。他们给村子里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是目前在第二后备团当差的格里高力·麦列霍夫已经投靠了布尔什维克,留在卡敏镇上了。一向不务正业的偷马贼马克西姆·戈里亚兹诺夫也在那里的二十七团里干起来了,他所以喜欢布尔什维克,是因为对天下大乱感到新鲜,能够无拘无束地过日子,据说他弄到一匹马,那马丑得惊人,可是腿脚也快得惊人;据说他那匹马有一道银白色的毛穿过整个脊背,就像一条天生的背带,那马个头儿不高,但是身子很长,毛简直跟牛毛一样红。大家都不怎么谈格里高力的事,都不愿意谈他,因为都知道他已经和村里的人分道扬镳,至于今后还能不能重新走到一块儿,那很难说。
许多哥萨克回到家里,是主人,也是久盼的客人,这些人家就欢天喜地。这种欢乐尤其尖利无情地挑动了那些丧失亲人的人已经受惯了的隐痛。有很多哥萨克不在了,他们死在加里西亚、布柯维纳、东普鲁士、罗马尼亚和喀尔巴阡山区的土地上,横尸田野,在大炮的哀悼声中烂掉,如今一座座高大的合葬坟已经长满荒草,任凭雨打,任凭雪花覆盖。不戴头巾的娇妻不管多少次跑到胡同口,手搭凉棚张望,心上人再也回不来啦!肿胀失神的眼睛不管淌多少眼泪,都冲不掉思念亲人的苦!在生日和忌日里不管怎样失声痛哭,东风也无法把她们的哭声送往加里西亚和东普鲁士,无法送到一座座合葬坟塌陷的坟头上!……
青草会掩没坟墓,时间会掩没痛苦。清风已经舔净出征人的脚印,时间也会舔净那些没有回来、而且永远也不会回来的人留下的痕迹,因为人的一生是短促的,我们每个人能践踏的青草都不多……
可是现在,普罗霍夫·沙米尔的老婆眼看着去世的丈夫的二哥马尔丁·沙米尔回到家里,跟自己的怀孕的老婆亲亲热热,哄着孩子玩儿,并且给孩子们带回礼物,她就拿头在硬邦邦的地上乱撞,拿牙齿啃黄土地。这娘们儿拿头撞着地,全身抽搐着在地上到处爬,孩子们就像羊群一样在旁边挤成一堆,用吓得瞪圆了的眼睛望着妈妈,大声哭号着。
好娘们儿呀,任凭你把仅有的一件小褂领子扯烂吧!任凭你撕扯因为生活艰难、没有欢乐而变得稀稀拉拉的头发,任凭你咬你那已经咬得出血的嘴唇,任凭你捶折到处是老茧的手臂,任凭你在空房门口的土地上撞头吧!反正你的房子里没有男主人啦,你再也见不到丈夫啦,你的孩子们再也见不到爹啦;你记住,再也没有谁来疼你和你的孩子们啦;你干活儿劳累,生活贫苦,再也没有谁来管啦;夜里你累得倒下来,再也没有谁把你的头搂到怀里,再也没有谁像他以前那样对你说:“别发愁,阿妮西卡!咱们的日子会好起来的!”今后永远不会有人爱你啦,因为干活、贫穷、孩子已经把你榨干,使你变呆啦;你那些光屁股的不懂事的孩子永远不会有爹啦;你要自己耕地和耙地,自己累得气喘吁吁地把一大抱一大抱的小麦从割麦机上往下卸,又用叉子叉起来往大车上装,就会觉得肚子下面有什么东西直翻腾,于是你就抱住头抽搐起来,血从下面直往外流。
阿列克塞·别士尼亚克的老妈妈一面翻弄儿子的旧衣服,一面哭,滴着痛苦的、已经不多的眼泪,闻着,但只有米沙·柯晒沃依带回来的最后一件衬衣的褶缝里还保留着她儿子的汗味,于是老人家就把头俯到这件衬衣上,摇晃着身子,用哭诉的腔调念叨着,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印着号码的肮脏的棉布衬衣上。
马内次柯夫、阿丰卡·奥捷洛夫、叶甫兰琪·加里宁、李霍维多夫、叶尔玛柯夫和另外一些哥萨克的家里也只剩了孤儿寡妇。
只是司捷潘·阿司塔霍夫没有谁来哭,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人了。他的房子空空的,门窗钉得死死的,不少地方已经坏了,即使在夏季里,也显得阴森森的。阿克西妮亚住在亚戈德庄上,村子里仍然很少听到她的消息,她也没有到村子里来过,看样子,她不想念这个村子。
顿河上游各乡的哥萨克,都一个乡一个村的结成伙儿,纷纷回家来了。到十二月里,维奥申乡各村在前方的人,几乎全部回到了家里。
白天和黑夜都有人骑马从鞑靼村里经过,人数从十几个到四十多个不等,成群成伙地朝顿河左岸走去。
“老总们,从哪儿来?”老头子们走出门来,问道。
“从黑河上。”
“从吉莫夫纳亚。”
“从杜布洛夫卡。”
“从列舍托夫斯柯依。”
“我们是杜达廖夫乡的。”
“我们是郭洛霍夫乡的。”
“我们是阿里莫夫乡的。”过路的人纷纷回答。
“怎么,打仗打够啦?”老头子们带着挖苦的语气问道。
有些哥萨克很忠厚、很老实,就笑着回答说:
“够啦,老大爷!我们打仗打够啦。”
“受罪受够啦,现在回家啦。”
那些愣头愣脑、脾气不好的,就张口骂人,说:
“你给我滚,老家伙,把尾巴收起来吧!”
“你问这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你们这些老家伙少管闲事!”
冬天就要结束的时候,诺沃契尔卡斯克附近已经出现了内战的苗头,但是在顿河上游的乡村里,依然十分平静。只是在一些人家里时常发生隐秘的、有时也暴露到外面来的家庭纠纷:老头子们和前方归来的人闹意见。
关于顿河军区首府附近的战事,大家只是听到一些传闻;大家模模糊糊地判断着政治形势,等候着事态发展,听着消息。
在一月以前,鞑靼村里的日子过得很太平。前方回来的哥萨克们,都躺在老婆身边睡大头觉,吃得胖胖的,并没有觉察到新的灾难和困苦已经等候在家门口,这新来的还要超过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所遭受到的。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