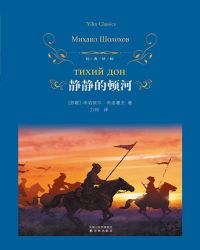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六十五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六十五章
五月十九日,第九军清剿旅的参谋长古曼诺甫斯基派米沙·柯晒沃依到三十二团团部去送紧急公文。根据古曼诺甫斯基得到的情报,该团团部驻扎在郭尔巴托夫村。
这一天傍晚时候,米沙来到郭尔巴托夫村,但是三十二团团部不在这里。村子里塞满了第二十三师的二类辎重队的许多车辆。这些车辆是从顿涅茨方面来,由两连步兵掩护着,朝大熊河河口方面去的。
米沙在村子里转悠了几个钟头,想打听出三十二团团部驻扎的地方。最后有一个红军骑兵告诉他,三十二团团部昨天驻扎在叶甫兰琪耶夫村,就在博柯夫镇旁边。
米沙喂了喂马,连夜赶到叶甫兰琪耶夫村,可是团部也不在这里。已经过了半夜,米沙在回郭尔巴托夫村的路上,在草原上碰上一支红军的侦察队。
“什么人?”他们老远就对米沙喝问道。
“自己人。”
“哼,你算什么自己人……”头戴白色库班帽、身穿蓝褂子的队长朝跟前走来,用伤风的哑嗓门儿低声说。“哪一部分的?”
“第九军清剿旅。”
“有部队的证件吗?”
米沙掏出证件。侦察队长一面借着月光仔细看那证件,一面带着不信任的口气盘问道:
“你们的旅长是谁?”
“是罗佐甫斯基同志。”
“现在你们旅在哪儿?”
“在顿河那边。同志,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是三十二团吗?”
“不是。我们是三十三库班师。你这是从哪儿来?”
“从叶甫兰琪耶夫村来。”
“上哪儿去?”
“上郭尔巴托夫村。”
“噢!郭尔巴托夫村现在住上哥萨克啦。”
“不可能!”米沙惊愕地说。
“我对你说,那儿是住上哥萨克叛匪啦。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我怎么能过得了郭尔巴托夫村呢?”米沙惊慌失措地说。
“那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侦察队长催动他那溜屁股的大青马,朝前走去,但是后来在马上侧转过身子,劝道:
“你跟着我们走吧,要不然他们会砍掉你的脑袋。”
米沙高高兴兴地跟着侦察队走了。当天夜里他跟着侦察队一起来到克鲁日林村,第二九四塔干罗格团驻扎在这里,他把公文交给团长,向他说明为什么没有能够将公文送交指定的部队以后,就要求留在团里参加骑兵侦察队。
第三十三库班师是不久前由塔曼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和一些志愿参军的库班人编成,从阿斯特拉罕开到沃罗涅日——里斯基地区来的。其中的一个旅,即塔干罗格团、杰尔宾特团和瓦西里柯夫团组成的旅,被调来镇压暴动。这个旅猛扑麦列霍夫的第一师,将该师赶过了顿河。
这个旅边打边进,以强行军的速度顺着顿河右岸一直从嘉桑乡推进到霍派尔河口乡西边的一些村庄,以右翼占领了旗尔河边的一些村庄,在顿河沿岸停留了两个星期之后,这才转回头来。
米沙参加了进攻卡耳根镇和旗尔河边许多村庄的战斗。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在下格鲁申村外的草原上,第二九四塔干罗格团的第三连连长,让战士们在路边站好队,宣读了刚刚接到的命令。于是米沙·柯晒沃依牢牢地记住了一些话:“……一定要摧毁那些无耻的暴徒和叛贼的巢穴。一定要把那些恶魔彻底消灭……”还有:“对付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帮凶们,要用铅弹、钢铁和火!”
自从施托克曼被杀害以后,自从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和叶兰乡的共产党员们牺牲的消息传到米沙的耳朵里,米沙心里对哥萨克痛恨到了极点。只要有被俘的暴动的哥萨克落到他手里,他再也不加考虑,再也不听那嘟嘟哝哝的哀告声。从那时候起,他没有宽待过一个俘虏。他用蓝蓝的、冷得像冰一样的眼睛看着同乡的哥萨克,问:“你和苏维埃政府打仗打够了吗?”也不等回答,也不去看俘虏那惨白的脸,就把他劈了。他杀起人来毫不留情!他不仅要杀人,还要把“红公鸡”放进暴动军放弃的村庄里的房子。等到吓得发了疯的公牛和母牛冲过着了火的牲口院子篱笆,吼叫着朝胡同里跑去的时候,米沙就对牛开枪。
他同哥萨克的富裕,同哥萨克的背信弃义,同几百年来在那些高大房屋里养成的顽固守旧的生活方式,进行着毫不妥协的、无情的斗争。他的仇恨是施托克曼和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的死激起来的,命令上的话只是清清楚楚地说出了米沙没有说出的心情罢了……就在这一天,他和三个同伴把卡耳根镇上的房子烧掉了一百五十多座。他在一家商店的仓库里弄到一桶煤油,用一只黑黑的手攥着一盒火柴,就在广场上转悠起来,他经过哪里,哪里就冒起苦烟和火焰,那些镶了木板、上了油漆、富丽堂皇的商人和神甫的房子、富裕哥萨克的房子,那些“用欺骗煽动愚昧的哥萨克群众掀起叛乱”的人的住宅,就笼罩在一片火海里。
骑兵侦察队总是首先进入敌人抛弃的村子的;不等步兵开到,米沙已经点着了那些最漂亮的房子。他想无论如何要到鞑靼村去,为了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和叶兰乡共产党员的死,要找村里人报仇,要烧掉半个村子。他已经在心里拟定了一份该烧的人家的名单,万一他的部队从旗尔河边向维奥申左面进军的话,他决定在夜里单独行动,想方设法要到自己村子里去一趟。
他一定要回鞑靼村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近两年来,因为时常和麦列霍夫家的杜尼娅见面,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用言语说不出的感情。杜尼娅那黑黑的手指头用彩线给米沙绣烟荷包,她在冬天里瞒着家里人送给他一副灰羊毛手套,当初杜尼娅用的一条绣花手绢,米沙还小心翼翼地藏在军便服的胸前口袋里。这条小小的手绢,三个月来在皱褶里一直还保留着隐隐约约、像干草气味一样的姑娘身体气味,他觉得说不出的可亲可爱!每当他独自一人单独掏出手绢来的时候,总要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使他无法平静的情景:井边一棵挂满霜雪的白杨,昏沉的天空飘舞着雪花,杜尼娅的线条清晰、哆哆嗦嗦的嘴唇,在她那弯弯的睫毛上慢慢融化的雪花闪烁着宝石一般的亮光……
他为回家做了精心的准备。他在卡耳根镇上,从一个商人家的墙上扯下一条花毯子,做了马衣,这马衣真是漂亮得出奇,那鲜艳无比的各种色彩和花纹老远就使人眼花缭乱。从一个哥萨克家的柜子里弄到一条带裤绦的、几乎全新的马裤,弄到六条女人披巾,可以做三副包脚布,还有一副女人的线手套,他暂时放进鞍袋里,因为目前在灰暗的打仗的日子里不能戴,要等到快进鞑靼村的时候才戴。
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传统:当兵的人回到村子里,一定要穿戴得漂漂亮亮的。米沙还没有摆脱哥萨克的传统,尽管他当了红军,还是一心一意想保持旧日的风尚。
他骑的是一匹白鼻子、枣红色的好马。马原来的主人是霍派尔河口镇的一个哥萨克,米沙在冲锋时把他劈死了。这马就是米沙的了。这马是一匹值得夸耀的马:不论身材、速度、步伐、姿势,都没有说的。可是米沙的马鞍却很不像样子。鞍垫已经磨坏,而且已经打了补丁,后肚带是生皮做的,马镫长满了陈锈,擦都擦不掉。马辔头也十分寒碜,一点装饰也没有。要想想办法,即使装饰一下辔头也好。米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苦苦思索了很久,终于,他想出一个很好的主意。就在广场上,一座商人的房子旁边,放着一张白镍床,这是商人家的仆人从着火的房子里抢出来的。床的四角有四个白球儿,经阳光一照,亮得耀眼。只要把这几个球儿拆下来或者砸下来,然后往辔头上一挂,辔头就大不一样了。米沙就这样做了:他把四个空心的白球儿从床角上拧下来,用丝带把四个球儿拴到辔头上,两个拴在马嚼子的环儿上,两个拴在鼻带两旁,于是白球儿就像白亮的中午太阳一样,在马头上放起光来。阳光一照,亮得刺眼!马只要迎着太阳走,就要眯起眼睛,踉踉跄跄,连步子都不敢迈。但是不管马眼睛被白球儿的反光照得多么难受,不管马眼睛被刺得流多少眼泪,米沙连一个球儿也不肯从马辔头上摘下来。不久就到了从烧毁了一半、到处散发着焦糊的砖味和灰烬气味的卡耳根镇出发的时候。
这个团要朝顿河,朝维奥申方面去。所以米沙没有费什么事就向侦察队长请准了一天的探亲假。
队长不仅准了他的短期假,还特意关照他:
“娶老婆没有?”他问米沙。
“没有。”
“有野花儿吧?”
“什么野花儿?……这是什么意思?”米沙惊愕地问道。
“就是相好的嘛!”
“噢——噢……这倒是没有。有一个爱人,是一个清白的姑娘。”
“你有怀表吗?”
“没有,同志。”
“你呀,真是!”侦察队长是个斯塔夫罗波尔人,以前是个超期服役的中士,在旧军队时不止一次请假回家,根据切身经验他知道,穿得破破烂烂地回家,滋味是不好受的。于是他从宽宽的胸膛上摘下怀表和老粗的表链,说:“你是个好战士!给你,戴上回家去,让姑娘们瞧瞧,只要记住我就行啦。我也有过年轻时候,也坏过几个大姑娘,玩过一些娘们儿,我知道……这链子是新的美国金的。如果有人要问,你就这样回答。如果有人死缠住不放,要问成色戳子在哪儿,你干脆就打他嘴巴子!是有那么一些厚脸皮的家伙,对这些家伙就是要打嘴巴,没有什么好说的。过去,在饭馆里或者在窑子里,要是从哪儿跑来一个当店伙或者当账房先生的酸文人,想当众羞辱我,说:‘把链子挂在肚子上,倒像是真金的哩……那么请问,这链子上的成色戳子在哪儿?’我从来就不给他想一想的工夫,就说:‘成色戳子吗?这就是!’”米沙的好心肠的队长攥起像小孩子脑袋一样大的棕褐色拳头,用老大的猛劲儿抡了抡。
米沙挂好怀表,夜里就着火堆的亮光刮了刮脸,备上马,骑上马就走。黎明时候他进了鞑靼村。
村子依然是原来的样子:砖瓦教堂的低矮的钟楼依然伸着退了色的镀金十字架,直指蓝天,村里的大操场上依然挤满了买卖人家和神甫家的一座座牢固的房子,米沙家快要倒塌的小屋边的白杨树依然在小声说着亲切的话儿……
使他吃惊的,只有那村子里一向少有的一片死沉沉的寂静,寂静像蛛网一样笼罩住大街小巷。街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家家的护窗都关得紧紧的,有些人家的门上挂着锁,但是大多数人家的门都大敞着。好像是瘟疫用它那黑脚在村子里走了一遍,带走了所有的院落和街道上的人,把空旷和死寂填进了住人的地方。
听不见一点人声,也听不见牲口叫声和公鸡打鸣声。只有一些麻雀,好像在大雨要来时那样,在棚檐底下和干柴禾堆上很起劲地叫着。
米沙走进自己家的院子。家里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他。进过道的门大敞着,门口有破烂的红军裹腿,血糊糊、皱皱巴巴的绷带,落满了苍蝇、已经臭了的鸡头和鸡毛。看样子,几天以前有红军在这里吃过饭:地上还有破瓦钵子碎片、啃光的鸡骨头、烟头、踩烂的报纸……米沙压制着沉重的叹息,走进房里。房里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只有每年秋天储存西瓜的地下室的门好像开了一点缝儿。
米沙的妈妈还喜欢背着孩子们,把苹果干儿藏在地下室里。
米沙想起这样的事,便走到地下室小门跟前。他心里想:“妈妈会不等我回来吗?也许,她给我留下什么呢?”他于是抽出马刀,用刀尖把小门一撬。小门吱嘎一声开了。从地窖里冒出一股潮气和霉气。米沙蹲下身子。他的眼睛因为不习惯黑暗,老半天什么都看不清楚,到最后才看见:在铺开来的一块旧桌面上,放着半瓶酒,一个平底锅里还盛着发了霉的煎鸡蛋,还有一块面包,已经被老鼠吃掉了一半;还有一只瓦壶,用一个木碗盖得严严的……这是老人家在等待儿子。就像是等待最高贵的客人!米沙走下地下室的时候,他的心因为沉浸在疼爱和欢喜里,激动得哆嗦起来。这些整整齐齐地摆在干干净净的旧桌布上的东西,都是妈妈那操劳的手在几天以前抚摩过的呀!……这儿的橛子上还挂着一个白白的麻布袋。他急忙把麻布袋摘下来,看见里面是他的一套衬衣,衬衣是旧的,但是缝补得整整齐齐,洗得干干净净。
老鼠已经把吃的东西啃得乱糟糟的,只有牛奶和酒没有动过。米沙喝完了酒和在地下室里放得格外凉的牛奶,拿起衬衣,爬了出来。
妈妈大概也到顿河那边去了。“她不敢留下来,这样也好,不然的话,哥萨克一定会打死她的。就这样,恐怕因为我的事,已经把她折腾得够戗啦……”他这样想着,放慢脚步,走了出去。他解开马,但是没有敢上麦列霍夫家去:他们家就在顿河边上,任何一个枪法好的射手都可以在对岸用暴动军的无壳铅弹把米沙打倒。所以米沙决定先上柯尔叔诺夫家去,到黄昏时候再回到广场上,趁着天黑,把莫霍夫家和其他买卖人家以及神甫家的房子烧掉。
他从后面来到柯尔叔诺夫家宽大的院子跟前,走进敞着的大门,把马拴在栏杆上,正要朝屋里走,恰好格里沙加爷爷来到台阶上。他那雪白的头打着颤,老花的眼睛像瞎子一样眯缝着。那油糊糊的领口上还钉着红领章的、挺结实的哥萨克灰制服扣得整整齐齐的,但是那肥大的裤子老是往下掉,所以老头子不住地用手往上提。
“你好,老人家!”米沙摇晃着鞭子,在台阶前站了下来。
格里沙加爷爷没有做声。在他那冷冷的目光中,有痛恨,也有憎恶。
“我是问,你好!”米沙提高了声音。
“托福托福。”老头子很勉强地回答说。
他依然在看着米沙,目光中那憎恨的神气依然没有减弱。米沙随随便便地叉开两腿,站在那里;玩弄着鞭子,皱着眉头,噘着像姑娘那样饱鼓鼓的嘴唇。
“格里沙加爷爷,你为什么没有跑到顿河那边去呀?”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这儿的人嘛,所以我知道。”
“你是谁家的?”
“是柯晒沃依家的。”
“是阿基姆卡的儿子吗?阿基姆卡不就是那个在我们家做过长工的吗?”
“就是的。”
“小东西,就是你吗?在受洗节给你起了个名字叫米沙,不是吗?好啊!真像你爹!以前你爹总是恩将仇报,你大概也是这样吧?”
米沙从手上脱下一只手套,眉头皱得更紧了。
“怎么给我起名字,起的什么名字,这都跟你没关系。我问你,你为什么没有跑到顿河那边去?”
“我不想走,所以就没走。你这是怎么啦?你成了反基督的走狗啦?帽子上戴上红星啦?你这狗崽子,坏蛋,这么说,你跟咱们哥萨克作对吗?跟自己村里人作对吗?”
格里沙加爷爷颤颤巍巍地走下台阶。看样子,自从柯尔叔诺夫一家人跑到顿河那边去以后,他的饭食太差了。他被家里人撇下后,身体异常衰弱,像所有的老头子一样浑身十分肮脏,他面对着米沙站下来,带着惊愕和愤怒的神气望着米沙。
“是要作对,”米沙回答说,“我们跟他们的账还有得算呢!”
“《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这话怎么样?”
“老人家,你别拿《圣经》来蒙哄我,我不是来听这个的。现在你马上从家里出去。”米沙沉下脸说。
“这是怎么回事儿?”
“就是这么回事儿!”
“你这是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你给我出去!……”
“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家。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你是反基督的走狗,你的帽子上有反基督的符号!《耶利米书》上说到过你们:‘我必将茵陈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我要把他们散在列邦中……’ 现在就是儿子起来反对老子,兄弟起来反对兄弟啦……”
“老人家,你别糊弄我啦!这不是兄弟间的事情,这笔账很简单:我爹给你们干了一辈子,一直干到死,我在打仗以前也给你们打麦子,我年纪轻轻的,肚子都叫你们家的粮食口袋压伤啦,现在到了算账的时候。你给我从房子里出去,我这就烧房子!你们以前住好房子,现在就跟我们一样,去住住草屋吧。你明白吗,老家伙?”
“噢噢!就是这么回事儿!在《以赛亚书》上就是这样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 ……”
“哼,我现在没工夫跟你啰嗦!”米沙带着愤怒的口气冷冷地说。“你出去不出去?”
“不出去!你滚,坏蛋!”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老顽固,才打起仗来的!是你们鼓动老百姓,叫他们反对革命……”米沙急急忙忙摘下卡宾枪……
一声枪响过,格里沙加爷爷仰面倒下,清清楚楚地说:
“我……自个儿不愿意死……可是天意要我死……主啊,收留你的奴仆吧……慈悲慈悲吧……”他哼哼起来,白胡子底下冒出血来。
“会收留你的!早就该把你这个老家伙送去啦!”
米沙十分厌恶地绕过直挺挺地躺在台阶前的老头子,跑上台阶。
被风吹进过道里的干刨花冒起红红的火苗,储藏室和过道之间的板墙很快就着了火。火烟冒到天花板上,过堂风一吹,就冲进了屋子。
米沙走了出来,不等他点着棚子和仓房,屋子里的火苗已经蹿了出来,沙沙地舔着松木窗框,像胳膊一样伸向房檐……
米沙走到附近的树林里,在缠满野蛇麻草的乌荆子凉荫下一直睡到黄昏时候。他那匹下了鞍、绊住腿的马,就在这里懒洋洋地扯着嫩绿的梯牧草在吃。到黄昏时候,那马渴了,嘶叫起来,把主人吵醒了。
米沙爬起来,把军大衣捆到鞍后皮带上,就在树林里用井水饮了饮马,然后上了鞍,骑上马朝小胡同里走去。
在已经烧光的柯尔叔诺夫家的宅院里,还有一些黑黑的、已经烧成炭的木桩子冒着烟,呛人的烟气慢慢扩散开去。一座高大的房子只剩了高高的石头房基,再就是那塌掉一半的炉灶,那熏得黑黑的烟囱还指着天空。
米沙径直朝麦列霍夫家走去。
伊莉尼奇娜正在棚子底下往围裙里捡引火柴,米沙也没有下马,推开篱笆门,就进了院子。
“您好啊,大婶儿!”他很亲热地问候道。
可是她吓坏了,连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耷拉下两手,引火柴都从围裙里撒了出来……
“您过得好啊,大婶儿!”
“托……托福。”伊莉尼奇娜迟迟疑疑地回答说。
“你活着吗,身体好吗?”
“活是活着,身体好可就说不上啦。”
“你们家的哥萨克都上哪儿去啦?”
米沙下了马,走到棚子跟前。
“上顿河那边去啦……”
“他们是盼士官生来吗?”
“我是女人家……这些事我不知道……”
“叶福杜吉娅·潘捷莱芙娜在家吗?”
“她也上顿河那边去啦。”
“鬼叫他们他妈的都上顿河那边去!”米沙的声音哆嗦了两下,因为愤怒强硬起来。“大婶儿,我要对您说:你儿子格里高力是苏维埃政府最凶恶的敌人。我们一到顿河那边,就把他第一个绞死。可是潘捷莱·普罗柯菲耶维奇真不该跑。他又老又瘸,就应该老老实实蹲在家里……”
“等死吗?”伊莉尼奇娜冷冷地问了一声,又往围裙里捡引火柴。
“哼,他还死不了。也许会多少抽他几鞭子,但还不至于打死他。不过,我自然不是为这些事来的。”米沙提了提胸前的表链,垂下眼睛。“我是来看叶福杜吉娅·潘捷莱芙娜的。我觉得很可惜,她也跑啦。不过,大婶儿,您是她的亲娘,我要对您说说。我要说的就是:我老早就在想她,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多工夫来想姑娘,我们要打反动派,要狠狠地揍他们。可是等我们把反动派完全消灭了,等到全世界都建立起太太平平的苏维埃政权,那时候,大婶儿,我就要请媒人上你们家来向叶福杜吉娅·潘捷莱芙娜求亲啦。”
“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不,是时候啦!”米沙皱起眉头,他的两道眉毛中间出现了倔强的皱纹。“求亲还不是时候,谈谈这件事是可以的。我再也找不到另外的时间来说说这话啦。今天我在这儿,明天说不定就上顿涅茨那边去。所以我要事先提醒您:不要随便叫杜尼娅嫁人,不然我可要对不起您。如果我的部队里有信来,说我已经死了,那时候您就叫她嫁人好啦,现在可不行,因为我和她有了情意。我没有给她带礼物来,因为没有地方去弄礼物。不过,如果您要什么资产阶级和商人的玩意儿的话,您就说吧,我可以马上去弄来。”
“可别这样!我们从来没要过别人家的东西!”
“噢,那就随您吧。如果您比我先见到叶福杜吉娅·潘捷莱芙娜的话,请您替我向她问好,大婶儿,再会吧,请您别忘了我的话。”
伊莉尼奇娜也不回答,便朝屋子走去,米沙便上了马,朝村子里的大操场走去。
到夜里,红军从山上下来,进了村子。他们的闹闹哄哄的说话声响遍了大街小巷。有三个红军带着手提机枪到河边去放哨,盘问了一下米沙,又看了看他的证件。他在“生铁头”谢苗家的对过又碰上四个红军。其中两个人赶着一辆大车,车上装的是燕麦,另外两个人和谢苗的害痨病的老婆一起,抬着一架脚踩缝纫机,扛着一口袋面粉。
“生铁头”的老婆认出了米沙,跟他打了一声招呼。
“大嫂子,你这是抬的什么?”米沙问道。
“我们这是扶助贫农阶级妇女成家立业:我们把资产阶级的机器和面粉送给她。”一个红军又敏捷又带劲儿地回答说。
米沙一连烧了七家的房子,这七家是逃到顿涅茨那边去的买卖人莫霍夫和“擦擦”阿杰平、维萨里昂神甫、潘克拉季教长和另外三个富裕的哥萨克,把火点着以后,他才出了村子。
他上了山冈,转过马头。下面,鞑靼村里,红红的火焰就像闪闪发光的狐狸尾巴似的,一直翘到黑漆漆的天空里。火焰忽而向高处蹿去,火光照得湍急的顿河水闪着粼粼的金光,时而倒伏下去,倒向西方,贪婪地吞食着一座座的房屋。
从东方吹来一阵轻轻的草原清风。微风吹得火焰越来越旺,并且把一个个黑黑的、闪烁着煤炭般亮光的烟团送得很远很远……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