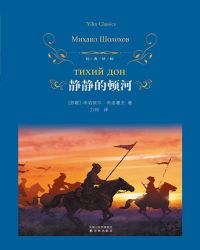第十八章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八章
卡列金自杀以后,诺沃契尔卡斯克的政权便转入顿河远征军司令纳扎洛夫将军之手。一月二十九日,他被参加军人联合会大会的代表们选为顿河军的委任司令官。参加这次大会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代表,主要来自南部地区下游各乡镇。这一次的军人联合会就叫“小联合会”。纳扎洛夫在小联合会的支持下,宣布征集十八到五十岁的男子入伍,并且采取了种种威胁恫吓手段,又派出武装部队到各乡镇去强行征集,但是哥萨克们都不愿意出来打仗。
在小军人联合会开始执政的那一天,克拉司诺希柯夫将军的顿河哥萨克第六团在塔青中校率领下,经过长途行军,从罗马尼亚前线回到了诺沃契尔卡斯克。这个团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开始,就且战且进,冲破布尔什维克部队的层层包围。在皮亚吉哈特卡、梅希瓦、马特维耶夫山冈和许多别的地方都受到拦截,尽管这样,这个团到达诺沃契尔卡斯克时几乎全员,军官无一伤亡。
为这个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在教堂广场上举行过祈祷仪式之后,纳扎洛夫就对哥萨克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保持了良好的纪律、良好的秩序,感谢他们回来保卫顿河。
不久这个团就开上前线,开到苏林车站附近,可是过了两天,诺沃契尔卡斯克就接到十分可怕的消息:这个团受到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自动离开阵地,拒绝保卫军政府。
小联合会的局面打不开。大家都感到同布尔什维克斗争没有什么希望。每次开会,纳扎洛夫这样一个有毅力、有朝气的将军都一手托腮坐在那里,另一只手捂着额头,好像是在苦苦思索什么问题。
最后的希望都化成了灰烬。赤卫队逼近了诺沃契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齐霍列茨克附近已经响起隆隆的炮声。有消息说,红军指挥员阿甫托诺莫夫少尉的部队正从察里津向罗斯托夫推进。
列宁命令南方前线于二月二十三日 拿下罗斯托夫。
契尔诺夫大尉的白卫军,受到西维尔司部队的攻击和戈尼洛夫乡哥萨克的背后包抄,于二月二十二日退进了罗斯托夫。
眼看着守不住了。科尔尼洛夫明白,留在罗斯托夫是很危险的,于是下令撤往奥里根镇。捷美尔尼克的工人对火车站,对军官巡逻队射击了一整天。快到黄昏时候,密密麻麻的科尔尼洛夫的队伍出了罗斯托夫。一大队人马就像一条老粗的黑蛇,渡过顿河,曲曲弯弯地朝阿列克塞爬去。一支支短小的连队,蹚着松软而潮湿的积雪,吃力地前进着。实业学校学生那带有锃亮的纽扣的草绿色学生大衣闪来闪去,但是大多数还是步兵军官的军大衣。担任排长的是一些上校和大尉。当兵的是士官生和军官,从准尉到上校都有。在数不清的辎重车后面,是一群一群的难民。都是一些上了年纪、很有气派的人,穿着很阔气的大衣和套鞋。许多妇女扶着大车,在老深的雪里很费劲地走着,高跟鞋一扭一扭的。
叶甫盖尼·李斯特尼次基大尉也在科尔尼洛夫团的一个连里。和他并肩走的,一个是挺有精神的作战部队军官司塔洛别里斯基上尉,一个是苏沃洛夫法拿果里精锐团包察里夫中尉,还有一个是罗维乔夫中校——是一个老掉了牙的作战部队的军官,浑身长着一层红毛,就像一只大狐狸。
暮色越来越浓。渐渐冷起来。从顿河河口吹来带咸味的、潮湿的风。李斯特尼次基习惯地、一步一步地踩着已经踩碎的积雪,注视着一些朝连队前面跑的人的脸。科尔尼洛夫团的团长涅申采夫和御林军普莱奥布拉申斯基团原来的团长库捷波夫从路边走了过去,库捷波夫敞着军大衣,制帽歪戴在平平的后脑勺上。
“团长先生!”罗维乔夫中校熟练地将步枪换了换肩,对涅申采夫叫了一声。
库捷波夫扭了扭宽额头、两只黑眼睛离得远远的、大胡子修成了铲子形的那张牛脸;涅申采夫隔着他的肩膀朝叫他的人看了看。
“请您命令第一连加快步伐!这种走法准得冻死。我们的脚都湿透啦,还要这样慢腾腾地走……”
“岂有此理!”嗓门儿又大又爱吵的司塔洛别里斯基叫了起来。
涅申采夫没有回答,走了过去。他正和库捷波夫争论着什么事。过了不大的一会儿,阿列克塞耶夫将军赶到了他们前头。将军的车夫赶着两匹肥壮的、扎着尾巴的大青马;雪粉一团一团地从马蹄下朝四处乱飞。阿列克塞耶夫的白胡子向上翘着,那上挑的眉毛也已经白了,一张脸被风吹得通红,他把制帽一直扣到耳朵上,身子斜靠在马车的后背上,瑟瑟缩缩地用左手扶着大衣领子。军官们都含笑目送着他那张大家都熟悉的脸。
被很多只脚踩得稀烂的大路上,渗出不少黄黄的小水洼。走起路来十分费劲,两只脚滑来滑去,雪水往靴子里直钻。李斯特尼次基一面走,一面听前面的人说话。一个声音浑厚、穿着皮上衣、戴着普通哥萨克皮帽的军官说:
“中尉,您看见了吗?那是国家杜马主席罗坚柯,也在步行呢。”
“俄罗斯在往峨尔峨他 走呢……”
有人咳嗽着,呼噜呼噜地吐着痰,想说说俏皮话:
“上峨尔峨他……跟这不大一样,上峨尔峨他走的是石子路,现在走的是雪地,而且水漉漉的,再加上冷得要冻死人。”
“诸位,知道在哪儿宿营吗?”
“在叶卡捷琳诺达尔。”
“我们在普鲁士的时候,有一次行军也是这样……”
“库班总会欢迎咱们吧?……什么?……当然,那就是另一回事儿啦。”
“您有烟吗?”郭罗瓦乔夫中尉问李斯特尼次基。
他扯下粗布手套,接过纸烟,道过谢,又像个士兵那样擤了擤鼻涕,在大衣襟上擦了擦手指头。
“中尉,您想学学大众化作风吗?”罗维乔夫中校微微笑着问。
“非得学学不可。您怎么……带了一打手绢准备着用吗?”
罗维乔夫没有回答。他那红中夹白的胡子上结起绿莹莹的冰凌。他偶尔地抽抽鼻子,冷风朝军大衣里直钻,冻得他皱起眉头。
“俄罗斯的精华。”李斯特尼次基十分痛心地打量着一列列的人和曲曲弯弯前进的队伍,心里想道。
好几个骑马的人跑了过来,其中骑在一匹高大的顿河马上的是科尔尼洛夫。他那件两侧带有斜兜的浅绿色皮袄和白色的皮帽在队伍里晃悠了半天。军官大队用浑厚、响亮的“乌拉”声在送他。
“这一切倒不算什么,问题是家里……”罗维乔夫老声老气地哼哧着,斜眼看了看李斯特尼次基的眼睛,好像是在寻找同情。“我的家眷还在斯摩棱斯克呢……”他又说了一遍。“妻子和一个女儿,女儿是个大姑娘啦。圣诞节的时候已经满十七岁啦……这可怎么办啊,大尉?”
“哦——哦……”
“你也有家眷吗?您是诺沃契尔卡斯克人吗?”
“不是,我是顿河区的。我只有父亲。”
“真不知道对她们该怎么办……我不在家,她们的日子又怎么过。”罗维乔夫又说。
司塔洛别里斯基气忿地打断他的话头,说:
“大家都有家眷留在家里。我真不明白,中校,您哼唧什么?真少见!还没有走出罗斯托夫的地界,就……”
“司塔洛别里斯基!彼得·彼得洛维奇!塔干罗格那一仗,您参加了吧?”有人在后面隔着一列人叫喊道。
司塔洛别里斯基转过气忿的脸,阴沉地笑了笑。
“哦……符拉季米尔·盖奥尔吉耶维奇,哪一阵风把您刮到我们排里来啦?调来啦?跟谁闹别扭啦?噢……是的,那是当然……您问塔干罗格那次打仗吗?是的,我参加啦……怎么?一点不错……他阵亡啦。”
李斯特尼次基漫不经心地听着他们说话,想起自己离开亚戈德庄时的情景,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阿克西妮亚。怀念之情忽然涌上心头,心里憋得发慌。他无精打采地走着,看着一根根上了刺刀的枪筒子在前面晃动,看着戴皮帽、制帽和风帽的许许多多的头随着脚步摆来摆去,心里想道:
“这五千个流亡的人,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怀着一股强烈的仇恨和愤怒。下流痞子们,把我们撵出了俄罗斯,又想来这儿称王称霸,等着瞧吧!……总有一天科尔尼洛夫会带我们上莫斯科!”
这时候他想起科尔尼洛夫那一次去莫斯科,于是高高兴兴地回想起那一天的情景。
后面不远处,大概就在他们这个连的尾部,有一个炮兵连。马匹打着响鼻,炮车轰隆轰隆地响着,连马汗气味都扑了过来。李斯特尼次基马上就闻出这种熟悉而亲切的气味,扭过头去;在前面当驭手的一个青年准尉看了看他,笑了一下,就好像见到了熟人似的。
三月十一日以前,志愿军的部队就已经集中在奥里根乡地区。科尔尼洛夫暂不下令出发,等候顿河远征军司令波波夫将军到奥里根来,波波夫将军已经率领自己的队伍退出诺沃契尔卡斯克,开到顿河对岸的草原上去,他的队伍大约有一千六百条枪、五门大炮和四十挺机枪。
十三日上午,波波夫由他的参谋长西道林上校和警卫队的几名军官陪着,来到奥里根镇上。
他来到科尔尼洛夫住的房子旁边的操场上,勒住马,扶住鞍头,很吃力地跨下马鞍。一个黑头发、黑脸膛、眼睛像麦鸡一样尖的年轻哥萨克勤务兵,连忙跑过来扶住他。波波夫把缰绳扔给他,便很有气派地朝台阶走去。西道林和几个军官也都下了马,跟在他后面。勤务兵们把几匹马牵进院子。一个上了年纪的跛脚勤务兵还在挂马料袋的时候,那个黑头发、眼睛像麦鸡一样的勤务兵已经和房东家的女仆搭讪起来。他对她说了几句酸溜溜的话。那个女仆——一个面色绯红的姑娘,披着一条十分漂亮的头巾,光光的腿上穿着深筒套靴——就一面笑着,脚下一面打着滑,踩着水洼从他身边跑过,啪哒啪哒地朝棚子里跑去。
派头十足、上了年纪的波波夫走进房子。他在堂前把军大衣交给一个动作麻利的勤务兵,把马鞭子挂在衣架上,大声地擤了半天鼻涕。勤务兵把他和边走边拢头发的西道林领进大厅。
应邀前来开会的将军们已经到齐。科尔尼洛夫坐在桌子旁边,两只胳膊肘撑在一张摊开的地图上;他的右首是白发苍苍、瘦骨嶙峋、腰板笔直、刚刚刮过脸的阿列克塞耶夫。邓尼金忽闪着两只精明而厉害的眼睛,正在和罗曼诺夫斯基说话。远看很像邓尼金的鲁科姆斯基,慢慢地在屋子里踱着,捋着大胡子。马尔科夫站在面向院子的一个窗户跟前,看着勤务兵们喂马,和年轻的女仆挤眉弄眼地说笑。
他们两个新来的,同大家打过招呼,就朝桌子跟前走去。阿列克塞耶夫问了几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问了问路上和由诺沃契尔卡斯克撤退的情形。库捷波夫走了进来,跟他一起来的还有科尔尼洛夫邀来开会的几位作战军官。
科尔尼洛夫对直地看着从容镇定地就座的波波夫,问道:
“将军,请您说说,您手下有多少条枪?”
“一千五百条枪,一个炮兵连,四十挺机枪,都配有机枪手。”
“志愿军被迫撤出罗斯托夫,这情况您已经知道啦。昨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向库班进军,方向是叶卡捷琳诺达尔,一部分志愿军部队正在这座城市附近活动。我们走这条路线……”科尔尼洛夫用没有削的铅笔头在地图上画了一下,说得快些了:“沿路吸收一些库班的哥萨克,粉碎那些小股的、零散的、没有战斗力的、企图拦阻我们前进的红军部队。”他对着波波夫那眯缝起来、转向一边的眼睛看了看,把最后的话说了出来:“我们向您建议,让您的部队和志愿军联合起来,同我们一起向叶卡捷琳诺达尔进发。力量分散——对咱们不利。”
“我不能这样干!”波波夫坚决而严峻地声明说。
阿列克塞耶夫微微朝他偏了偏身子。
“请问,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离开顿河区地界到什么库班去。我们北面有顿河作屏障,可以在越冬地区观望事态的发展。敌人不可能有什么大规模的行动,因为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河面就要开始解冻,不仅炮队不能过河,连马队也不能过河。可是我们在越冬地区,草料和粮食都有充分保证,可以随时随地展开游击战。”
波波夫理直气壮地举出很多理由,驳斥科尔尼洛夫的意见。他缓了一口气,看见科尔尼洛夫要说话,就很执拗地摇了摇头,说:
“请让我把话说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我们这些做将领的,也要加以考虑:就是我们的哥萨克的情绪。”他伸出一只肉嘟嘟的白手,那手上的金戒指嵌进食指的肉里;他一面打量着大家,提高声音继续说下去:“如果我们朝库班开拔,军队就有瓦解的危险。哥萨克们就可能不肯去。不应当忘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我的部队最根本、最坚定的部分就是哥萨克,然而就士气来说,他们并不怎么可靠,就像……就连您的部队也是这样。他们简直还没有自觉性,说不去,就是不去。整个部队有可能散掉,我可不能冒这个险。”波波夫干脆利落地说,他又不让科尔尼洛夫说,接着说下去,“请您原谅,我对您说出了我们的决定,并且斗胆向您说明: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决定。当然,分散力量对咱们是不利的,不过,情况既然已经是这样,只有这个办法了。我认为,根据我刚才提到的情况来看,志愿军最好不要上库班去,库班哥萨克的情绪很使我担心,志愿军最好还是跟顿河军一起到顿河对岸的草原上去。在那儿可以利用休息时间整顿一下队伍,在开春以前,就可以用从俄罗斯自动来的新的骨干力量补充起来……”
“不行!”科尔尼洛夫叫道。昨天他还主张开往顿河对岸的草原上,而且还很坚决地驳斥了阿列克塞耶夫的反对意见。“上越冬地区毫无意义。我们差不多有六千人呢……”
“如果说的是给养问题,大人,那我可以斗胆向您保证,越冬地区完全可以充分供应。并且,您还可以从那儿的私人养马场上弄到一些马匹,可以装备一部分马队。以后您就有条件去进行野地运动战。您是很需要马队的,可是志愿军的马并不多。”
科尔尼洛夫今天对阿列克塞耶夫特别客气,这会儿朝他看了一眼。科尔尼洛夫显然在选择进军方向问题上是动摇不定的,很想得到另外一个有权威的人的支持。大家都十分注意地听完了阿列克塞耶夫的发言。这位老将军解决问题一向干脆、利落、明快,用几句简单明了的话就说清了向叶卡捷琳诺达尔进军的好处。
“走这个方向,我们很容易冲破布尔什维克的包围,同活动在叶卡捷琳诺达尔附近的部队会合。”他最后说。
“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这样进军要是失利呢?”鲁科姆斯基很小心地问道。
阿列克塞耶夫咂了咂嘴,用手在地图上画了画。
“退一万步说,如果失利,那我们还可以到高加索山里去,把部队化整为零。”
罗曼诺夫斯基支持他的意见。马尔科夫说了几句热情的话。阿列克塞耶夫的很有分量的理由似乎是无可反驳的了,但是鲁科姆斯基接过话来,把两边的分量拉平了:
“我赞成波波夫将军的意见,”他字斟句酌、不慌不忙地说,“向库班方面进军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其困难在这里是无法估量的。首先,咱们要过两次铁路线……”
参加会议的人的目光都顺着他的手指所指,转向地图。鲁科姆斯基很坚定地继续说下去:
“布尔什维克会千方百计地截击我们,他们会派铁甲车来。我们的辎重队太累赘,伤号又多;我们又不能扔下不管。这一切都使军队行动起来特别困难,不能很快地前进。还有一点我也很不明白,凭什么可以说,库班哥萨克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呢?就拿顿河哥萨克来说,本来也说是不满意布尔什维克的政权的嘛,所以我们应该抱着格外小心和最大的怀疑态度来看待这一类的说法。库班人也在害那种布尔什维克式的沙眼病,这种病是从以前俄罗斯军队里传染去的……他们会敌视我们的。最后我要再说一遍,我的意见:往东去,往草原上去,到那里养精蓄锐,威胁布尔什维克。”
科尔尼洛夫在手下大多数将领支持下,决定走维里柯克尼亚什以西的路线,在路上给非战斗人员补充一些马匹,然后从那里拐向库班。他宣布散会以后,和波波夫说了几句话,冷冷地道过别,便朝自己的房里走去。阿列克塞耶夫跟着他走进房里去了。
顿河军的参谋长西道林上校碰得刺马针丁当丁当响着,来到台阶上,又响亮又得意地朝勤务兵喊道:
“带马!”
一个留着淡黄色小胡子的青年哥萨克中尉,扶着马刀,蹚着水洼,走到台阶跟前。他在最下面一级旁边站下来,小声问道:
“上校大人,怎么样?”
“不坏!”西道林兴高采烈地小声回答说。“咱们拒绝上库班啦。咱们马上就走。你们准备好了吗,伊兹瓦林?”
“好啦,马来啦。”
勤务兵们骑上马,把马带了过来。那个黑头发、眼睛像麦鸡一样的勤务兵,还在一再地问他的同伴。
“怎么样,她漂亮吗?”他哧哧地笑着问道。
那个上了年纪的勤务兵低声笑了笑。
“不怎么样。”
“如果她叫你去,你怎么样?”
“算了吧,呆子!现在是大斋期。”
格里高力·麦列霍夫的旧同事伊兹瓦林,跳上自己那匹白额头、白鼻子、屁股下垂的战马,对勤务兵吩咐说:
“你们先到街上去。”
波波夫和西道林一面同一位将军道别,一面走下台阶。一名勤务兵勒着马,帮助将军的脚踩上马镫。波波夫晃了晃不算讲究的哥萨克式马鞭,赶着马小跑起来,几个哥萨克勤务兵、西道林和几名军官也都欠身站在马镫上,身子微微前倾,跟着他跑起来。
经过两天的行军,志愿军来到梅契庭镇,这时候科尔尼洛夫又得到有关越冬地区的一些新消息。这些消息都是不太好的。科尔尼洛夫把所有作战部队的指挥官都召集了来,宣布了向库班进军的决定。
他又派一个传令官去见波波夫,再一次建议联合起来。传令官在老伊万诺夫地区追上了部队。他带回了波波夫的回信,回信依然是那样:波波夫很客气、很冷淡地拒绝了科尔尼洛夫的建议,并且在信上说,他的决定是不可能变更的,还说他要暂时在萨尔斯克州驻下来。 静静的顿河(经典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