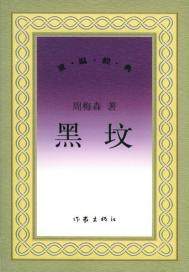小兔子觉着自己快要死了。他感到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不太对劲。小便失禁了,两条的大腿内侧总是湿漉漉、黏糊糊的;脖子也变得软绵绵的,好像已无力支撑他那沉重的脑袋。他眼前时常冒出一片片旋转的金星,耳旁时常响起一种单调的、令人心烦意乱的嗡嗡长鸣声。他的步履不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居然变得踉踉跄跄起来,每向前挣扎一步,都要付出许多精力。虚弱的汗水从他身上的汗毛孔里渗了出来,头上、脖子上、胸脯上,一直到腰上、腿上、脚面上全都是汗津津的。他发着烧,喘息得很厉害,每向前走一小段,就要扶着棚腿“呼哧”、“呼哧”地喘上一阵,好像吸进肺腑的空气总是不够用似的。
他认定自己快要死了,他觉着,他生命的浆汁正随着他脚步的每一次迈动,随着他身体的每一次摇晃,在悄无声息地、一点一滴地渗入脚下这条黑暗的道路里。他觉着,他不是在一条实实在在的道路上行走,而是在一张巨大的、没有边际的蜘蛛网上挣扎。他的脚很沉、很重,好像总是牢牢粘在蜘蛛网的黏液里,他似乎再也无力从这张网里挣脱开去。
在前面等待他的,是命运的毒蜘蛛,它正悄悄地潜伏在一片黑暗中,等待吃掉他!只要他倒下去,它一定会吃掉他的!
他不能倒下去。
他似乎忘记了身上的伤痛、忘记了饥饿的肚皮、忘记了已经经历过的一切痛苦的磨难,机械地向前走着;只要双腿还能支撑住他的身躯,他就要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然而,他摇摇晃晃的身躯在黑暗中却一次次撞在棚腿上、煤帮上,他一次次倒在潮湿的地下;每到这时候,他便趴一会儿,喘息一下,爬起来再走。
他希望在这充满险恶的生命旅途上能够出现一点奇迹他渴望能碰到一个比他更弱小的濒临死亡的人,甚至渴望能碰到一具人的尸体。他无数次地想象着,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奇迹,那么,他就要像狼一样地扑上前去,撕它的皮、扒它的肉,或者干脆咬断它的喉管、吮它的血……他敢么?也许……也许他是敢的,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他就把他当作一匹死马、一匹死骡子……
从那条没顶的水巷子里钻出来的时候,他把用布条扎在腰上的最后两条马肉给弄丢了。他不知道把它丢在了哪里,他想再回水巷去找,可试着往回摸了几步,他就停住了脚。他知道,重新找回他的马肉几乎是不可能的,水巷很长,中间有一小段地方黑水没了顶。他也许就是在那段黑水没顶的地方弄丢他的马肉的。他记得,那一瞬间,他又看到了他的窑神爷,窑神爷向他招了招手,他就一个猛子扎了下去……从水里勉强探出头时,马肉好像已经丢了,不过,那时候他没有注意,他在急切地寻找那个蓝面孔——他的窑神爷,他找了好久也没找到,等到想起拴在身上的马肉时,马肉已经不存在了。
这真是件意想不到的事。
他是为着保住这点马肉,才从那个避风洞里逃出来的;可逃出来以后,竟丢了他的马肉!
他想哭,但哭不出来,他似乎已不会哭了。他眼里早已流不出泪了。他呆呆地倚着煤帮站了一会儿,像是一只迷了路的羔羊,不知道该把自己的脚步迈向哪里。继而,他感到浑身发冷,他顺着煤帮软软地坐了下来,身体尽量往一根长着霉毛的木头棚腿上靠,靠在那根棚腿后面,他迷迷糊糊地又走进了另一个世界……
他看见了他那失落已久的太阳。他的太阳又圆又大,像一个着了火的兔子,从一个深深的、看不见底的山谷里火爆爆地蹦了出来,蹦到了他家的院子上空,蹦到了他家的屋顶上。他的面前一片光明,他感到浑身暖洋洋的。他把两只干瘦的、沾满煤灰的手伸向了太阳,手掌上马上感觉到了太阳的温暖。太阳却是躁动不安的,它开始向空中升腾;他哭了,他不让太阳离去,他再也不愿和他的太阳分开了,他扑过去搂住了他的太阳。
他搂住他的太阳睡着了。
睁开眼时,他才发现,他搂住的不是他的太阳,而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把他揽在怀里,正用手抚摸着他的头发,轻轻向他说着什么;母亲身边还站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恍惚是他的父亲。他从母亲怀里挣扎着坐了起来,扑到了父亲面前,向他讲述了母亲的不贞,讲述了另一个占有他母亲的男人,讲述了那风雨夜中的一幕……父亲发怒了,又像往日喝醉了酒那样,揪住母亲的头发,和母亲扭打起来。又过了一会儿,那个不要脸的男人跑来了,和母亲一起打他父亲;他上去给父亲帮忙,打那个男人,那个男人飞起一脚,将他踢出了大门。他出了大门,便像鸟儿一样,在空中飞,他的两只胳膊变成了鸟儿的翅膀。他飞呀,飞呀,飞到了那个挂绸布灯笼的地方……那地方好像不是窑子,可他却在那地方看见了小二姐,他早就想着和她玩一玩了,为此,他曾暗地里扣下了几班工钱。可母亲发现了,把他骂了一顿,把他扣下的钱也给翻走了,他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找到他藏钱的地方的,他藏钱时,母亲并不在跟前呀!
他这次是带了钱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反正口袋里有钱。
他站到了小二姐面前,怯怯地去拉她的手,小二姐忸忸怩怩的,没有拒绝。于是,他便去扒她的衣裳。他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成年女人身上应有的一切……他像个老嫖客一样,趴了上去……
在这最愉快的时刻,凉飕飕的巷道风将他吹醒了,他的身上黏黏糊糊湿了一片,他这才明白过来,他是倚着棚腿睡着了,做了一个有关太阳、有关母亲、有关女人的梦。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小便失禁了,那玩意儿竟像个破水桶似的,滴滴答答地漏个不休,使他的两条大腿变得湿漉漉的。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他独自一人,又将许多黑暗抛到了身后,他一次又一次想到他要死了,他快要死了,可却总也死不掉。每一次倒在地上的时候,他都觉着自己再也爬不起来了;然而,每一次爬起来的时候,他又觉着自己还能走下去。
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吃支撑巷道的腐朽木头,吃脚下踩到的面矸子。他还拼命喝水,只要在巷道的水沟里发现了水,他就俯下身子喝个够。他自以为多喝水,就能帮着消化吃进肚里的木屑和石粉,自己的生命就可以多维持两天。
然而,始终没有出现奇迹。一路上,他再也没摸到一个活着的人,没摸到一具人的尸体,他摸到的除了棚腿、矸石,就是连绵不断的煤壁。
他几乎完全绝望了。
在这绝望之中,他又想起了二牲口和三骡子。他不知道他们是死、是活?他希望他们活着,希望他们从后面的黑暗中赶上来。在那条水巷里看见窑神爷的时候,他恍惚听到过身后的水声,他痴迷地想这蹚水的人或许就是二牲口和三骡子呢;如果是他们,那该多好呵!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在挣扎着走到他面前的时候,突然倒下成为一具尸体,那就更好了……
不管饿到什么程度,三骡子都牢牢记着那些有经验的老窑工给他说过的话“面矸子不能吃,那玩意儿是要吃死人的!”他不吃面矸子,他吃腐朽道木和巷道木的木渣,他把那木渣捻成面,和着水沟里的黑水,一把把硬吞下去。
他很后悔。早知带在身上的马肉会被那帮饿狼们抢去,那他就根本不该主动去和他们打招呼,或者他应该让自己先吃个饱。如果,一次吃饱了,即使没有水,他也能支撑六七天哩!
他和二牲口都没想到那帮饿狼会抢他们的马肉,更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凶狠地揍他们!现在回忆起来,他还感到后怕,他揣摩,那帮饿狼本来就不安好心!他们是要算计他们的性命的!在扭打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就使劲咬住他的肩膀,险些将他肩膀上的一块肉给咬下来。他和二牲口嚎叫着逃出了洞子,逃到了大巷里,蹚着水游到了几乎没顶的两架棚子下面。他抱着一根棚梁,二牲口抱着身边的另一根棚梁,硬是在冰冷的黑水里泡了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时节,他们真怕呀,前面是没顶的水巷,后面是一帮丧失了理智,丧失了人性的恶狼,他们既不能退,又不能进……
后来,两只胳膊都累酸了,两只手都发麻了,他们才想起了小兔子。他们断定小兔子不会往回跑,他一定是顺着水巷游了出去!若是小兔子游得出去,他们也可以游出去!他们试探着向前蹚,贴着煤帮、贴着棚梁,蹚到黑水没顶的地方,他们就一憋气潜入了水底……
竟然游了出去。
没顶的那段巷道总共不过三四棚,也就是十三四步的样子。
他们又向前游了一阵。渐渐地,脚下的水浅了,从胸脯退到腰际,又从腰际退到大腿、退到脚踝。
他们的脚又踏到了满是煤粉、矸子碴的道路上,他们又摇摇晃晃地上路了。
这次上路后,三骡子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感情仿佛全被浸泡在那水巷的黑水里了,他变得冷冰冰的了,一路上,几乎再也不愿多说一句话,即使是二牲口和他讲话,他也不理不睬。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都还希望能赶上小兔子,能和小兔子一起,分食他带出的马肉。然而,走了很长、很长时间,也没见到小兔子的影子,他们开始恶毒地诅咒这个可恶的小狼羔子。他们认定这个狡猾的混小子带着救命的马肉独自逃了,他用不着他们了,把他们甩了。
在第一次吃朽木粉的时候,三骡子恶狠狠地骂
“日……日他娘!我……我逮着小……小兔子这杂……杂种,非吃他的肉不可!”
二牲口道
“这狗……狗崽子也……也太没良心!我……我……也……也得扒他的皮!”
这是他们走出水巷之后惟一的一次对话,此后,他们彼此再也没说过什么,仿佛像两个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一样,各自凭着自己的力量,在黑暗中气喘吁吁地向前挣扎着,走着。
谁也帮不了谁,谁也不想帮谁,他们的感情已经完全麻木了,存在的只有求生的本能。
好在走出水巷之后,大巷变得宽阔起来,他们的脚下又出现了走马车的铁道,巷道里再也没有什么堵塞物,他们也无须齐心协力去对付什么了。
三骡子的体力显然比二牲口要好一些,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走在前面。他走走歇歇,以听到二牲口的脚步声为原则;等二牲口追上来以后,他又拔腿向前走去,要是听不见了,他就停下来等候。
这一次停下来时,他摸到了一根插在煤壁上的腐朽的木板,那木板的表面还带着一层拇指般厚的树皮。他把木板拽了下来,坐在地上剥那层树皮;剥下一点后,便弄碎塞进嘴里。
正吃树皮的时候,他听到了身后一阵踉踉跄跄、很沉重的脚步声,继而,又听到了二牲口断断续续的呼叫声
“骡……骡子!我……我的脚崴了!”
他只是下意识地回过头向身后看了一下,便又自顾自地去掰那块干硬的树皮。
“骡……骡子!骡子!”二牲口又喊。
没有脚步声,二牲口大概是扶着煤帮站住了。
他依然不理。他把那掰下来的树皮用手指捻,捻不动;又用牙去咬,咬下一点,再捻。
“骡子!来……来扶我一把!”
他感到很不耐烦。他站了起来,折下一块树皮抓在手上,继续向前走,一直走到听不见二牲口声音的时候,才又倚着煤帮,坐到地上,认真对付他的树皮。
二牲口还是赶上来了。
当他听到二牲口“呼哧、呼哧”喘息声的时候,就站起身想走,不料,二牲口已不顾一切地扑到了他面前,抓住他的头发就打。
“养……养的!你……你他妈的心这么狠!老……老子白救……救你了!”
救我?!那老子下窑又是为了救谁?!
他想这样分辩的,可他没讲。他不愿白白浪费力气。他一拳打落了二牲口架在他脑袋上的胳膊,挣扎着站起来,又跌跌撞撞向前走。
他觉着二牲口太傻了,眼下到什么时候了,哪还能打架?他就是能打过二牲口,他也不打。这不是怜悯他,而是为了保存力气,他还要用这点力气,走完他要走的求生的路,他不能浪费一丁点儿力气。
向前走了七八步,他听到了二牲口呜呜咽咽的哭声。他心软了。他站下了,他等着他跟上来。他不忍心把他一个人抛在这里。他现在能够给一个朋友、给一个救命恩人的最大帮助只能是这么多了。
然而,就在他站下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听到了一阵急促的喘息声。开始,他以为这喘息声是身后的二牲口发出的,可听听却觉着不对。这喘息声分明是从前面黑暗的巷道中传来的,是另一个活人的胸腔里发出的。他一时没想到是小兔子,他试着伸出脚、伸出手,一点点地悄悄向前试探。当他的脚碰到一个热乎乎的身躯时,那身躯动了起来,他感到一双滚烫的胳膊,搂住了他的腿。
他被搂倒了。
“谁?你……你是谁?”他喊。
搂住他腿的手松开了,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我!是……是我!”
“小兔子!你……你狗日的是……是兔子?!”
他翻身坐了起来,急不可待地在小兔子身上摸索起来,他要找那个救命的马肉!这些马肉不能、也不该仅仅属于小兔子一人,应该归他们三人共有!
摸了半天,他什么也没有摸到!
他火了,一巴掌将小兔子打到煤帮上,又扑上去揪住他的头发,气喘喘地吼道
“肉……肉……肉呢?”
小兔子木然地道
“丢……丢了!早就……就丢了!”
“你……你说谎!一……一定是……是让你狗日的给独……独吞了!”
“没……没有!”
这时,二牲口也听到了他和小兔子的对话,二牲口也在他身后的黑暗中喊
“是……是兔子么?是么?快!快!兔……兔子,快来扶我一把!”
小兔子立时嘶哑着嗓子叫了起来
“二……二哥,你……你来救我!骡子打……打我!二哥!快……快来呀!”
三骡子更火了,他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压到小兔子瘦小的身躯上,想用两只手去掐小兔子的瘦脖子;小兔子脑袋乱晃、手乱抓,两条腿拼命地在地上蹬着,把地上的煤灰蹬得飞飞扬扬;突然他的一只手,被小兔子咬住了,他痛得大叫起来。
他一边叫着,一边用另一只手死死地按住了小兔子的脖子……
二牲口爬起来了,把他从小兔子身上扯了下来,也和小兔子一起打他。
三骡子这才感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他知道,他一个人是打不过面前这两个人的!这两个人都姓田,而他姓胡,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势必要合伙对付他的。倘若他被打败了,被他们打死了,他们真会吃他的肉的!
三骡子挣了几挣,打了几个滚,总算摆脱了二牲口和小兔子的纠缠,又站了起来,独自一人向前走了。
三骡子“踢拖,踢拖”的脚步声渐渐远了。
二牲口这才从满是煤尘的地上爬了起来,气喘喘地搂着小兔子滚烫的身子坐下了。他那老树皮一般粗糙的手开始哆哆嗦嗦朝小兔子身上摸
“兔……兔……兔子!你……你行!你真行!快!快告……告……告诉我,马肉藏在哪……哪里了!咱们……咱们是……是不该给骡……骡子吃!这……这小子也……也黑了心!”
小兔子呜咽着道
“二……二哥!我……我不骗你!马……马肉真的丢了!在过那条水巷时丢的!”
二牲口不相信,他那满是臭气的大嘴里发出一阵木棍断裂般的干涩的笑声
“兔……兔子!你……你别蒙我!我知道!我……我知道你精明哩!是……是不是藏到煤帮上了!快……快……快找出来!二……二哥要……要饿死了!”
二牲口说这话时,已抛开了小兔子。他把整个身子都俯到了地下,高高昂着头,两只大手在地下四处乱摸。他从道心摸到了水沟上,又从水沟上摸到了煤帮边。
“二哥!二哥!你……你别找了!没……没有!真……真没有了!”
小兔子跟在他身后爬。
小兔子抱住了他的脚。
二牲口一脚将小兔子蹬到了一边,又从那侧煤帮往这边摸。小兔子的举动,加深了他的怀疑,他断定那块救命的马肉,就藏在这黑暗中的一个什么地方。
然而,他摸了半天,摸得一头一脸的煤灰,摸得浑身是汗,还是没有摸到。这一次,轮到他发火了,他用两只干瘦如柴的手牢牢抓住小兔子的肩头,拼命摇撼着,像摇一段没有生命的朽木似的。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一阵“呼噜、呼噜”的可怕的异响。他用变了腔的声音吼道
“肉呢?肉呢?肉……肉在哪里?”
小兔子吓傻了。他认定二牲口是饿疯了,他不敢再说那块肉不存在了,他怕他会掐死他
“肉……肉……肉在……在……在前面的水沟旁边,在……在一块大矸石下面,我……我……我……”
二牲口的手松开了
“快,快去拿!快……快去!”
二牲口一松开手,小兔子便迅速向前爬去,爬了几步之后,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跑了。跑了好远、好远,才回头喊
“二……二哥,真……真的没有肉了,你、你……你快走吧!我……我也走了!”
二牲口愤怒而绝望地喊
“我……我剥了你个狗……狗娘养的!”
继而,二牲口又狼嚎一般地哭了起来,边哭边道
“小兔……兔子,嗷嗷,等……等……等……等我,扶……扶我一……一把!别……别把……把我一人扔……扔在后面!嗷嗷嗷……”
小兔子装作没听见,他扶着煤帮前的一根根棚腿,小心翼翼地向前摸去。他像个狡诈的狐狸似的,警觉地支楞起两只耳朵,一会儿听听前面的声音,一会儿听听后面的声音。他打定了主意,既不能走得太快,也不能走得太慢;既不能让走在前面的三骡子抓住,也不能让跟在后面的二牲口抓住。
他要吃掉他们,而决不能被他们吃掉!
他希望走在前面的三骡子先倒下去。他的耳朵一直在紧张地捕捉着从前面遥远的黑暗中传来的三骡子的脚步声,他的耳朵变得出奇的好。长期的黑暗,使人的视力退化了,他的眼前除了偶尔闪过的一片片旋转的金星外,几乎再也看不到什么东西;而他的耳朵却因此而进化了,他的耳朵现在能听见几十丈以外的一点很小的响动。他的耳朵跟踪着三骡子的脚步声,捕捉着夹杂在这沉重脚步声中的一阵阵艰难的喘息。他一次又一次地根据自己跟踪、捕捉到的声音来推断他们彼此相隔的距离和三骡子可能倒下去的最后时间。
他心里浮现出一个顽强的、不屈不挠的念头,这念头随着他脚步的每一次迈动、随着他的每一次喘息,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到后来,这念头竟变成了一堆火,一盏灯,一轮生命的太阳!
“你们吃不掉我!我要吃掉你们!”
他反反复复这样想着。他觉着自己的身体好得很哩!他觉着自己还可以拼将全部力气,和身前、身后的这两个要吃人的人进行一场严酷的厮杀,格斗!他断定二牲口和三骡子都要吃他。三骡子扼他脖子时的凶狠劲,二牲口掐住他肩头时的疯狂劲,使他想起来就感到后怕,他想,若是他们当时一齐扑上来将他按倒,他的小命就葬送了!他身上的皮肉,现在就不会再完整地贴在他的骨头上了!
他们失去了一个吃掉他的机会!
现在,轮到他来寻找机会吃掉他们了!
在关注着三骡子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走在他身后的二牲口。他将自己的脚步尽量放轻,使前面的三骡子和后面的二牲口都摸不清他的动向。他一下子想起了二牲口的许多坏处。这一路上,二牲口打过他多少次呀,他竟把他打昏过两次,他早就没安好心了!他早就想打死他,少个拖累;他那会儿打不过二牲口,这会儿却不一定打不过了!他能打过他,说不定还能吃了他!这没有什么不合理,他小兔子是在实行正义的报复!二牲口如此对待他,他为什么还要认这个本家二哥呢?至于三骡子,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胡家没有一个好东西,就冲着田、胡两家几十年的世仇,他打死他,吃他的肉也是合情合理的!
自然,他更希望二牲口和三骡子之间展开一场搏斗。如果他们能干起来,他就不必费什么精力了!不管谁打死了谁,对他都会有好处的!
他注意着二牲口的脚步声。二牲口的脚步声比三骡子的脚步声要沉重得多,他因此判定二牲口先倒下去的可能性要比三骡子大得多。有一次——当他扶着一根歪斜的棚腿喘息的时候,他听到身后“扑通”一声,心中一阵狂喜,以为二牲口终于不行了,他想摸过去看一下。可还没等他转过身,二牲口又气喘吁吁地爬了起来,可怜巴巴地喊
“骡……骡子!兔……兔子,等……等……等我呀!”
从二牲口的呼喊声中,他又判断出,二牲口还能勉强支撑一段时间,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彻底倒下。他失望地扭过身子,又木然地向前走了。
前面依然是永恒的黑暗。
三骡子最先摸到了那扇又宽又大、又高又厚的风门。最初,他没意识到这扇风门对他意味着什么,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摸到的是风门,他以为是一个机器房的大门。他用肩膀扛了一下,想扛开门,走进里面歇一下。然而,扛了几次,他也没扛动,门里面有一股强大的、具有弹性的力量将门压死了。这时,他才猛然想到这是一条主风道的风门,他一下子想起了斜井,想起了通往地面的道路。他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周身热血一下子升到了脑门,他那干枯的、深深陷下去的眼窝里涌出了热泪。他紧紧抓住风门上的铁把手,才没让自己的身子倒下去。他想向身后的二牲口和小兔子喊,可嘴唇动了半天,嘴里也没发出一点声音。
他又试着扛了一下。
风门支开了一道小缝,枪弹一般坚硬的风从门缝里钻了出来,几乎将他推倒在地。他的身子晃了一下,离开了风门,风门又“啪哒”一声死死合上了。
他转过身子,倚在风门上喊
“快,快来呀,我……我们走到斜井下了!这……这里是……是风门!”
是的,这是风门。
这是生命之门。
这是希望之门。
他的喊声给了小兔子和二牲口极大的刺激,黑暗的巷道里响起了一阵阵滚爬、跌撞的声响,响起了小兔子和二牲口带着哭腔的呼应
“来……来了!我……我们来了!”
“骡……骡子!来……来扶我一把!”
三骡子一下子慷慨起来,他不再顾惜自己的体力,他离开风门,顺着巷道的一侧向回摸,摸到二牲口之后,将他的一只胳膊架了起来。
他们三个人在这道生命之门下面会合了。
他们用肩头、用臀部、用脊背紧贴着这扇风门,一齐用力。
风门支开小半边,没容他们用脚抵住,又“啪”的一声关严了。
小兔子被打回来的风门撞倒在地上。
小兔子躺在地上大笑起来。
二牲口和三骡子也大笑起来。
阴森的巷道里充满了生命的欢娱、生命的笑声!
三个人的肩头、脊背、臀部又紧紧贴到了风门上。
二牲口喝起号子,三骡子和小兔子跟着呼应
“伙计们来!”
“嘿哟!”
“齐使劲来!”
“嘿哟!”
“这风门来!”
“嘿哟!”
“好他妈的重来!”
“嘿哟!”
“扛开它来!”
“嘿哟!”
“就走上窑来!”
“嘿哟!”
在这号子声中,风门一点点扛开了,倚在风门口的小兔子第一个蹿出了风门,紧接着倚在中间的二牲口也离开了风门。二牲口离开风门时,防了一手,他知道风门的力量很大,搞得不好,会把三骡子一人打到外边,他抓住了风门的门沿
“快!骡子!快过来!”
风门被风鼓着,像匹野马,拼命往回挣,二牲口一把没抓住,猛然闭合的风门还是将三骡子的一只胳膊给挤住了。
三骡子惨叫一声,挂在闭合的风门缝上昏了过去……
三骡子醒来时,已安然躺在二牲口身上。他那只被夹在风门上的胳膊已经断了,肘关节以下的部位软软地挂落下来。他顾不得胳膊上的疼痛,挣扎着爬起来,对二牲口道
“二……二哥,走!咱……咱们走!”
他们又打开了第二道风门,然后,沿着斜巷向上爬;爬了约摸半里路的样子,又一堆冒落的矸石,将他们的去路挡住了。
他们不得不再一次和这些冒落的矸石作战!
他们从死亡地狱爬到了这里,爬到了希望的边缘上,他们已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他们马上就可以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了,他们不能在这最后一堆阻碍物面前失去勇气!
他们疯狂地扑到了面前的堵塞物上,用最后一点残存的力气拼命扒了起来。
然而,他们毕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毕竟都奄奄一息了,面前的矸石、煤块对他们来说是太沉重,太沉重了!
小兔子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扛开风门给他带来的欣喜又被深深的绝望取代了。他痛苦地想也许这里就是他们最后的墓地,也许他们谁也不能走出这块墓地了……
他又一次想到了吃人与被吃!
他不再那么卖力了,他尽量躲懒,只把身下的矸石拨得哗哗响,却决不像二牲口和三骡子那样把最后一点力气都使出来。
二牲口和三骡子很快便发现了这一点,他们扑过来揍他;他便往斜巷下面滚,躲在黑暗中支起耳朵听他们的咒骂声,也听他们的干活声。他很清楚,他们的生命是联在一起的,他们扒通了道路,也就等于他扒通了道路;他们出得去,他也就出得去;他不能为此耗费宝贵的力气,他的力气要用在关键的时候,用在最后走出斜井的道路上。
他依然觉着自己有被吃掉的可能。
他认为,他们说他不卖力,是在为吃他寻找借口!寻找理由!
他们真坏,他们吃人还要找理由!
那个顽强的、不屈不挠的念头又在他脑海里浮现出来
“你们吃不掉我!我要吃掉你们!我要吃掉你们!”
万万想不到,就在他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前面的黑暗中传来了二牲口惊喜的喊声
“通了!扒……扒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