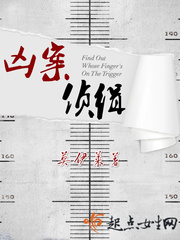等张宽看清眼前的情景,再次失声痛哭,哭的张长贵心惊胆战,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问题,只是不停地用手抚摸着张宽胸口。
哭了几声,张宽清醒过来,抽噎着鼻子道:“刚才做了个梦,跟真的一样,太吓人了。”
张长贵忙用被子盖住张宽,口里叽里咕噜不知说了些什么,然后才问,“做了什么内容的梦,吓成这样。”
张宽止住哭泣,正想开口说,无意间看了手臂一眼,登时愣住,手臂上明晃晃的两排牙印,已经发青红肿。看着这牙印,张宽迟疑了一下,把自己嘴巴凑上去,大小刚合适,瞬间,张宽后背就出了一层冷汗。
“这事玄乎,没理由我把自己咬成这样还不醒。”
听到儿子自言自语,张长贵不解地问,“到底怎么回事?你告诉我,或许我有办法解决。”
张宽摇摇头,“这事你没办法解决。”但还是把梦里的事情大概说了一遍,末了问道:“你说现实中,真有人黑白不分,是非颠倒吗?”
张长贵闻言一笑,极其苦涩,“这种事自古到今多了去,穷人永远都是被欺负的,自古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都是如此。”
张宽忽然想起,父亲曾说过他当初就是被冤枉的,当下问道:“难道你也是被诬陷的?”
张长贵摆摆手,“都是过去的事,不提也罢。现在能和你好好生活,我就很满足了。”
一听这话,张宽就明白了,父亲绝对是被冤枉的,又想到母亲,如果不是父亲被冤枉,母亲怎会弃自己而去?这样算来,当初冤枉父亲的人真是罪大恶极。想着就变的气愤起来,问道:“是谁冤枉你的?”
张长贵依然摆手,“算了,算了,都过去了。”
“不行!”张宽一砸炕头道:“你过去我过不去,我们两受了这么些年苦,这仇得报。”
张长贵一阵苦笑,“你这小子,等什么时候你身家过亿,我就告诉你仇人是谁。”
身家过亿?张宽一愣,“诬陷你的人很牛?”
张长贵摇头,“不是很牛,是非常牛,你身家过亿,有资格问当年的事情。但不代表你能报当年的仇。”
“那身家到了多少才能报仇?”
张长贵叹了一声,“现在这局面,要报仇,不仅仅是身家多少的关系,你还得有够强的势力。其余的你也别再问了,人生短短几十载,我已经失去了多半,剩下的日子,能让我好好的看着你,成家立业,让我抱抱孙子,我就心满意足了,什么报仇不报仇的,都是镜花水月了。”
听父亲这样说,分明是不想多说,张宽也不再问,只是心里在想,身家过亿,就凭自己,可能吗?如果这辈子一直穷下去,仇就不报了吗?
可是,要成为亿万富翁,该是多么难啊。
张长贵拿来消毒液,把张宽手臂上的牙印擦了擦,对他道:“凡事都会有个头绪,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做这么凶的梦,肯定是代表了什么。我觉得,从今往后,你得改改性子,凡事多为以后考虑,别动不动就匹夫之怒,要做枭雄,往前看,往远看。”
张宽闻言点头,“你说的对,如果梦里的事真成为现实,确实恐怖。”
张长贵又拿来一段挂着玉坠的红绳,给张宽系在手腕上,告诉他道:“玉这东西辟邪,你戴着,以后再想动手,不妨看这玉坠一眼,想想家里,能少结个仇家就少结个仇家,凡事都是如此,多条朋友多条路,只要不是生死之争,均可退步,有时候,吃亏是福。”
张宽沉默不语,细细思索父亲的话,虽然没有完全接受,但也记住一点,以后尽可能的不跟人争执,遇事必须三思而行。
早上起床,张宽正愁怎么去上班,张艳玲打来电话,说他要上班的话可以送。
张宽就纳闷了,自己那点好,值得人家女子如此倒贴?
其实世间男女之间不外乎如此,越是容易到手的越不珍惜,反而紧追那些难以驾驭的。张艳玲本是个实在的关中女子,骨子里带着关中女人的憨厚忠实,认定一个男人就不再改变,张宽初时为了娶她立下的豪言壮语让她暗生情愫,越想越觉得他好,一发不可收拾,此时想回头,已是不可能了。
而张宽则是出于男人的本分躲避张艳玲,并不是不喜欢她。
眼下见张艳玲又来,心说这样可不行,天天不是接就是送,时间久了,怕是连自己都把持不住,人家闺女又不是丑八怪,自己也不是什么柳下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见面。
如此一想,张宽忽然怀念自己的电瓶车,心说不如今天请一天假,去龙首村把电瓶车取回来。说走就走,张宽立即给徐迎春打电话,告诉她今天有事,休假一天。
业务员本来就和正式员工不同,工作相对自由,就是张宽说不请假,是去见客户,徐迎春也不会说半个不字,于是爽快地同意了。
至于若若那边,发个微信,让她多关注一下何校长的进度,毕竟,这可是有若若参与设计的服装啊。
若若很快回了信息,昨天晚上何校长看了APP,很满意,今天就拿去教育局,下午时候就会有消息。
张长贵听说儿子要去龙首村,又去村口小店买了许多礼品,告诉他说:“中秋快到,也给你师傅送点礼。”
当下,张宽就坐上了白色捷达,朝着龙首村驶去。
一路无话,一个不好意思说,一个故意装傻。张艳玲就打开了车载音响,里面传来好听的女声歌曲:如不是因为爱着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你,爱着你。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放弃……
听到这里时,张宽眼眶就不自觉地湿润了,这首歌唱的如诉如怨,词也写的好,刚好唱进张宽心里,莫名地让他感动,或许,张艳玲也是这么想吧。
一曲终了,两人相视一笑,张宽问道:“这歌叫什么名字?”
“《爱情》”张艳玲回答,“莫文蔚唱的,好听吧。”
“的确好听!”
车子行驶至龙首乡公路时,一辆拉猪车翻到在路,交警还未到,各种猪或躺或站挤满了路,一时无法通行,张艳玲只好停下车,在路边等。
因为张宽说了一句好听,张艳玲把《爱情》设置了个单曲循环,这下可就要了张宽老命,只觉得整颗心都融化在歌曲了,随着莫文蔚的声音,渴望甜蜜的爱情。
张艳玲也受了感染,慢慢的,车里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张宽强守着心中的信念,坚决不跟张艳玲再发生任何肢体接触,开口说道:“艳玲,如果到了三个月,我还没凑够钱,你会怎么办?”
张宽说这话的时候异常严肃,他已经打了腹稿,无论张艳玲说什么,他都回复,我觉得你父亲说的对,我配不上你,你是大学生,我是混混子,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所以,还是分开的好。
可是,随着莫文蔚的想你,想你,好想你的歌曲,张艳玲眨巴着眼睛,长长的睫毛抖动着,忽然做出连她自己都惊讶的举动。
她扑了过来,紧紧吻住了他。
这回,不是张宽说什么的问题,而是对方根本没给他辩解的机会。
这一吻,起先是如涓涓细流,绵延悠长,慢慢的演变成江河,波涛翻滚,最后成为大海,巨浪滔天。
张宽被张艳玲压在身下,手无处安置,睁大眼睛看着对方,忽然想起昨晚的梦,张艳玲那副高高在上趾高气扬的模样,说的那些侮辱讽刺的话,登时让他心里变的亢奋起来,奋力把她推回去,按倒在驾驶座上,像初生的牛犊,乱拱乱撞。
嘴里还夹杂着凶狠的话语,“你不是看不起我么?不是觉得我低贱么,现在又如何,还不是乖乖在我身下?”
张艳玲吓了一跳,大呼冤枉,“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
“昨天晚上。”张宽怒目而视。
“昨天晚上?”张艳玲大惊失色,结结巴巴地道:“昨天晚上我都没跟你说过话。”
“在梦里。”张宽气哼哼地道,“在梦里你看不起我,说我配不上你。”
张艳玲闻言一阵羞涩,脸红的像苹果,小声喃喃道:“你这人真是,梦里的事也怪我,我能那么说你,肯定是你在梦里做了不好的事。”
张艳玲这么一说,张宽也觉得无趣,动作停了下来,躺回副驾驶。
张艳玲见他萎靡不振的样子,猜不透他心里想什么,弱弱地道:“我没有看不起你,你,你只要不是那事,你做什么我都愿意。”说完这话,小姑娘的脸红极了,像熟透的螃蟹。
“真的吗?”张宽生了恶趣味,“那你解开扣子,我要吃奶。”
张艳玲看他一眼,又羞又恼,骂道:“滚,要吃自己解。”
听到这话,张宽就如虎一般的扑上去……
忽然,有人敲车窗,交警在车外道:“道路通了,可以走了,另外,系好安全套,路上别出意外。”
这番话说的两人都不好意思,赶紧分开,张艳玲慌忙用衣服盖上。那交警还指着路上的牌子,上面写着:开车不摸奶,摸奶不开车。
车子重新上路以后,张宽狠狠地给了自己一个嘴巴。张艳玲不解,“这是干啥?”
“我再惩罚我自己,管不好这张嘴。”张宽愁眉苦脸地答。
“怎么啦?嘴巴犯了什么错要挨打?”
“该说的话不说,不该做的事他又做了,所以他就得受罚。”张宽如此说。
张艳玲乜了他一眼,“切,明明是你思想不正经,又把责任推到嘴身上,如果真要怪,那你应该把那玩意给剪了,就啥错也不会犯。”说着用手指点了点,张宽低头一看,胯下早就立起鼓囊囊的一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