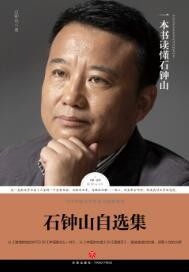八
马林看见细草蹲在后院茅厕旁的雪地上屙屎,风卷起地上的浮雪迅疾地在院子里跑荡。细草哆嗦了一下,然后用稚气的声音喊旋风旋风你是鬼,三把镰刀砍你腿……
马林恍惚记得自己小的时候,也曾冲着风这么喊过。他立在那里,看了细草一眼,又看了细草一眼,马林想,一切都该结束了。这么想完,他推开了下屋的门。
秋菊在屋内梳头,她面前摆了一个铜盆,盆里面盛着清水,一把缺齿的梳子握在秋菊的手里。以前马林无数次地看过秋菊梳头,那时的秋菊是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自从马林十六岁那一年和秋菊圆房之后,秋菊的两条辫子便剪了。秋菊的头发短了,但仍又浓又黑,秋菊的头发里有一股很好闻的气味。
此时,马林站在秋菊面前,他深吸了一口气,那股幽幽的淡淡的发香再一次飘进他的肺腑,他的身体里很深的什么地方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一时间他觉得自己口干舌燥。刚进门的时候,秋菊看了他一眼,看了他一眼之后便把头埋下了,目光落在少了齿的梳子上。他干干地说秋菊,我要休了你。
俺知道。秋菊摆弄着手里的梳子。
马林其实不想这么说话的,可不知为什么话一出口就变了味道。
他又说我要杀了鲁大。
她说俺知道。
他还说我不杀了鲁大,我就不是个男人。
她说这俺也知道。
他还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来。他立在那里,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不知为什么,他从内心里从没把秋菊当成老婆看过。他和秋菊房是圆了,男女之间的事也做过不知多少次了,可他仍没找到过她是他老婆的感觉。秋菊人不漂亮,可心眼善良,又会疼人,这一点他心里清楚。他在奉天城里爱上杨梅以后,那时他曾在心里发誓,这一生一世要好好待两个女人,一个是秋菊,另一个是就杨梅。他和杨梅还不曾结婚,就已经把杨梅当成自己的女人了。也许这是天意。
他记得小的时候,大冬天里爬到街心的老杨树上去掏乌鸦窝,乌鸦窝是掏下来了,却把他的一双小手冻得通红,回到屋里猫咬狗啃似的疼,秋菊就把他的双手捉了,握在自己的手里,用她嘴里的热气吹着他冻僵的小手,还是疼,热热的,麻麻的。再后来,秋菊就解开自己的棉袄把他一双小手揣进了自己的胸前,果然他就不疼了,只剩下了热,那热一直通过他的双手传到了他的全身。
秋菊就说还疼不?
他摇头。
秋菊又说以后还淘气么?
他不语,就笑。
秋菊似嗔似怒地扬起手在他的脑门上拍了一下。
还有一次,吃饭时马林不小心摔破了一只碗。
马占山心疼那个花边大瓷碗,马占山不仅心疼这些,他心疼家里的每一棵草,每一寸地。眼见着那个花边大瓷碗被马林摔得四分五裂,马占山暴怒了,心疼了。那时的马占山哮喘病还不怎么严重,于是人就显得很有力气。很有力气的马占山一把便把马林从炕上拽到了地上,嘴里骂着你这个小败家子呀,打死你呀。
于是马占山的巴掌一下下冲马林的头脸打来。
马林就叫爹呀,我不是故意的呀。
马占山不管儿子是不是故意的,他要让马林长记性,家里的每一片瓦每一棵草都是来之不易的。他扬起很有力气的巴掌,劈头盖脸地向马林打来。
秋菊站在一旁先是吓呆了,以前马占山曾无数次地这样打过秋菊,哪怕秋菊做饭时不小心浪费了一粒米,也要遭到马占山的一顿暴打。秋菊呆了片刻,便清醒过来了,她“呜哇——”一声便扑在马林的身上,泪眼汪汪地说爹呀,要打你就打俺吧,俺比他大呀。
那一次在马林的记忆里印象深刻。
在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秋菊在马林的心里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女人,温暖的女人。
北方的冬天奇冷,夜晚更是冷。
童年的马林和秋菊住在下屋,一个住南,一个住北。马占山为了节约柴火和几个长工挤在上屋的一铺炕上。马占山从不让秋菊在灶坑里多加一把柴火,于是屋里就很冷。马林每到入夜躺在冰凉的炕上冻得直打哆嗦,越冷越睡不着。他上牙磕着下牙在冰冷的被窝里哆嗦着,嘴里不停地吸着气。
秋菊在另一间屋里,中间隔着一道门,有门框却没有门。马林的吸气声显然是被秋菊听到了,她就问弟呀,你冷么?在没圆房以前,秋菊一直唤马林为弟。
冷,冷哩。马林哆嗦着答。
秋菊便从自己的被窝里爬了起来,很快地走过来,又很快地钻进了马林的被窝。她用自己的手臂紧紧地拥了马林。
马林觉得秋菊的身体又热又软,马林在秋菊的体温中渐渐伸张开了身体,又很快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马林睁开眼睛的时候,秋菊已经起来了。她有很多活儿要做,做饭、洗衣,还要喂猪喂鸡。但她的温暖仍在马林的被窝里残留着,那股淡淡的发香不时地在马林的身旁飘绕。从那时起,马林就很愿意闻秋菊的头发。
从那以后,只要马林一钻进被窝,他便冲秋菊那屋喊秋菊,我冷哩。
来啦。秋菊每次都这么答。
不一会儿,秋菊就过来了,轻车熟路地钻进他的被窝,用自己的身体为马林取暖。马林便在温暖的梦乡中迎来了又一个黎明。
后来,他们就都长大了,马林不好再叫秋菊为自己暖被窝了,秋菊也不过来了,最后一直到他们圆房。那一年他十六,她十八。
青春年少的两个身体再碰到一起时,当然那是另一番滋味和情调了。然而幸福的时光却是那么短暂。
在奉天城里,马林娶杨梅时,并没有想过要休了秋菊。秋菊是他的第一个女人,杨梅是第二个。在他和杨梅结婚前,这一点他已经和杨梅讲清楚了。杨梅不在乎,他也不在乎,一个在靠山屯,一个在奉天,也许这两个女人今生今世都不会相见的。没想到的是,世界变得这么快。她们在靠山屯相见了,又是在这种情况下相见的。
马林望着眼前既熟悉又陌生的秋菊,觉得有许多话要对秋菊说,可又不知说什么。
当他得知秋菊被鲁大抢到老虎嘴山洞,直到生完孩子才被送回时,那一晚马林是狂怒的,他恨不能拔出腰间的快枪,先一枪打死秋菊,再一枪结果了那个小野种。后来他就冷静了下来,要是几年前那一枪结果了鲁大,就不会有以后这些事了,要恨只能恨自己,是自己一时手软,留下了今天的祸根。但他也恨秋菊,心里曾千遍万遍地想过秋菊呀,鲁大奸了你,你当时咋就不死呀——你要是死了,我就只剩下对鲁大的仇了,我要杀上他千次万次,为你报仇,为你雪恨。我还要在你的坟头,烧上一刀纸,为你哭,为你歌——可眼下却不一样了。
马林觉得,眼下他做的只能是休了秋菊了,从今以后和秋菊没有关系了,然后杀了鲁大,鲁大在腊月二十三的正午不是要送上门来吗?然后一了百了了。
马林这么想着,门“吱嘎”一响,细草走进屋内,他的一张小脸冻得通红。
细草对马林已不再感到陌生了,他瞪着一双黑眼睛仰着头盯着马林,稚声稚气地问你是谁,以前我咋没有见过你。
马林下意识地拔出了腰间的枪,乌黑的枪口冲着细草,他咬着牙说小野种,我一枪崩了你!
秋菊“呀——”地叫了一声,“咣啷”把手里那把缺齿的梳子扔到了地上,她扑过来,弯下腰死死地抱住细草,一双眼睛惊惧地望着马林。
细草在秋菊的怀里挣扎两下,不谙世事地冲马林说我娘说了,我不是野种。
秋菊站起身,紧紧抱着细草,哽了声音说马林,你对俺咋的都行,你不要伤害孩子。
细草声音很亮地说娘不怕,怕他干啥。
秋菊低了声音又说咋的,他也是俺的骨肉,要是没有细草,俺早就死过千回万回了,你马林也不会在今天看到俺了。秋菊说完放声大哭起来。
马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怔怔地站在那儿,愣愣地看着手里的枪。马林就想秋菊我要休了你,休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九
马林走进了村里教私塾的钱先生家,钱先生的家门是紧闭着的,马林没有叫门,他推了两次才把钱先生的门推开。
钱先生是全村唯一有学问的人,全村的大事小情,凡是需要写文书、契约的都请钱先生。小的时候,马林在钱先生家读了三年私塾。马林和秋菊圆房时,就是请钱先生写的契约。
钱先生家里显得很乱,钱先生和女人正齐心协力地把头扎在炕柜里往外翻东西,炕上一溜摆满了春夏秋冬的衣服。两个人撕撕巴巴地仍从炕柜里往出掏东西。马林不知钱先生这是要干什么。
马林咳了一声,钱先生这才发现屋地中央站着的马林,钱先生愣怔了一阵,待明白过来之后,慌慌地用身体把柜门掩了,语无伦次地说大侄呀,你啥时回来的?
马林掏出盒纸烟,先递一支给钱先生。钱先生摆手,马林也没再让,自己点燃一支吸了,他一抬屁股坐在钱先生家的炕沿上。
马林说钱先生,秋菊的事你也知道了。
钱先生白了一张脸,先是点头,又是摇头,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
马林不理会这些,仍说下去今天有个事来求你,就是请你帮我写份休书。
钱先生直到这时才镇静下来,马林不知道钱先生为什么要这么慌乱,他是来请钱先生写休书的,钱先生慌不慌乱和自己是没关系的。
钱先生镇静下来之后就说大侄哇,你休秋菊是不?
马林点点头。
休吧,该休哩,休了秋菊就一了百了了。钱先生又说。
马林淡笑一次。
钱先生就冲仍愣怔在那里的女人说还不快给我找来纸笔。
女人应一声,慌慌地便找来纸笔。
钱先生在很乱的炕上摊开了纸笔,钱先生写这种物件驾轻就熟,很快便为马林写好了休书,并一式两份。马林便把休书叠好揣了,从怀里掏出两块银元扔在钱先生家的炕上。
钱先生就说大侄哇,这是干啥。说完,还是把钱塞到一个破包袱里。马林说过谢话便走出了门。
钱先生又追了出来,压低了声音道大侄哇,杨树上那个帖子你可看了?
马林不明白钱先生为何要问这,便淡笑一次,踩着雪,揣着休书“吱吱嘎嘎”地走去。
腊月二十二的正午仍旧很冷,冻得马林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马林走回自家院落的时候,看见杨梅在正房门前的雪地上堆一个雪人。那雪人已见规模了,身子很大,头却极小,似一个怪物。杨梅堆雪人时一脸的灿烂又一脸的天真。杨梅看见走回来的马林说这里的雪可真大。
马林说钱先生把休书写好了。
说完,马林伸手往外掏休书,杨梅说我不看,休不休秋菊是你的事,我不在乎。
马林便把手停住了。他拾了一次头,看见天空灰蒙蒙的,太阳似一个冰冷的光球,在遥远的空中亮着,一点也不灿烂,也不耀眼,于是整个世界都显得灰蒙蒙的,像此时马林的心情。
马占山在地窖口坐着,他在那里已经坐得有些时辰了。马家的积蓄除掉这个院落,还有那些土地,其他的都装在这个地窖里了。地窖里存放着一些白菜,还有一些土豆,更主要的还有两罐子银元。那是马占山大半辈子的积蓄,也是马占山的命。
两罐子银元早就被马占山埋在地窖的土里了,他不放心,又在土上堆满了烂白菜和土豆。地窖里因长年不透风,陈年的霉味直呛鼻子。可马占山喜欢闻这股霉味,他一天闻不到这股腐烂的气味,他心里就不踏实,觉也睡不着。他每天都要在很深的地窖里爬上爬下几回,为了掩人耳目,他每次爬上爬下从来不空着手,手里不是攥两个土豆,就是举着一棵烂白菜。白天里,没事可干的时候,他都要长时间地钻到地窖里守望,他待在那里,才感到安全、可靠。
鲁大要来了,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菜窖。自从早晨看见自家门上的帖子后,他便在地窖那里守望有些时候了。地窖口不大,用两捆谷草堆了,谷草上还压了块石头,马占山仍放心不下。他从门前的空地上,又搬来一块石头,用自己和那块石头一起压在地窖口上。干这些时,马占山拼命地喘息,他的气管仿佛是一只破风箱。
马林望见了自己的父亲马占山,马占山不望他,仰了头眯了眼,冲着昏蒙的天空费劲地想着什么。马林咽了口唾液,又收回目光看了一眼仍专心致志堆雪人的杨梅,怀孕五个多月的杨梅虽穿着肥大的棉袍,腰身还是明显地显露出来。
他心里热了一下,想冲杨梅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什么也没说,扭过头,向下房走去。
秋菊背对着门坐在炕上,细草睡着了。窗纸透进一片光,一半照在细草熟睡的脸上,一半照在炕席上。马林走进来,秋菊连头也没回,她在一心一意地望着睡着的细草。
马林立在秋菊身后,立了一会儿,又立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在怀里掏出那两份休书,把一份放在炕上,另一份又揣在自己的怀里。马林做完这些时,纷乱的心情平静了一些。
马林说这一份你拿了吧。
秋菊没有动,似乎长吁了口气。
马林想走,又没走,侧身坐在炕沿上,他望着秋菊的后背说你进马家这个门也这么多年了。
马林看见秋菊的肩在一耸一耸地动,他知道,她哭了,却无声。
马林又说你也不易。
秋菊的肩在抖,整个身子都在抖,像风中的树叶。
马林说你是无路可走了,才到的马家,关外你也没啥亲戚,我休了你,你也没个去处,这我想过,以后你还住在这里,愿住多久就住多久。
秋菊的身子不抖了,她隐忍着说不。
马林惊愕地望着秋菊的背。
秋菊说不,俺走,最快明天晚上,最迟后天。
马林又掏出烟点燃,深一口重一口地吸。
马林说我知道这事不能怪你,只怪我没有杀死鲁大。停了停他又说你应该明白,虽说不是你的错,可我马林不能再要被胡子睡过的女人。
马林说到这儿又看了一眼睡在炕上的细草。
秋菊终于哽了声音说俺谁也不怪,怪俺当时没有死成。要是死了,俺的魂也会是你马家的鬼。
马林夹烟的手哆嗦了一下,于是又狠命地抽了口烟。
马林说告诉你秋菊,你哪儿也不要去,我马林是个男人,以后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秋菊不再哽咽了,声音清晰地道马林俺不是那个意思,俺要看你亲手杀了鲁大。
马林下意识地又摸了一下腰间的枪,他的嘴角掠过一丝冷笑,仿佛此时鲁大就在眼前,他的枪口已对准了鲁大的头。
秋菊还说俺会走的,走得远远的,俺要把发生的一切都忘掉。
秋菊说完转过身来。马林看见秋菊满脸的泪痕。
秋菊说马林求求你,你这次一定要杀死鲁大。
在秋菊求救似的目光中,马林点了点头。
秋菊说马林,你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说啥也不行,鲁大手下不是几年前的十几个人啦,他手下有几十人。
马林说十几个几十个其实都一样。
马林说完又掏出腰里的两把快枪,很自信地在手里把玩。
秋菊说不,你一个人不行,鲁大也不是几年前的鲁大了,他为了报仇,这些年天天在老虎嘴的山洞里练枪,他一口气能打灭十个香火头。
马林抬起头,认真地看了眼秋菊。秋菊也正在望他。他从她的眼睛里似乎又看到了少年秋菊的影子,他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秋菊躲开马林的目光,望着他的头顶说像当年一样,你要叫上耿老八、狐狸于、刘二炮,他们和鲁大都有仇,让他们一起来帮你。
两滴泪水顺着马林的脸颊流了下来,他不知道自己这是咋了,他不能也不应该在秋菊这样的女人面前流泪。他恨不能打自己两个耳光。
秋菊说鲁大心狠手黑,到时候你一定要当心才是。
马林点了点头。他握枪的手有些抖,此时他觉得腊月二十三的正午有些太晚了,太漫长了,让他等得心焦。
他站了起来,他想自己在秋菊这儿待的时间太长了,他应该走了。可他的双腿却无法迈出。
他终于说你不走不行么?
秋菊摇了摇头。
马林又说你真的要走,我也不拦你,我会给你带够你一辈子的花销。
她说不!
接下来,两人都沉默了,他们都在想着各自的心事。
不知过了多久,她说她好么?
他怔了一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待反应过来后说城里人,娇贵。
她不语了,低头又想了想说今晚俺给你们做一床狗皮褥子吧,这不比城里,寒气大。
他没点头,也没有摇头,望着她。
她低下头又说她有身子了,几个月了?
他答快六个月了。
她说莫让她乱动,怕伤了胎气。
说完,她吁了口长气。
他说那我就走了,啥时候走,告诉我一声。
说完,他真的转过身。
这时她叫一声哎——
他立住了,回身望她。她以前就是这么叫他。他望着她。她把他留在炕上的那份休书拿了起来,认真地看了几眼。他知道她不认识那些字,但她还是看了,每一眼都看得极认真。
半晌,她说过一会儿俺做一点糊糊,把它贴到老杨树上去。
他说不,不用,钱先生会把话传出去的。
她吁了口气,沉重地把那份休书举了,悠悠地说还是贴出去好,让靠山屯的人都知道,从现在起,俺秋菊再也不是马家的人了。
马林逃跑似的离开了下屋,当他关上门时,秋菊的哭声潮水似的从门缝里流泻出来。马林背靠着门,在那儿茫然无措地立了一会儿。
他听见细草说娘,娘,你咋了,咋了?
马林的心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
十
太阳偏西的时候,秋菊把休书贴到了老杨树上。这是马林不愿看到的一幕。
此时,靠山屯仿佛死了。家家户户仍门窗紧闭,街上一个行人也没有。一只发情的母狗冲着老杨树上那张休书愤愤不平地叫着,疯子耿莲不知在什么地方喊来呀,你们都来干我呀。
细草已经醒了,他站在下屋的门前冲着雪地撒尿,小一抖一抖的。撒完尿的细草就看到了杨梅已堆完的雪人,那个雪人仍旧头小肚子大,怪物似的立在那儿。细草走过去,绕着怪物似的雪人走了两圈,他说咦——咦——
杨梅弯下腰看细草。
细草说这雪人是你么?
杨梅笑了笑,没有说话。
细草又说你从哪儿来,我咋不认识你。
杨梅仍弯着腰说你叫什么?
细草说我叫细草,俺娘给起的。
杨梅不笑了,愣愣地望着细草。
马占山仍坐在地窖的石头上,阴森古怪地朝这面看。只要他的视线里出现细草的身影,他的目光便阴森得怕人。
当初鲁大放回秋菊和细草时,鲁大冲马占山说了一番话。
鲁大当时就用那只阴森古怪的独眼望着马占山。
鲁大说老东西你听好,秋菊是马林的女人,今儿个我送回来了,你对她咋样我管不着,细草可是我的儿子,要是细草有一丝半点差错,你老东西的命可就没了。
当时马占山就是坐在地窖口的石头上听鲁大那一番话的。
他没有说话,却在拼命地喘。
鲁大又说老东西,我和你儿子的仇是你死我活,我不想把你咋样,要是现在要你的老命也就是我吹口气的事。
鲁大说完,吹了吹举到面前的枪口。
马占山闭上了眼睛,他在心里说白菜烂了,土豆也烂了。
鲁大又说秋菊是马林的女人,是杀是休那是你儿子的事,在马林没回来以前,秋菊还在你这吃,在你这住,要是在你儿子回来前,秋菊不在了,我会找你要人,你听好啦。
马占山的心里又说都烂了。
鲁大说完这话,便带人走了。鲁大走时在他脚前扔了两块银元,他盯着那两块银元好久,后来把银元飞快地拾了,钻进了地窖里。
从那以后,他不再和秋菊说一句话了,阴森地望着秋菊娘俩。
秋菊回来不久的一天,给他跪下来,跪得地久天长。刚开始秋菊不说话,只是以泪洗面。最后秋菊说爹,俺对不住你,对不住马林。
马占山又在心里说都他妈的烂了。
秋菊说爹,你杀了俺吧。
马占山拼命地喘着。
秋菊又说爹,你杀了俺,俺心里会好过些。
马占山在这之前是闭着眼睛的,这时睁开眼睛说以后你不要叫我爹了,我承受不起。
从那以后,秋菊果然再没有叫过马占山一声爹。秋菊像从前一样,屋里屋外地忙碌,洗衣、做饭、喂猪、喂鸡。
每天做好饭菜她总要给马占山盛好,送到马占山房间里去,马占山扭过头不望她。马占山拒绝着秋菊,却不拒绝秋菊的饭菜,他总是把秋菊送来的饭菜吃个精光,然后呼哧呼哧地走到田地间做活儿去了。
也是刚开始时,细草很怕马占山的眼神。其实秋菊一直在避免马占山和细草相遇,三口人在一个院子住着,不可能没有碰面的时候。细草每次见到马占山就吓得大哭,渐渐细草大了,习惯了马占山的眼神,便不再哭了。
那一次中午,马占山扛着锄出门去做活路,迎面碰见了细草。细草小心地望着马占山走过去,在马占山身后小声地叫爷爷。这一声,使马占山的身子哆嗦了一下,似被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身子嘎了一下,半晌扭过头,凶凶地望着细草,恶声恶气地说谁让你叫的?!细草吓白了脸,忙慌慌地说你不是我爷爷。
马占山这才长出口气,扭过头喘着走了。
细草咬着指头,呆呆地望着远去的马占山的背影。直到秋菊走过来,细草才恍怔地道他不是爷爷。
秋菊狠狠地打了细草一掌,恶声恶气地道不许你叫,以后再叫看俺不剥了你的皮。
细草吓得大哭不止。
马占山觉得秋菊是应该死在老虎嘴的山洞里的,若是死了,秋菊的魂还是他马家的鬼,逢年过节,他会为她烧两张纸,也会念着她活着时的好。出乎他意料的是,秋菊却没死,又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个胡子种。马占山的日子颠倒了。
那些日子,他盼儿子马林回来,又怕马林回来,他就这么盼着怕着熬着难受的时光。他曾在心里千遍万遍地说儿呀,你杀了她吧,杀了这个贱女人吧。
马林休了秋菊,马占山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相反,马占山觉得这样太便宜贱女人秋菊了。他又想既然儿子马林不杀秋菊,那就让她和那个野种多活两天,等马林杀了鲁大,再杀贱女人和那个小野种也不迟。马占山甚至想好了杀秋菊和细草的工具,就用自家那把杀猪刀。马占山年轻时能把一头猪杀死,于是他想连猪都能杀,难道就不能杀这个贱女人么。
马占山在腊月二十二的那天下午开始磨那把锈迹斑驳的杀猪刀了,他一边磨刀一边喘。
杨梅好奇地看着马占山不解地问爹,你这是干啥?
明天就是小年哩,要杀猪哩。马占山这么答,喘得愈发无法无天了。
在杨梅的眼里,马占山这个老头挺有意思的。
马占山认为眼前这位细皮嫩肉的女子不是当老婆的料,马林和这样的女子以后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马占山觉得,马家从此就要败落了,马占山一边磨刀,一边生出了无边的绝望感。他想,人要是没有了奔头,活着就没意思了。
马占山眼前的理想是先杀了贱女人秋菊和野种细草,然后再和儿子商量是不是也休了眼前这位叫杨梅的女人。到那时,马家是充满前途和希望的。马占山又想到了地窖里那两罐子白花花的银两。想到这儿,马占山又快乐起来,他更起劲地磨着杀猪刀了。
十一
太阳又西斜了一些,天地间便暗了些,西北风又大了一些,吹得村中那棵老杨树一片疯响。村中仍静静的,不见一个人影,两只饥饿的黑狗匆匆忙忙地从街心跑过,凛冽的风中传来疯女人耿莲的喊声来呀,你们咋不来干我了。
这种反常的景象马林并没有多想,他也无法意识到,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正在一点点地向靠山屯走近,向马家走近。
马林站在院子里,望着清冷的寂寞的靠山屯,心里竟多了种无着无落的情绪,这种情绪很快在他的周身蔓延开了。
马林并不希望秋菊把休书张贴在老杨树上,他下决心休秋菊,并不是冲着秋菊的,他是冲着鲁大。他知道鲁大的险恶用心,这比杀了秋菊杀了他还要令他难受百倍千倍。他下决心休秋菊是要让鲁大和众乡人看一看,告诉众人,秋菊只是个女人,像我马林的一件衣服,我马林说换也就换了,鲁大你爱奸就奸去,爱娶就娶去,秋菊原本和我马林并没什么关系,说休就休了。
他想潇洒地做给鲁大和众人看一看,他快刀斩乱麻地做了,回家后的第二天他就把该做的做了,剩下的时间里,他就要一心一意地等鲁大送上门来了。马林想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本应该轻松一下。要在平时,自家的院子里早就聚满了乡人,他们来看从奉天城里回来的马林,快枪手马林是靠山屯的骄傲。可这一切在腊月二十二这一天没有发生。腊月二十二这一天靠山屯似乎死去了。
下屋门开着,马林看见秋菊在收拾自己的东西,属于秋菊的东西并不多,只是一些简单的换洗衣服,装在一个包袱里。秋菊做完这些便坐在下屋的炕上,痴痴地发呆。细草站在门口望着院子里被风刮起的浮雪喊旋风旋风你是鬼,三把镰刀砍你腿……
看到这些,马林的心里疼了一下,又疼了一下,往事如烟如雪。
秋菊这种忧戚的面容他是见过的。那是他每次从奉天城里回来,住几日之后要走的时候,每次秋菊都是这般神情。在还没认识杨梅以前,那时的奉天城里还算太平,马林每年都能回靠山屯住上几日。但也就是几日。那时马林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属于靠山屯了,他是东北军里著名的快枪手,是大帅张作霖身边的人,他不属于自己,一切的命运和东北军的命运紧紧系在一起了。
马林回靠山屯的日子很平淡,没住上几日便匆匆地返城了。
在马林回家的这些日子里,马占山和马林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了,他在翻来覆去地说他的那些地,说他的粮食。
马占山冲马林说这些时,马林的目光是虚幻的,他一直这么虚幻地望着爹那张苍老的面孔。
爹说咱家的地越来越大了。
爹又说这回你带回来的钱又够置二亩水田的了。
爹还说耿老八家南大洼那块地他不想要了,到秋咱就买下来。
爹继续说以后咱就要把靠山屯的地都置下来,这是你爷活着时做梦都梦不见的好事。
说到这儿,爹就咧开嘴无限美好地笑,也喘吁吁的。
马林收回虚虚的目光说爹,你治一治病吧,置那些地干啥,有多少地就受多大罪。
马占山不高兴了说咦——这地,这家以后还不都是你的。
马林不说话了,虚虚的目光中他又看见了秋菊。秋菊整日忙碌着,这个家她有忙不完的事情。在这个家里,秋菊从来不多说一句话。
马占山就喘着气说你也该有个孩子了,要生就生男的。咱马家这么多代了,一直是单传,现在咱有地了,本该人丁兴旺些才好。
说到这儿父亲就叹气了。
马林一年也就回来这么一两次,在家住的日子屈指可数。秋菊的肚子一直瘪着。
让马林惊奇的是,秋菊的想法和爹的愿望如出一辙。每次马林回来,秋菊都在黑暗中的炕上冲他说俺想要个娃,是男娃。
马林在黑暗中不说什么,突然抱紧了肥肥壮壮的秋菊。经年的劳累使秋菊的身体变得粗糙而又结实。不是生孩子的念头使马林抱紧了秋菊,而是年轻人的冲动。年轻的马林有使不完的力气,干渴的秋菊有着丰富的念头。短暂的日子,对秋菊来说是一年中最幸福的几日。
马林终于走了,秋菊便一脸的忧戚。
马林骑在马上,两支乌黑的快枪在两边的腰上,悠荡着。秋菊送马林,走在地下,细碎的马蹄声伴着秋菊无奈的脚步声在靠山屯的小路上响起。
马林说你回吧。
秋菊不回,仍低着头随在马旁向前走。
半晌,秋菊终于拾起一双泪眼,忧忧戚戚地说你还啥时候回呀?
秋菊的表情和语调令马林的心揪紧了。不知为什么,一回到靠山屯,一看到秋菊的样子,他的心就乱七八糟的。
马林说也许今年,也许明年。
秋菊又不语了,紧走几步,从怀里掏出昨夜晚为马林准备好的路上带的食物,递给马林道包里有饼有蛋。
饼是油饼,蛋是咸蛋。这是马林平时最爱吃的。只有马林回来时,马占山才让秋菊动一动白面和蛋,这是过年马家也舍不得吃的食物。马林把吃食接过,暖暖的,温温的。马林知道,那是秋菊的体温。
马林不想再这样儿女情长下去了,于是松开马缰,在马的屁股上拍了一掌冲秋菊道你回吧。
马便小跑着向前奔去。
秋菊快走几步,那样子似要追上那匹马,终于不能,于是便无奈地立住脚,望着马林的身影在视线里愈来愈小。
远去的马林是也回了一次头的,秋菊的影子已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再回过头来的时候,马林揪紧的心一点点地松弛下来了。心离靠山屯和秋菊越来越远了,离奉天城里那个著名的快枪手越来越近了。马林在东打西杀的日子里,靠山屯的一切在他心里日渐模糊了。
在腊月二十二太阳已经偏西的辰光中,马林看到秋菊,心又一次莫名地揪紧了。眼前这一切恍若隔世,已物是人非了。马林站在西斜的阳光中,仿佛做了一场梦。
马林又想到了腊月二十三的正午,他的嘴角又闪过一丝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