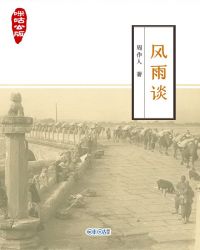鸦片事略
鸦片事略
查旧日记第二册,在戊戌(一八九八)十二月十三日下有一项记事云:
“至试前,购《思痛记》二卷,江宁李圭小池撰,洋一角。”小池于咸丰庚申被掳,在长毛中凡三十二月,此书即记其事,根据耳闻目睹,甚可凭信,读之令人惊骇,此世间难得的鲜血之书也。我读了这书大约印象甚深,至民国十九年八月拿出来看,在卷头题字数行云:
“中国民族似有嗜杀性,近三百年张李洪杨以至义和拳诸事即其明征,书册所纪录百不及一二,至今读之犹令人悚然。今日重翻此记,益深此感。呜呼,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乎。”
李小池后来做了外交官,到过西洋,著有游记等书,我未得见。孙彦清《寄龛丙志》卷四云:
“近阅李小池圭《游览随笔》,载强水棉花,云以强水炼成,有干湿两种,干者得火即发,湿者置火中可以二刻不燃,以电线发之,方三寸,厚寸许,重不过二两者,百步外能震巨石成齑粉。”所记盖是棉花火药欤。又所著有《鸦片事略》,近日在北平市上获得一部,其价却比《思痛记》要高了三十倍了。书凡两卷,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刻,后于《思痛记》十五年,板式却是一样,很觉得可喜。卷首说明著书的宗旨云:
“鸦片为中国漏卮,为百姓鸩毒,固尽人知之,而其于郡县流行之本末,禁令弛张之互用,与夫英人以售鸦片而兴戎乞抚,又以恶鸦片而设会劝禁,三百年来之事,则未必尽人知之。用就见闻所及,或采自他书,或录诸邮报,荟萃成此,附以外国往来文牍,曰‘鸦片事略’。”由此可知这是鸦片文献的重要资料,北平图书馆之有翻印本也可以作证,我所留意的却不全在此,只是想看看中国人对于鸦片的态度,其次是稍找民俗的资料而已。这种材料在道光十八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奏中找得一点,乃是关于烟具的:
“查吸烟之竹杆谓之枪,其枪头装烟点火之具又须细泥烧成,名曰烟斗。凡新枪新斗皆不适口,且难过瘾,必其素所习用之具,有烟油积乎其中者,愈久而愈宝之。此外零星器具不一而足,然尚可以他具代之,唯枪斗均难替代,而斗比枪尤不可离。”又云:
“如烟枪固多用竹,亦间有削木为之,大抵皆烟袋铺所制,其枪头则裹以金银铜锡,枪口亦饰以金玉角牙,又闻闽粤间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其烟斗自广东制者以洋磁为上,在内地制者以宜兴为宝。恐其屡烧易裂也,则亦包以金银,而发蓝点翠,各极其工。恐其屡吸易塞也,则又通以铁条,而矛戟锥刀,不一其状。”在奏折中本来不易详叙,却也已写得不少,很是难得,所云甘蔗枪在小时候曾经看见过,烟斗与烟签子也有种种花样,这倒都是中国的自己创造。《鸦片事略》卷上记罂粟花云:
“产土耳基波斯多白花白子,产印度者两种,一亦白花白子,一红花黑子,平原所植俱白花,出喜马拉山俱红花。法国人以其子榨油,香美,颇好之,英人亦用其浆为药材。印人则取干块为饼,嚼食款客,南洋诸岛有生食者,俾路芝以西各部酋皆酷嗜之,亦生食也。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滤去渣滓复煮,和烟草末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又云:
“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我曾听说鸦片烟的那种吸食法是中国所发明,现在已得到文献的证明了,烟具的美术工艺虽然是在附属的地位,但是其成绩却亦大有可观也。
中国人对于鸦片烟的态度是怎样呢?人民似乎是非吃不可,官厅则时而不许吃时而许吃,即所谓禁令张弛之互用也。雍正中的办法是:
“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吸食者没有关系。嘉庆中改正如下:
“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道光中议严禁,十九年五月定有章程三十九条,中云:
“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
“一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
“一制卖鸦片烟具者照造卖赌具例分别治罪。”三年后江宁条约签字,香港割让,五口通商,烟禁复弛,至于戊戌。《事略》卷末论禁烟之前途云:
“今日印度即不欲禁,风会所至,非人力能强,必有禁之之日,禁之又必自易罂粟而植茶始。中国土烟既收税厘,是禁种罂粟之令大弛,民间种植必因之渐广,或至尽易茶而植罂粟,数十年后中国或无植茶地,印度则广植之,中国无茶以运外洋,印度亦无鸦片以至中国,漏卮塞矣,利源涸矣,而民间嗜食者亦必犹淡巴菰之人人习为固常,则亦不禁之禁,弛而不弛矣。”这一节文章我读了好几遍,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似讽刺,似慨叹,总之含有不少的幽默味,而亦很合于事实,又不可不谓有先见之明也。现今鸦片已不称洋药而曰土药,在店吸食则云试药,早已与淡巴菰同成为国货矣,中国自种罂粟而印度亦自有茶,正如所言,然则鸦片烟之在中国恐当以此刻现在为理想的止境欤。
一八七五年伦敦劝禁鸦片会禀请议院设法渐令印度减植罂粟,议院以四端批覆,其首二条云:
“鸦片为东方人性情所好,日所必需,一也。华人自甘吸食,与英何尤,二也。”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言请弛鸦片之禁,中有云:
“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这些话都似乎说得有点偏宕,实在却似能说出真情,至少在我个人看去是如此。去年四月里写了一篇《关于命运》,末后有一节话是谈这个问题的,我说:
“第一,中国人大约特别有一种麻醉享受性,即俗云嗜好。第二,中国人富的闲得无聊,穷的苦得不堪,以麻醉消遣。有友好之劝酬,有贩卖之便利,以麻醉玩耍。卫生不良,多生病痛,医药不备,无法治疗,以麻醉救急。如是乃上瘾,法宽则蔓延,法严则骈诛矣。此事为外国或别的殖民地所无,正以此种癖性与环境亦非别处所有耳。我说麻醉享受性,殊有杜撰生造之嫌,此正亦难免,但非全无根据,如古来的念咒画符读经惜字唱皮黄做八股叫口号贴标语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画,或以声音,均是自己麻醉,而以药剂则是他力麻醉耳。”我写此文时大受性急朋友的骂,可是仔细考察亦仍无以易吾说,即使我为息事宁人计,删除口号标语二项,其关于鸦片的说法还是可以存在也。至于许君所说,不佞亦有相同的意见,不过以前只与友人谈谈而已,不曾发表过。但是,这里也有不同的地方。许君只说烟民都是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所以大可任其胡里胡涂的麻醉到死,社会的事由不吃鸦片的人去做,只消多分担一点子也就可以过去了。若照我的看法,麻醉的范围推广了,准烟民的数目未免太多,简直就没有办法。对于真烟民向来一直没有法子,何况又加上准烟民乎,我想大约也只好任其过瘾。写到这里乃知李小池真有见识,我读其《思痛记》将四十年犹不曾忘,今读《鸦片事略》,其将使我再记忆他四十年乎。
(廿五年四月九日,北平。)
附记
上文写了不久就在《实报》上看见王柱宇先生的两篇文章,都很有价值,十一日的一篇是谈烟具的,有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十日的文章题为“土药店一瞥”,记北平樱桃斜街的鸦片烟店情形,更是贵重的资料。今抄录一部分于下:
“我向柜上说了声,掌柜辛苦。他说,你买什么?我说,借问一声,我买烟买土,没有登记的执照,可以吗?他说,有钱就卖货,不要执照,因为从我们这里买去的烟或是土,纸包上都贴有官发的印花,印花上边印着一条蛇一只虎,纸的四角印有毒蛇猛虎四字,这种意思便表示是官货,不是私售。”后来掌柜的又说,“你如果愿意在这里抽,里边有房间,每份起码两角。”此即报上所记的“试药”,吾乡俗语谓之开烟盘者是也。王先生记其情景云:
“楼上楼下约莫有五六间房,和旅馆相仿佛。我在各房看了一遍,每房之中有两炕的,有三炕的。一炕之上摆着两个枕头,每个枕头算是一号买卖。这种情形又和澡堂里的雅座一样。不过,枕头虽白,卧单却是蓝色的。”我真要感谢作者告诉我们许多事情,特别使我不能忘记的是那毒蛇猛虎的印花,很想得他一张来,这恐怕非花二元四角去买一两绥远货不可吧。代价是值得的,只是这一两土无法处置,所以有点为难。
(四月十二日又记。)
补记
从来薰阁得李小池著《环游地球新录》四卷,盖光绪丙子(一八七六)往美国费里地费城参观博览会时的纪录,计美会纪略一卷,游览随笔二卷,东行日记一卷。自序称尝承乏浙海关案牍十有余年,得德君(案税务司德璀琳)相知之雅,非寻常比,于是荐由赫公(案总税务司赫德)派赴会所。查《思痛记》陷洪军中共三十二月,至壬戌(一八六二)秋始得脱,大约此后即在海关办事,《思痛记》刊于光绪六年,则还在《新录》出板二年后了。上文所引强水棉花见于游览随笔下英国伦敦京城篇中,盖记在坞里治军器局所见也。篇中又讲到太吾士新报馆,纪载颇详,结论云:
“窃观西人设新报馆,欲尽知天下事也。人必知天下事,而后乃能处天下事,是报馆之设诚未可曰无益,而其益则尤非浅鲜。”李君思想通达,其推重报纸盖比黄公度为更早,但是后来世间专尚宣传,结果至于多看报愈不知天下事,则非先哲所能料及者矣。东行日记五月初一日在横滨所记有云:
“洋行大小数十家,各货山积,进口多洋货,出口多铜漆器茶叶古玩,而贩运洋药商人如在中华之沙逊洋行者(原注,沙逊英国巨商,专贩洋药)无有也。盖日本烟禁极严,食者立治重法,国人皆不敢犯禁,虽是齐之以刑,亦可见法一而民从。惜我中华不知何时乃能熄此毒焰。”亦慨乎其言之。
(五月四日加记。) 咪咕公版·风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