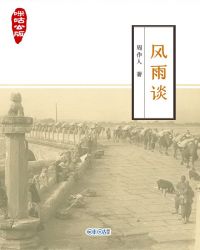关于家训
关于家训
古人的家训这一类东西我最喜欢读,因为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的诚实,虽然有些道学家的也会益发虚假得讨厌。我们第一记起来的总是见于《后汉书》的马援《诫兄子严敦书》,其中有云: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这段文章本来很有名,因为刻鹄画虎的典故流传很广,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乃是他对于子侄的诚实的态度。他同样的爱重龙伯高杜季良,却希望他们学这个不学那个,这并不是好不好学的问题,实在是在计算利害,他怕豪侠好义的危险,这老虎就是画得像他也是不赞成的。故下文即云:
“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后人或者要笑伏波将军何其胆怯也,可是他的态度总是很老实近人情,不像后世宣传家自己猴子似的安坐在洞中只叫猫儿去抓炉火里的栗子。我常想,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负责任。谢在杭的《五杂组》卷十三有云:
“今人之教子读书不过取科第耳,其于立身行己不问也。……非独今也,韩文公有道之士也,训子之诗有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之句,而俗诗之劝世者又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语,语愈俚而见愈陋矣。”这也可以算是老实了罢,却又要不得,殆伪善之与怙恶亦犹过与不及欤。
陶集中《与子俨等疏》实是一篇好文章,读下去只恨其短,假如陶公肯写得长一点,成一两卷的书,那么这一定大有可观,《颜氏家训》当不能专美了。其实陶诗多说理,本来也可抵得他的一部语录,我只因为他散文又写得那么好,所以不免起了贪心,很想多得一点看看,乃有此妄念耳。《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赵敬夫作注将以教后生小子,卢抱经序称其委曲近情,纤悉周备,可谓知言。伍绍棠跋彭兆荪所编《南北朝文钞》云:
“窃谓南北朝人所著书多以骈俪行之,亦均质雅可诵,如范蔚宗沈约之史论,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斯皆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诚使勒为一书,与此编相辅而行,足为词章家之圭臬。”这一番话很合我的意思,就只漏了一部《颜氏家训》。伍氏说六朝人的书用骈俪而质雅可诵,我尤赞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即《盘谷序》或《送孟东野序》也是如此。唐宋以来受了这道统文学的影响,一切都没有好事情,家训因此亦遂无什么可看的了。
从前在涵芬楼秘笈中得一读明霍渭崖家训,觉得通身不愉快。此人本是道学家中之蛮悍者,或无足怪,但其他儒先训迪亦是百步五十步之比。在明末清初我遇见了两个人,傅青主与冯钝吟,傅集卷二十五为家训,冯有家戒两卷,又诫子帖遗言等,收在《钝吟杂录》中。青主为明遗老中之铮铮者,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非凡夫所及,钝吟虽儒家而反宋儒,不喜宋人论史及论政事文章的意见,故有时亦颇有见解能说话。家戒上第一节类似小引,其下半云:
“我无行,少年不自爱,不堪为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岁读古圣贤之书,至今六十余年,所知不少,更历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谆谆之言非所乐闻,不至头触屏风而睡,亦已足矣。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未必无益也。”我们再看《颜氏家训》的《序致》第一云: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耳。”两相比较,颜文自有胜场,冯理却亦可取,盖颜君自信当为子孙所信,冯君则不是这样乐观,似更懂得人情物理也。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六云:
“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义大利诗人勒阿巴耳地(G. Leopardi)曾云,儿子与父亲决不会讲得来,因为两者年龄至少总要差二十岁。这都足以证明冯君的忧虑不是空的,“无如之何,笔之于书,或冀有时一读”,乃实为写家训的最明达勇敢的态度,其实亦即是凡从事著述者所应取的态度也。古人云,藏之名山传诸其人,原未免太宽缓一点,但急于求效,强聒不舍,至少亦是徒然。诗云: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王瑞玉夫人在《诗问》中释曰,“故人未必冒雨来,设辞尔。”钝吟居士之意或亦如此,此正使人觉得可以佩服感叹者也。
(廿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平书。) 咪咕公版·风雨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