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耍货
二三 耍货
《湖雅》卷九器用之属中有这一节:
“摩侯罗,按即泥孩儿,俗称‘泥菩萨’,以毗山泥造人物形,儿嬉所用。有泥猫,置蚕筐中,以辟鼠,曰‘蚕猫’。又以五色粉造人物形,曰‘粉作’;熬蔗糖和以麦面,就木范中浇成人物形,曰‘糖作’,亦呼‘糖菩萨’,亦呼‘糖人’;熬青糖,就木范中吹成人物形,曰‘吹糖’,皆以供儿嬉。酒筵看席或用粉作糖作盛碟,以配粘果。凡小儿戏具,皆以木以锡以纸以泥造成,形式名目甚多,统名耍货。”
又查《通俗编》卷三十一俳优类有泥孩儿一则,今录于下:
“《老学庵笔记》:鄜州田玘作泥孩儿名天下,一对直至十缣,一床直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许棐有咏泥孩儿诗。
《方舆胜览》:平江府土人工于泥塑,所造摩侯罗尤为精巧。
《白獭髓》:游春黄胖起于金门,地有杏花园,游人取其黄土戏为人形,谓之湖上土宜。
按,摩侯罗,游春黄胖,俱泥孩之别称也。又《广异记》载韦训卢赞善事,有帛新妇子磁新妇子,乃即今所谓‘美人儿’,而肖婴孩者亦往往剪帛烧磁不一。”
范寅著《越谚》(1882),收录方言颇为详备,我以为定有好些耍货的名称,岂知检阅一过,却没有什么,殊出意外。孙锦标的《通俗常言疏证》(1925)虽最近出,但专以古证今,所以也只寥寥几条,不足称引。中国对于儿童及其生活可以说是很是冷淡了。《潜夫论》云,“或作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皆无益也,”这或者可以代表中国成人们的玩具观罢。
我读了《湖雅》的文章,却引起了好些回忆,虽然我童年的回忆是那么暗淡而且也很有点模胡了。因为这“耍货”二字很是面善,—是的,这是在从市门阁至青黛桥(据说本字是清道桥,但我是照音写的)的一条街,即所谓鹅项街的中间,有几爿店,在他的招牌或墙上写着这两个字曰“耍货”。卖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也无非是竹木制的全副兵器,纸糊面具,不倒翁称“勃勃倒”,染色的木盘杯碗酒坛,泥青蛙,或老虎及鸭,大抵背上有孔可吹,或是底板的桑皮纸夹层中置叫子,按起来会吱吱地叫。此外自然有“烂泥菩萨”,无论他是状元,老嫚(Laumoen 堕民中之妇女),或“一团和气”,都平等地陈列在架上,但我们喜欢它却别有缘因,并不是它好看,只因为可以从他们的泥背上刮“痧药”,装在小瓶子里开药铺。全个耍货店的货色,一总不值三五块钱,但是,吓!这店面着实威严,近看远看,已尽够我们的欣羡了。倘若这是正月的前三天,再往东走去,可以在从轩亭口(这是丁字街,即秋瑾女士被害的地方)至大善寺的路上发见一两摊做火漆货的。我还记得,青蛙六文,金鱼八文,三脚蟾十二文,果品大约是四文均一罢,至于摸鱼的老渔翁,白须赤背,则要二十四文,要占去我普通所有的压岁钱四分之一,不敢轻易问鼎了。这些火漆货最易融化,譬如一颗杨梅你搁得久一点,一面就平了,再也看不出用鹅毛管印出的圆点,所以须得每天检点,放在冷水里洗个浴才好;可是这也不很容易,因为有时略略多浸,里面的芦干被浸涨了,三脚蟾之类的背上往往生出裂纹。不过这总还可以玩上几天,糖人面人则只能保存一天左右,而且没有补救的方法。糖人还可以吃了,如不嫌那吹糖人的时常用唾沫去润指尖,面人则唯一的去路便是泔水缸,浸软了一并喂鸡,抛到垃圾堆上去是不可的,因为太“罪过人”了。比较起来最有意思的要算是糖菩萨。这实在是用糖“铸”成的各种物事,有鸡,有马,有鳌鱼,有桥亭,有财神,弥勒佛称“哈啦菩萨”等等,而买时以斤论,每斤不过二百文罢,倘若你到大路口的糖色店里去。一斤,大的可以有三四“尊”,小的则二三十个不等,实在便宜极了。只要隔几天一晒,—而且愈晒愈白,—可以保存到上坟时候,不幸而打碎一个,那就可以分吃,味道与“巧糖”一样。《湖雅》说“用糖作盛碟”,这便是巧糖,有红黄白三色,状如贝壳而平面。但是小儿们所喜欢的还有杂色“棋糖”,这不但因为好吃,好玩,实在还是因为杂得有趣,正如茶食里边的百子糕以及“梅什儿”(即“杂拌”)一样。
关于范寅,我在民国四年的笔记里曾记有一则,题曰“范啸风”:
“范寅字啸风,别号扁舟子,前清副榜,居会稽皇甫庄,与外祖家邻。儿时往游,闻其集童谣,召邻右小儿,令竞歌唱,酬以果饵,盖时正编《越谚》也。尝以己意造一船,仿水车法,以轮进舟,试之本二橹可行,今须六七壮夫足踏方可,乃废去不用。余后登其舟,则已去轮机仍用篙橹矣。晚年老废,辄坐灶下为家人烧火,乞糕饼炒豆为酬。盖畸人也。《越谚》虽仍有遗漏,用字亦未尽恰当,但搜录方言,不避粗俗,实空前之作,亦难能而可贵。往岁章太炎先生著《新方言》,蔡谷清君以一部进之,颇有所采取。《越谚》中收童谣可五十章,重要者大旨已具,且信口记述,不加改饰,至为有识,贤于吕氏之《演小儿语》远矣。”
但是《越谚》出板于光绪壬午(1882),其时我尚未出世,至十岁左右,我听见他的轶事,已在出板十二三年后了,所以上文云“正编《越谚》”不确,盖谈者系述往事,误记为当时的事情也。
(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于北京苦雨斋。) 咪咕公版·自己的园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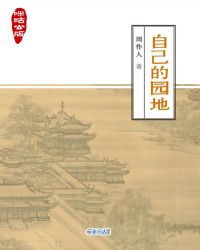
![全宇宙都爱看我的女装直播[穿书]](/uploads/novel/20210402/07ad511b03c8fb6d38c6c1ade68fa23a.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