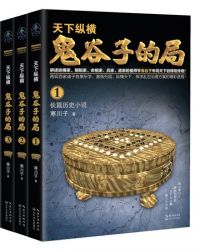第25章 膳馆苏张醉结义 灵堂父女伤别离
大周天牢苏秦关押处,宫正缓步走进,对司刑传达道:“娘娘口谕,将昨日所押的那个揭榜人无罪释放!”
司刑拱手:“遵旨!”
苏秦一步一步地走出宫门,神态狼狈。
小顺儿远远望见,撒腿就朝贵人居狂奔。
当张仪六神无主似的在院中走来走去时,小顺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来,扶在门框上喘道:“公公子,口口吃他出出来了!”
张仪蹿过来,瞪他一眼:“咦,你口吃个啥?人呢?”
“不不晓得顺儿回回来报”
张仪蜷起中指,朝他头上连敲几下:“报你个头呀!让你守在那儿,就是要你迎接卿相,你跑回来做啥?”
小顺儿以手护头,嘟哝着驳道:“主人吩咐小人一见口吃就回来报信,小小人哪儿错了?”
张仪在他头上又敲一下,一脸兴奋道:“本公子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还敢犟嘴?”说完“噌”地蹿到门外,撒开两腿就朝宫门方向跑去。
苏秦头低着,状态就如喝醉一般,正朝贵人居方向晃悠。
张仪远远望见,迎上去,扯住他,上下左右打量一遍,见他毫发无伤,惊诧道:“神了!真是神了!”
苏秦一脸诧异:“什什么神了?”
“呵呵呵呵,当然是苏兄你神了!”张仪退后一步,揖个大礼,“苏兄在上,受张仪一揖!”
苏秦打个愣怔,竟是忘了还礼:“张张公子,方方才你你叫苏苏秦什什么来着?”
“哈哈哈哈,”张仪擂他一拳,爆出一声长笑,“叫你苏兄啊!就冲你今日这股豪气,本公子也该叫你一声苏兄!”
苏秦受宠若惊,长揖至地:“苏苏秦谢谢谢张公子厚厚爱!”
张仪一把扯起他:“走走走,仪请苏兄畅饮一爵,为苏兄压惊!”
走没几步,苏秦看到一家酒肆,指道:“张张公子,这这儿如如何?”
张仪不屑一顾道:“市井之地,怎么能为苏兄压惊?”
“张张公子想想去哪儿?”
“老地方!”
老地方自然是指万邦膳馆。
接待他们的依旧是行人。得知他们仍要之前的雅舍,仍点之前的菜谱之后,行人不敢怠慢,匆匆禀报大行人:“报,上次那两个小子又来了。”
大行人看向他:“哪两个小子?”
“就是点下八十年陈酿并八热八凉共四镒足金却未付一文的那两个小子!”
“他们此来为何?”
行人苦笑:“仍是吃饭,仍要在原来那个雅间,仍要曾经点过的八热八凉,仍要一坛八十年陈酿!”
“上次是燕使代付,这次由谁来付?”
行人皱眉道:“下官忧心的正是这个。”
“这样吧,”大行人略一沉思,“给他们那个房子,就说最近生意清淡,原来点的膳品没有进货,原有的货不新鲜了,只能供应寻常菜品,至于八十年陈酿,也只有一瓶,被他们喝了,剩下的不过是些寻常陈酿,二十年之内的,要吃就吃,不吃就请他们自便。”
行人出去,不一会儿折返回来,兴奋道:“他们说吃,高兴着呢,看来此番意不在吃!”
大行人嘘出一口气:“那就好。”
“可万一他们仍然不给钱呢?”
“真不给也就算了。前番燕使给了四镒足金,不是赚了一些吗,大不了补给他们就是。”
“好吧。”
行人将苏、张请至先前那个雅舍。不消一时,酒菜悉数陈列于案,张仪斟酒捧爵,毕恭毕敬地敬上:“在下敬苏兄一爵,权为苏兄压惊,请!”
苏秦接过酒爵,诚惶诚恐道:“张公子大大礼,苏苏秦担担担当不不起!”
“苏兄不必客气,且饮下此爵,仪有话说!”
苏秦仰脖饮下。
张仪再次倒满,推在苏秦面前,自己端起另一爵:“仪多有得罪,自罚一爵,算是向苏兄赔罪!”说完一饮而尽,重新斟上,不无感慨,“不瞒苏兄,自你走进那扇朱漆大门,在下这颗心也就跟着进去了。昨儿整整一宵,在下是一眼未合呀!”
苏秦大是感动,朝张仪深深一揖:“苏苏秦无无无能,让让让张公子挂挂挂心了!”
张仪举爵道:“有能无能另当别论,苏兄能够毫发无伤地走出宫门,足见福大命大,可成大事!来来来,这一爵,张仪祝苏兄心想事成,万事圆满!”
苏秦亦举爵,与张仪碰一下,木讷地应道:“苏苏秦谢谢张公子美美言!”
苏、张二人开怀畅饮,不消一个时辰,一坛老酒已经喝光,张仪、苏秦均呈醉态。
张仪呼着酒气,朝外大叫:“酒呢!”
一个仆从又抱一坛走进,哈腰赔个笑,转身离去。
“好好好,来来来,”张仪开封,斟酒,推给苏秦一爵,“苏兄,苏兄,苏兄,喝喝喝,不醉不休!”
苏秦醉眼蒙眬:“不不不不”后面干脆不说了,仰脖饮下。
“哈哈哈哈,”张仪手指苏秦,“好一个苏兄!看仪的!”说罢仰脖饮下。
苏秦抢过酒坛,倒酒。
张仪舌头也不囫囵了:“不不瞒苏兄,起初在下真真还瞧你不上,不想苏兄竟竟然是个人物!张张仪服服了!”
苏秦全然没了往日的怯弱,将酒坛放下,手指张仪:“苏苏秦虽虽虽说身身贱,好好好歹也也是知的。张张公子说说出此此话,又称在在下兄兄弟,无论是是否真真心,苏秦都都将铭铭记于心!”
“苏兄,”张仪激动起来,“在下真心,敢对日月!”眼珠儿一转,朝侍奉在门外的仆从扬手,“来人,摆香案,义结金兰!”
仆从们摆上香案,点燃香烛,又在案上摆了两只大碗。
张仪将坛中老酒全部倒进碗里,酒太多,满案子流。
张仪起身,拉过苏秦,双双牵手,径至香案前面,各自焚香,双双跪下。
张仪拿过切肉的刀,划破手指,滴血入酒。
苏秦也划破手指,滴血入酒。
张仪焚香,拜叩天地四方,朗声道:“四方神灵在上,魏人张仪与周人苏秦义结金兰,苏秦年长为兄,张仪年幼为弟。自今日始,张仪诚愿与苏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共谋人生大业!若有背逆,天地不容!”
苏秦亦对香案连叩几下,吃力地说道:“苍苍苍天在在上,苏苏苏秦与张张张公子义义结金金兰,他他日苏苏秦若若得富富富贵,定定定不独独享,若有背背背背逆,刀刀刀刺我我我心!”
誓毕,张仪、苏秦各自端酒,起身,碰碗,仰脖饮尽。
靖安宫门外,宫正奉了王后旨意,尽职地守候。之后的两个时辰,前后共有三人前来探望,一是姬雨,二是西周公,三是内宰。宫正将王后的话重复三遍,一个也未让进。
天色迎黑,周显王放心不下,在内宰的陪同下亲自探视。
宫门依然紧闭,宫正依旧守在门外。
周显王诧异道:“你这是”
“娘娘正在小憩。”
“小憩就小憩嘛,你关门做啥?”
“是娘娘吩咐。娘娘说,她想睡个长觉,无论何人都不能打扰!”
显王皱眉:“寡人也不能吗?”
“娘娘是这么吩咐的!娘娘要老奴将此锦囊转呈陛下!”宫正起身,从袖中摸出锦囊,双手奉上。
显王接过锦囊,看到锦囊封口处细密有致的针脚,知是王后亲手所缝,忙拆开,抽出里面的丝绢,打眼一扫,脸色立变,一把推开宫正,撞开宫门,跌跌撞撞地冲进宫里。
宫正、内宰无不傻愣。
周显王扑到榻前,失声痛哭:“汕儿—”
内宰跟进来,见王后妆饰一新,头被丝帛做成的套子套着。显王急切解袋,手却抖作一团,解不开。内宰急将套子取掉,手搭在王后鼻孔上,人早没气了,摸脉,手腕已凉。
显王伏在王后身上,哭得伤悲。
宫正赶过来,拿过袋子,闻到桐油味道,跪地大放悲声:“娘娘,是老奴害了您啊!”
内宰看向他:“怎么回事儿?”
宫正哽咽道:“娘娘午时要老奴寻些桐油,说是派个用场,老奴不知就里,到库房里四处寻找,竟就寻到一罐。老奴拿来交给娘娘,谁想娘娘她—”呜呜咽咽,“娘娘啊,您您怎能走走上这条路啊!”
内宰将袋子“噌”地夺过来,纳入袖中,脸色一虎,声音低沉,斥道:“什么路不路的?娘娘是久病卧榻,一口气没有跟上来!快召太医!”
宫正打个惊愣,飞奔出去。
太医赶至,摸摸王后脉相,验过鼻息,跪地,颤声道:“娘娘驾崩了!”
内宰似是不信:“娘娘中午还是好端端的,为何这就驾崩了呢?”
“是哩,娘娘患的是心病,发作起来很急的!”
“哦。”内宰转对宫正,“拿块白帛来!”
宫正找来一块白巾,递给内宰。
内宰接过,轻轻蒙在王后面上,转对众宫人:“娘娘久病未愈,突发心风,于辛丑日人定辰光驾崩,举国治丧!”
夜幕降临,周王宫里,灯火闪烁。王后暴毙,丧钟鸣响,哀乐声声,悲声一片。
公主闺院里,姬雨在莲花池边正襟危坐,面前摆着琴架,架上是姬雪留给她的五弦凤头琴。
姬雨纤指飞扬,琴声忧伤,《流水》声声传出。
姬雨一边弹琴,一边在心中向姐姐诉说:“阿姐,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阿姐?刮风了吗?下雨了吗?不要着急赶路,天不黑就要歇着阿姐,雨儿这要捎给你一个喜讯儿,明日凌晨,雨儿和母后就要飞走了,飞进先生的那片林子里,自由自在,远离尘嚣”
宫中尽是哀乐和丧钟,姬雨却充耳不闻。许是被这悲凉的气氛所感染,一旁的侍女无法再听下去,“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公主”
姬雨微微抬头,泪眼略显诧异地看向侍女。
“公主,娘娘娘娘她”
姬雨心头一震,手指剧烈抖动,但仍然在弹,只是泪眼惊讶地看向侍女,目光征询。
侍女放声大哭:“娘娘她驾崩了”
琴声刹那间停止,声声哀乐隐约传来。
姬雨蒙了,手指僵在琴上,两只眼睛如痴呆一般盯牢侍女。
侍女惊愕,膝行至前:“公主,您您这是怎么了?”
姬雨仍旧僵在那儿。
时光凝滞,姬雨的一只手悬在空中,一只手抚在弦上,就如一具僵尸。
侍女迅速站起,趋前,急切地叫道:“公主!公主!公主—”
姬雨仍无反应。
侍女惊呆,退后几步。
姬雨抚琴的那只手动了,缓缓扬起,再扬起,一直扬到不能再扬的高度。
陡然,姬雨的两手如疾风般落下,“啪”地砸在琴上,一根琴弦应声而断,鲜血顺着姬雨的手指汩汩流出。
侍女惊叫一声:“公主”
姬雨不应,只将十根手指如雨点般落下,两行泪水如珍珠般洒下。凤头琴上溅满了姬雨的鲜血和泪珠,点点滴滴,梅花带雨。
与此同时,燕国的迎亲车队已经行至宿胥口,歇宿在镇上一家最好的驿馆里。
姬雪静静地坐在餐案前,案上摆着几道菜,上面已经不冒热气了。
春梅候立一旁,不无关切道:“公主,再不吃,饭菜就凉了!”
姬雪泪水滚出。
“公主,是不是又想洛阳了?”
姬雪哽咽道:“梅儿,我我看到母后了”
春梅惊愕了:“娘娘,公主怎么会看到娘娘呢?她在哪儿?”
“她她就站在我眼前,她”
“娘娘怎么了?她说什么了吗?”
“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站在那儿,看着我”
春梅扑哧笑了:“公主,没事的,是你想念娘娘了!吃饭吧,公主!”说完蹲下来,为她夹菜。
姬雪拭把泪:“你们吃吧,我我吃不下,也不想吃。”说罢缓缓起身,走向寝处。
酒逢知己千杯少。苏张二人义结金兰,自是开怀畅饮,不消半个时辰,已喝空两坛陈酿,无不酩酊大醉,相互搀扶,脚步踉跄地走出膳馆大门。
大行人、行人及几个仆从站在门口,看着二人。
张仪冲几人扬手道:“结结结账”
苏秦亦扬手道:“记记记秦账账账下”
大行人几个摇头苦笑一下,回去了。
“哈哈哈哈,”张仪转对苏秦笑道,“今与苏兄义义结金金兰,仪得兄长,痛快!”
苏秦喷着酒气:“苏苏秦能与张张公子义结金金金兰,就就就如做做做梦一般!”
“不不许再叫张公子,叫仪仪弟!”
“不不不是仪仪弟,是贤贤贤贤弟!”
“好,就就贤弟!”张仪又走几步,酒也略略醒些,似乎想起什么,仰天长笑,“哈哈哈哈—”
苏秦一怔:“贤贤弟为为为何发发笑?”
张仪止住笑,看向他,言辞流畅许多:“苏兄,还记得看相的那个老白眉吗?什么‘远观万里鹏程,近判旦夕祸福’,净是胡扯!”
“贤贤弟何何何出此此言?”
张仪哼出一声:“他说六十日之内,苏兄将逢人生大喜,张仪则有人生至悲。屈指算来,今日届满此数,苏兄喜在哪儿?张仪我又悲在何处?”
“贤贤弟所言甚甚是,想我苏苏秦这这这般光光景,混混混口饱饱饭已是不不易,哪哪哪里还还还能贵贵贵贵至卿卿”苏秦一个趔趄歪在地上,几次欲站起来,皆是不能。
张仪伸手拉他,没拉起来,自己反被拖倒。
二人在大街上仰天躺下,头对头,排成两个头对头的大字,占去了大半个街道。
张仪醉眼蒙眬:“不瞒苏兄,今朝醉了,待到明日,仪弟定要寻到那个老白眉,看他有何话说?若是说说得好听,服软求饶,仪弟或可放放他一马。若是说得不不好,看我把他的招幡扯下来,踩踩在脚下!”
苏秦已然呼呼大睡,发出沉沉鼾声。
就在此时,苏代与同村的一个小伙子从远处走过来。
小伙子道:“苏代,都寻老半天了,寻不到呀!”
苏代应道:“寻不到也得寻!”
小伙子笑道:“嗨,寻不到才叫好玩呢,这边新夫人空守炕头,那边新郎官在外逍遥!不是吹的,在咱轩里,还真是黄花闺女进洞房,头一遭哩!”
苏代啐他一口:“遭你个头!阿大在家里大办喜事,兴师动众,我们若是寻不到二哥,叫阿大咋个收场?”
前面现出两个人,小伙子惊叫:“看,前面有两个醉鬼!”
苏代也看过去。
小伙子揉揉眼睛:“左边那个像是你二哥哩!”
苏代喜道:“是二哥!快!”
二人急奔过来。
苏代扳起苏秦,摇晃他道:“二哥,二哥,你醒醒!”
苏秦揉揉眼道:“谁谁在叫叫”
“是我,苏代,阿大让你回去!”
“我我我不不不”
张仪听得清楚,一骨碌爬起,坐在地上:“请问仁兄,你是何人?为何拉扯苏兄?”
苏代抱拳应道:“在下苏代,苏秦是我二哥。家父想见二哥一面,在下特来请他回去!”
苏秦接道:“贤贤弟,甭甭理他,咱快快走,我我要学学艺要跟贤贤弟共共谋大大”
张仪踉跄着站起:“苏兄弟,请问令尊为何要见苏兄?”
苏代稍作迟疑,缓缓说道:“家父说,他要死了,他想再看二哥一眼!”
张仪大惊,揖道:“既如此说,苏兄就交给你了,张仪就此别过!”
苏秦已如一摊烂泥,呼呼大睡起来。苏代让同伴招来一辆骡车,三人将苏秦抬到车上,别过张仪,扬长而去。
张仪踉踉跄跄地走回居处。
眼见贵人居在望,张仪打个趔趄,扶墙而行,嘴里嘀咕着:“人生至悲,莫过于丧父。苏兄之父若死,当是大丧。今日恰满六十日,若是苏兄遭遇大丧,老白眉所言也不为虚!”又走几步,停住脚,自语,“咦,就算老白眉预言应验,也不过应验一半,且这一半还是颠倒的。苏兄所遇,当是人生至悲,何来大喜?”爆出长笑,扶墙又是一番深思,“嗯,若以此说,当是喜丧颠倒。苏兄遭遇大悲,我当应验大喜才是!天已迎黑,我的大喜又在何处?看来,那个老白眉纯属瞎蒙!哈哈哈哈,他的那个小招幡儿,明日我是扯定了!”
小顺儿听到笑声,急急走出:“公子呀,您总算是回来了!”
张仪劈头大骂一通:“你小子死死哪儿去了?快,到万邦膳馆结结账!”
小顺儿搀住他:“公子呀,家里来信了,送信的说,是个急事,小人四处寻您,可寻不到您呀,不晓得您哪儿去了?”
“啥啥个急急信儿?”
“是张伯捎来的!”
张仪酒劲醒去一半,盯紧他,急切问道:“张伯?急信?信呢?”
小顺儿摸出信,递给张仪。
张仪接过,自语道:“难道是是个喜信儿?”边说边拆,因醉劲儿太大,手指不听使唤,连拆几次,依旧启不开蜡封。
小顺儿看得着急,一把将信夺过,三下两下开了封,抽出信函递予张仪。
张仪读信后神色立变,发出一声长长的惨叫:“娘—”
入夜,苏家院落中张灯结彩,仍有不少人在忙活。门外一阵响动,苏代二人架着苏秦回来了。苏秦头低着,仍旧没醒。
苏姚氏闻声迎出:“是秦儿吗?”看到苏秦这个样儿,想起王榜之事,吓哭了,转对苏代,“代儿,这这是咋哩?”
苏虎、麻姑儿急从客堂里跑出来。
苏虎打量一下苏秦,目光落在苏代身上。
苏代笑道:“大,娘,没事儿,我二哥喝多了!”
苏虎老眉紧锁:“喝多了?在哪儿喝的?”
“万邦膳馆!”
“万邦膳馆在哪儿?”
“就在万邦使馆那道街,膳馆就是专供列国公使吃饭的地方。”
“啥?”苏虎哪里肯信,“那地方能轮上他去喝?”
苏代嗫嚅道:“我也不晓得,看见时,他就躺在膳馆外面的大街上,还有一个富家公子,都喝醉了!”
“唉,”苏虎气得直跺脚,“这臭小子,丢人丢到公使馆里,还不让列国看笑话?”
“呵呵呵,”麻姑乐了,“老哥儿呀,二小子能回来就好,要不然,明天可就抓瞎哩!”
苏虎转对苏代:“愣个啥哩,抬他回去,锁起来,甭让他夜里跑了!”
一辆辎车停在万邦膳馆门口。
微弱的夜光下,张仪烂醉如泥。
小顺儿付完膳费,从大门里走出,大行人、行人等出门送行。小顺儿跳上马车,扬起鞭子响一声,马车疾驰而去。
与此同时,秦使馆里一片沉闷。
打破沉闷的是公子疾,他轻叹一声:“唉,都怪臣弟,过于急切了!”
“哦?”嬴驷看过来。
“据林仙姑诊断,王后上一次是装病,这一次是真病,但病不至死,调养调养也就好了。臣以为,既然病不至死,何不借此压一下周室,因而仍旧说她装病。估计王后得知,觉得委屈,气郁加重,这才”公子疾顿住,一脸自责。
“你是说,”嬴驷紧盯住他,“王后不愿意女儿做我大秦国的太子妃?”
“据西周公所说,雪公主愿意,可魏人不让。该到雨公主,魏人无话说了,但雨公主不肯!”
嬴驷咬牙:“这个女人,可恶!”
“驷哥,事已至此,该如何办为好?”
嬴驷语气坚决:“她愿也好,不愿也好,本宫认定的东西,就是本宫的!”
“臣弟晓得了!”
“不过,”嬴驷缓和一下语气,“周室大丧,且缓他几日,再与他们计较!”
公子疾点头:“臣弟遵旨!”
夜深了,雨公主仍旧坐在闺房外面,如一根木头。
侍女走过来,将一件外衣罩在她的身上。
哀乐仍旧响着。宫城外面,不知哪儿响起二更的梆声,两种声音交融,汇成王城之夜的节奏。
梆声消停了。
姬雨缓缓起身,将早已打好的包裹背在身后,抱起凤头琴,一步一步地挪向靖安宫。
靖安宫里,烛光点点,哀乐声声。
宫中央摆着灵榻,王后静静地躺在榻上,身上蒙着一袭白缎。
一身孝服的周显王守在灵榻前,神情木呆地望着灵榻上方的画框。画中的王后抿着嘴,甜甜地朝他微笑,仔细看,那笑容显然是挤出来的。灵榻两侧,顺溜儿跪着大小贵妃、几个王子和小公主,全都孝服在身,悲悲切切。
姬雨抱着琴,悄无声息地站在门口。
内宰看到,拿过一身孝服帮姬雨穿了,又在她的头上扎上一条白色麻巾,另一条系在腰间。
姬雨表情木然,既没有哭,也没有动,只拿两眼痴痴地凝视灵榻,就如一座雕塑。
披戴已毕,姬雨重又抱起凤头琴,缓缓走到灵榻前面,在王后身边放下琴,轻轻揭开罩在她脸上的白缎。
王后安静地躺着,两眼闭合,就像平日睡熟时一样,只有两道细眉锁在一起,似是凝结了太多的忧伤。
姬雨伸出双手,轻轻抚摸母后紧锁的眉头,想让它们展开,可它们怎么也展不开,就像被什么拧起来一般。
姬雨将面颊轻轻贴在母后的面颊上,嘴唇对着她的耳朵,嘀嘀咕咕很久,谁也不知她说了些什么。
姬雨抬头,再次抚展王后的双眉。
凝眉舒开了,王后的面容慈爱而又安详。
姬雨俯身亲吻王后,从额头一直吻到嘴巴,然后是她的脖颈、双手。姬雨在王后头下垫个枕头,让她面对自己。
姬雨起身,打开琴盒,在灵榻前面支起琴架,将姐姐的凤头琴摆在架上,端坐下来,面对母亲,轻声抚琴。
尽管只有四弦,琴声反倒添了几丝悲切,长了几分愁韵。姬雨弹的依旧是《流水》,只是这流水此时听来,就如在寒冰下面无声地呜咽,如泣如诉,却不为他人所见。
姬雨就这样坐着,就这样奏着,奏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泪水,也没有哭泣。
跪在王后榻前的贵妃、小王子、小公主们,不知何时,一个接一个离去。只有宫正、内宰和显王三人依旧跪在榻前,各噙泪水,听着姬雨的诉说。
突然,周显王动了一动,缓缓转过身子,静静地望向女儿。
显王吃力地站起来,挪几步,坐到姬雨身边,轻轻抚摸她的秀发。
姬雨弹琴的手越来越慢,眼睛紧紧闭合,眼中滚出泪花。
姬雨转身,一头扎入显王的怀中,放声大哭:“父王”
周显王将她紧紧抱在怀中,生怕有谁从他怀中夺走她似的。
父女拥作一团,互相抱着,紧紧地抱着。
蜡烛燃完了,宫正换一根,又换一根。
天色拂晓,远处传来鸡啼声。
姬雨挣开显王,跪在地上,抬头凝视他:“父王!”
周显王淡淡道:“说吧,孩子!”
“雨儿不能尽孝,雨儿不能服侍父王,雨儿雨儿这就去了!”姬雨的泪水流出,起身,一拜,二拜,三拜。
周显王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凝视姬雨。
“父王”
显王淡淡说道:“是去云梦山吗?”
姬雨淡淡说道:“是的。”
周显王慢慢闭上眼睛,声音从喉管深处蹦出:“去吧,鬼谷先生在等你呢!”
“父王,您全都知道了?”
周显王摸出王后的锦囊,交给姬雨:“你的母后说,这是一个偏方儿!”又将头转向王后,略顿一顿,泪水盈眶,哽咽,“是一个偏方儿!”不停地重复,“是一个偏方儿”越说越伤心,呜呜咽咽,伏在王后的尸体上悲泣起来。
姬雨一看,正是苏秦托她交给母后的锦囊。
姬雨打开,里面是块丝绢,丝绢中间是鬼谷子亲笔书写的两行墨字:“道器天成,鬼谷重生;携蝉归林,可解纷争。”丝绢下面,则是王后用血写成的一行小字:“陛下,欲从先生,难舍君情;欲与君偕行,豺狼不容;君恩社稷,夙愿近忧,臣妾两难,唯有远行;恳请陛下,听妾遗声,雪儿远嫁,已是苦命;唯此雨儿,托予先生”
姬雨将锦囊捂在胸前,朝王后的遗体缓缓跪下,放声悲哭:“母后,母后,您答应雨儿,您答应雨儿一道走的呀,母后”
显王转过来,轻轻抚摸姬雨的秀发:“去吧,孩子,听你母后的,投先生去,走得越远越好!”
姬雨抬起泪眼,凝视显王,担心道:“父王,秦人那儿”
显王抬起头来,声音哽咽,悲怆道:“生离死别,国破家亡,寡人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还能怎样?他们又能怎样?”
夜空里传来缥缈的埙声,远古,苍凉,悲怆,似是在为王后悲号。
显王拿袖管抹一把泪水,凝视姬雨,轻声吟唱: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显王的吟咏缓慢,低沉,与那埙声一样,苍凉中不无悲壮。
姬雨含泪和合,父女二人悲怆的声音响彻灵堂: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
行迈靡靡,中心如醉。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
行迈靡靡,中心如噎。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内宰、宫正俱是泣不成声。
远处雄鸡再啼。
姬雨起身,背上凤头琴,挽了包袱,拜过父王,吻过母后,挂上佩剑,一个转身,径出宫门。
晨雾缭绕,洛阳大街上,空无一人。
一身孝服的姬雨目不斜视,快步走向洛阳东门,过城门东出,投轩辕庙而去。
轩辕庙外,庙门虚掩,院中传来扫帚声。
姬雨嘘出一口气,轻轻叩门。
童子开门,手中拿着扫帚。
姬雨揖礼:“请问阿弟,先生可在?”
童子回一揖道:“总算等到姐姐了!”
姬雨吃了一惊:“等我?”
童子指指大殿:“是哩,家师正在候你!”
姬雨走进殿里,见殿里殿外清扫完毕,所有物事摆放齐整,就连轩辕泥塑上的浮尘也被童子扫了个干净。
鬼谷子端坐于轩辕塑像前,眼睛微闭。
姬雨放下琴盒、包裹,跪叩:“姬雨叩见先生!”
鬼谷子依然是两眼微闭,似乎没有听到她的声音,也没有在意她的存在。
姬雨再叩:“小女子叩见先生!”
鬼谷子嘴角启动:“你的麻衣可是为你母亲穿的?”
姬雨悲哭。
鬼谷子淡淡说道:“你的母亲因道而来,循道而去,可喜可贺,你哭个什么?”
姬雨止住哭声,有些迷惘地看向鬼谷子。
“姑娘此来,欲求何事?”
“果如先生所言,”姬雨诉道,“罗网张来,那只玉蝉儿走投无路,欲随先生远遁山林,恳求先生容留!”说毕再叩。
“山林虽有自在,却是寂寞之地,只怕姑娘耐熬不住!”
“小女子早已厌倦尘世喧嚣,无心他求,愿从先生终老于林莽,潜心向道!”
“老朽观你是个道器,收留你了。你既以玉蝉儿为喻,自今日始,就叫玉蝉儿吧!”
姬雨叩首,悲喜交集:“玉蝉儿谢先生赐名!”
“辰光到了,该上路了!”说完鬼谷子缓缓起身。
旭日东升。
童子扛幡儿打头,玉蝉儿跟后,鬼谷子走在最后,一行三人走出庙门,走下土坡,拐上洛阳通往虎牢关的衢道,迎着旭日渐去渐远。
龙口村,老喜儿家的大门外面,迎亲车辆已准备就绪。
小喜儿却仍躲在闺房里不肯出来。
麻姑儿急了,进去催道:“小喜儿,快点呀,日头已经出来了,大伙儿都在候你哩。”
小喜儿忧心忡忡,小声问道:“麻姑儿,他回来没?”
“谁回来没?”
“就是那个人!”
“呵呵呵,瞧你问的啥话?人不回来,结个啥亲哩?”麻姑压低声,“不瞒你说,昨儿晚上就回来了,到家已是小半夜,不知和哪个富家公子在喝酒哩,弄得一身酒味,熏得我呀”捏住鼻子,做个苦相。
小喜儿嘘出一口气:“他揭王榜没?”
“啥王榜不王榜的,都是瞎传,要是揭了,人能回来吗?”
“嗯。”小喜儿略略一顿,俏脸上现出一丝忧虑,“他不会嫌弃我是”看向自己的跛脚。
“呵呵呵,你还没嫌弃他呢!”麻姑学苏秦的口吃状,“小小小小小喜儿”
小喜儿扑哧笑了,在麻姑的搀扶下,一跛一跛地走出来。
苏秦烂醉如泥,躺在自家的土炕上正在呼呼大睡,苏代拿着新郎服饰进来:“二哥,还没睡醒呀?”
苏秦动也不动,继续打着呼。
苏代扯他几下,见他仍旧醉着,急了,使劲扯他胳膊:“二哥,快起来,新娘子马上到了!”
苏秦如同木头,任凭他怎么折腾都在沉睡。
苏家院门内,张灯结彩,一派喜气。
全村人都来帮忙了,院中人来人去,甚是热闹。院门外面列着三口铁锅,一口烹猪,一口烹羊,另外一口烹了一只硕大的牛头。
一辆披红挂彩的牛车在锣鼓声中徐徐进村,渐至苏家院落的柴扉外面。苏厉点燃一捆干竹,爆裂的竹节噼里啪啦,声声脆响。
爆竹声中,一行人抬着各色嫁妆走进苏家院门。
锣鼓声更见响亮。
麻姑儿大步走进院里,朗声叫道:“老哥儿,新人到了,快叫新郎官出来迎接!”
苏虎看向苏代:“代儿,你二哥呢?”
苏代一脸无奈地朝屋里努下嘴。
苏虎几步跨进厢房,果见苏秦仍在呼呼大睡,不禁怒从心起,“噌噌”几步走到灶间,舀来一瓢凉水,“噗”地浇在苏秦脸上。
苏秦打个惊战,酒也醒了,睁眼看到苏虎,急又闭眼,连揉几揉,再次睁开,认准了是在自己家中,一时大怔。
苏虎将一套新郎服“啪”地扔在炕上,低声喝道:“人都到了,还不赶快换上?”
苏秦越发惊讶,似乎是在梦中。
苏虎瞪一眼苏代。
苏代过去,匆匆为苏秦穿上新郎服饰。
苏秦一头雾水:“这这这”
苏代悄声道:“二哥,二嫂已到门外了!”
苏秦惊愕:“二二二嫂?谁谁家二二嫂?”
苏代将苏秦的衣裳穿好,戴上冠带,端详一阵,满意地笑了:“今儿是二哥的大喜日子,阿大为二哥娶媳妇了,新人已在门外,等二哥去迎哩!”
苏秦惊呆了,两眼直视苏虎。
“看什么看?”苏虎白他一眼,“快去擦把脸,到彩车上抱你媳妇进门!”
苏秦豁然明白,手指苏虎,嘴唇哆嗦:“阿阿”气得“大”字出不来了,干脆“唰唰”几下将身上的新衣悉数脱下,摔在地上,解下冠带,一一抛到一边,倒头又睡。
院外锣鼓声紧,人声鼎沸。
麻姑儿站在院中,不无夸张地大叫:“新郎官哩,总不能一直把新人晾在车上啊!”
苏虎急了,斜眼示意苏代。
苏代上前硬扯苏秦。
苏秦显然是故意的,睡得呼呼直响。
苏代放开苏秦,看向苏虎,苦笑:“阿大,看样子,二哥的酒劲儿还没过去呢!”
苏虎气恨恨道:“什么没过去!他是装的!”说着上前拧住苏秦耳朵。
任凭苏虎怎么拧掐,苏秦愣是忍着。苏虎扳他起来,稍一松懈,苏秦就又倒下。苏虎没辙儿了,照他屁股上踹几脚,苏秦照睡不误。
院门外面,因了苏秦的名声,看热闹的人越发多了。锣鼓手看到人多,劲头也来了,越敲越紧,声声催促。
观众七嘴八舌:
“咦,新郎咋还不出来呢?新娘子等有半个时辰了!”
“嘘,听说这小子揭了王榜,要给娘娘治病哩!”
“啥?他会给娘娘治病?我鼻子也不信!”
“是呀,这阵儿不定仍在天牢里关着,等着斩头呢!”
“天哪,要是真被斩了,新娘子咋办?”
“一定是了,要不然,这么久了,咋还不出来呢?”
对于众人的闲言碎语,彩车里的小喜儿听在耳里,脸上忧急。
麻姑风风火火地冲进厢房:“新郎呢?”
苏虎气呼呼地指指炕头。
麻姑看过去,急得跺脚:“这这这这可咋整哩?”瞥到苏代,眉头一动,“嘿,有了!”
苏虎看向她:“什么有了?”
麻姑对苏代道:“苏代,你穿上新郎服,先把新人抱回来再说!”
苏代面色绯红,摆手道:“这咋能成?我是小叔子,哪能去碰嫂子哩?”
“嘻嘻,”麻姑笑了,“什么小叔子不小叔子的,新人进门,三天内没有大小,你只管去。再说,你名字就叫苏代,啥叫代呢?就是代你哥,去吧。只要抱进院里,跨进正堂,就算娶进家门了!其他事情,都好说!”
苏代连连后退,使劲摇头:“不成不成!”
苏虎一咬牙关:“代儿,听麻姑的,把你二嫂抱回来!”
苏代欲再推托,见苏虎瞪眼,只好穿上新郎服,跟着麻姑走出去。
当麻姑领着穿着新郎服的苏代走出前院时,人群沸腾,口哨声、起哄声四起。苏代一句话不说,低着头走到彩车前面。
麻姑走到彩车边,对小喜儿小声嘱道:“那小子还醉着,让他弟背你进门!记住,脚不要沾地!”
小喜儿点头,伸手给伴娘。
伴娘扶她走出篷车,双双蹲在车沿上。
麻姑让开位置,低声对苏代道:“人都出来了,快呀!”
苏代两眼一闭,走到车前,不由分说,抱起一人就走,结果却是伴娘。伴娘尴尬不已,挣扎着要下来,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麻姑急了:“苏代,抱错人了!”
苏代一脸尴尬,忙把伴娘放下,回身抱起小喜儿,在众人的哄笑声与更加起劲的锣鼓、唢呐声中走进院门,走进堂间。
苏家正堂里布置一新,明堂燃着喜烛,正中是伏羲、女娲泥塑,泥塑前面是列祖列宗的牌位,上方高悬周天子题的“天道酬勤”匾额。
小喜儿坐在麻姑儿早已备好的软垫上,头上罩着红巾。
麻姑儿走到苏虎跟前,低声道:“老哥儿,人进家了,下一步该是拜天、地、宗、亲,不能代了!”
苏代猛地脱掉新郎服饰,抱怨道:“不代了,不代了,打死我也不代了!”
众人皆笑起来。
苏虎转对苏代说道:“喊两个人,把你二哥拖过来!”
苏代看向麻姑:“麻姑,我二哥还没醒酒,能否再让他睡一会儿,晚点儿拜堂?”
麻姑郑重说道:“不拜天地宗亲,就得不到各方神灵荫佑,这桩亲事就等于没结。再说,这都快中午了,堂不拜,外面的宴席就开不成,众多亲朋早饭都没吃,急等开宴呢!”
苏虎急了:“这咋整哩?”
“这样吧,”麻姑略一思忖,“新郎既然没醒酒,就让二人拜个醉堂。”
“咋拜?”
麻姑对苏代交代道:“苏代,把这衣服给你二哥穿上,架他过来,按住他拜。”
苏代连连摇头:“这这这我不干!”
苏虎眼一瞪:“这你娘个脚!”拿起新衣,转对两个年轻亲戚,“你俩,跟我来!”
两人跟着苏虎走到偏院。
厢房里,苏秦仍在装睡,门口守着一个壮小伙子。
苏虎将衣服扔在地上,嘴努向苏秦:“给他穿上!”
几人把苏秦拖起来,穿上。
苏秦仍旧装睡,夸张地打起鼾声。
苏虎怒不可遏:“拖到正堂!”
几人架起他,拖到正堂。
见一切皆已准备就绪,麻姑朗声唱道:“天地四方诸神灵、苏氏列祖列宗在上,今有轩里村苏氏苏虎次子苏秦与龙口村朱氏朱老喜儿独女朱小喜儿喜结伉俪之好,敬请四方神灵、列祖列宗证之、佑之!”又转对新郎、新娘,“新郎、新娘,一拜天地神灵!”
伴娘上前架住新娘,这边几人扭住苏秦,敬拜天地,共是三拜。苏秦被人按下又拖起,脸色极是难看,怒气在聚集,但表相仍是醉态。
麻姑朗声唱宣:“二拜列祖列宗!”
苏秦又被按住,按下再拖起,如是三拜。
“三拜高堂!”
苏虎、苏姚氏过去,并排坐在堂前一个席案前。苏秦再被按住,又拜三拜。
“夫妻对拜!”
新娘子转过身,面对苏秦,深鞠一躬。苏秦硬起腰杆死不鞠躬。几人硬将他的头弯下一些,算是鞠了。
仪式总算是走完了,麻姑朗声高唱:“仪式完毕,新郎、新娘入洞房!”
苏秦呆在那里,脸色乌青,酒精遇到肝火,燃烧了。
锣鼓声再度响起。
拜过天地,新娘已是苏家的人,脚可落地了。也就是说,小喜儿必须自己走进洞房。
苏家共有三进院子,正房苏虎老两口占了,第二进是苏厉家占了,第三进分东西两个小院,苏秦的洞房位于第三进的东小院。这是一段不小的距离。
麻姑再唱:“请新郎、新娘入洞房!”
伴娘走到小喜儿左边,架起她的胳膊,穿过后堂,走向第二进院子。小喜儿只用一只脚点地,但在长裙下面,不是明眼人看不出来。
然而,怕处有鬼,痒处有虱,偏就有个明眼人看得真切,就如发现宝贝似的大叫道:“咦,快看呀,新娘子只用一只脚走路!”
众人惊愕,七嘴八舌道:
“一只脚咋走哩?”
“跳呀!咦,快看,新娘子真就是在跳哩!”
所有目光全都聚焦在小喜儿的跛脚上。
小喜儿急了,跛脚落地,身子明显歪了一下。
众人又开始叫起来:
“哈哈哈,是个跛脚!”
“是哩,我也看见了。”
众人皆笑起来。
“这就对了,口吃对跛脚,绝配哩!”
“对呀,对呀,天作之合!”
响起一阵更大的哄笑声。
面对众人的冷嘲热讽,苏虎听得耳根发热,怔了一会儿,方才回过神来,恨恨地剜了麻姑一眼。
麻姑回他一个干笑,转对观众:“有啥好看哩?开宴喽!”忙追上去扶住小喜儿,二人架起她,“噌噌”几下就进了第三进院子。
苏虎恨恨地转向苏代等人吼道:“愣个啥?弄进洞房去!”
几个小伙子扭住苏秦,欲将他强行架出堂门。
苏秦两臂猛地一甩,挣脱出来,转身怒视苏虎,似要喷出烈焰。
众人惊愕。
苏虎怔了,逼视苏秦:“你你小子,敢这样瞪我?”
苏秦目不斜视,直盯住他。
苏虎憋久的气寻到泄处,一步一步逼近苏秦。
苏秦本能地后退,一直退到正堂中间,但目光丝毫不躲,眼中充满了怨、恨与怒。
苏虎爆发了。
苏虎“噌”地走到门后,抄起顶门棍子,高高扬在空中。
苏秦动也不动,目光依旧盯住他。
苏虎颤着两手,冲上来,劈肩打下。
苏厉急了,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扯过苏秦的胳膊,用力拉开。
苏虎一棍打空,身体失去平衡,一个踉跄,额头撞在案角上,登时鲜血流淌,倒地不动了。
看热闹的眼见闹出人命来,不再哄笑了,一起围上抢救,堂中一片混乱。
苏秦也是傻了,钉在那儿一动不动。
众人把苏虎抬到他的卧房,有人拿出一把草木灰按在他的额头止血,有人去找疾医,皆在忙活。
苏虎发出哼哼声。
苏秦嘘出一口气,见没有人再看管自己,便悄悄挪出屋子,溜出院子,撒腿跑向村外。
颠簸一夜,天色大亮时,车马进入崤道,张仪的酒这时也醒了,坐起来,怔怔地听着马蹄声。
马儿走累了,脚步慢下来。
马停下来,走到路边,啃起树叶来。
小顺儿毫无察觉。
“顺儿?”张仪怔了下,叫道。
小顺儿打个惊战,揉眼。
“车子咋不走哩?”
“我”小顺儿惭愧道,“我睡着了。”
张仪走到驭手位置,从他手里抓过缰绳:“你睡吧,我来!”
小顺儿忙抢回来:“这这这怎么能让公子驾车呢?”
“那你走快点儿!”
小顺儿看看马,面露难色:“马不行了,得吃草料、饮水,也得歇个脚儿!”
“咦!”张仪看看马,跳下车子。
小顺儿给马饮水,抱些干草和饲料。
马儿吃起来,小顺儿歪在一边打瞌睡。
张仪掏出信,盯住上面的文字:“仪儿,见信速回,夫人病重,恐不久矣。张伯。”
张仪将信捧在心头,泣道:“娘,您一定要等着仪儿,等着你的仪儿啊”
“什么,雨公主不见了?”嬴驷盯着公子疾,表情愕然。
“是哩,”公子疾点头,“方才臣见西周公从宫里出来,拦住他问询宫中之事,西周公说,所有宫人并满朝文武都在为王后举丧。臣问他雨公主情绪可好,他打了个怔,说是没有看到雨公主。臣怕出意外,使他进去寻找。西周公进宫半日,说是雨公主不见了,所有人都不晓得她哪儿去了,就连内宰、周天子也是不知。”
“那”嬴驷吸一口气,“他们急不?”
“急呀。这辰光都在寻找呢!”
嬴驷又吸一口气,声音似从牙缝里挤出:“这个女人”顿住。
公子疾凝视他,目光征询:“驷哥,如果雨公主跑了,如何是好?”
“一个深宫女子能跑到哪儿去?”嬴驷转对公子华,“华弟,放黑雕,无论她跑到哪儿,都给我抓回来!”
公子疾嘴巴动了几下,没有出声。
“疾弟,你想说什么?”嬴驷看得真切,冲他问道,“你”字发音怪怪的。
“回驷哥的话,”公子疾拱手道,“臣弟有两个奏议:其一是,要么不找,要找就动兵马,将三千甲士放入城中,关闭城门,挨家挨户搜查,闹他个惊天动地;其二是,趁机收手,留下话给周室,早晚寻到公主,知会秦室,秦室再行聘娶!”
嬴驷眼睛眯成一道缝:“如果由你决定,你选哪一个?”
公子疾语气坚决:“臣弟倾向于后者!”
“要是周室耍我呢?”嬴驷恨道,“偌大一个周宫,随便藏个人不是难题!”
“臣已使西周公荐给宫中两个线人,公主若在宫中,不可能藏久。”
“如果藏了呢?”
公子疾阴阴一笑:“果真藏了倒是好事!殿下可以奏请君上,以周室失道为由,出兵伐之!那时,周室输理在先,面对我‘正义’之师,还能不唯唯喏喏?”
“哼,届时唯唯喏喏怕已迟了,看我绝了他的宗祠!”嬴驷转对司马错,“司马将军,传令,拔营,回秦!”
从家中逃出后,苏秦一气跑到轩辕庙里,却见庙中干净整洁,空无一人。轩辕像前摆着三只烙饼。
许是饿极了,苏秦顾不上其他,拜过轩辕,将供品拿来,一路吃,一路赶向城中,到贵人居的那家客栈里,却见院门紧闭,门上挂着大锁。
苏秦纳闷了一会儿,来到客栈主人家,问他门上为何落锁,张公子何在,主人应道:“张公子昨晚已经搬走了!”
苏秦惊愕:“去去去哪儿?”
“张公子收到家信,说是母亲病危,连夜回家了!”
苏秦拱手问道:“张张公子家家家在哪哪儿?”
客栈主人走进房中,拿出一块竹简,道:“这是他们入住时记的,魏国河西,少梁东张邑!不过,听说现在这地方归秦国了!”
苏秦拱手:“谢谢店店家!”说罢转身走去。
店主扬手:“苏公子留步!”
苏秦站住。
店主跑向里间,拿出十几枚铜板:“昨晚小顺儿结账,仓促之间,多算了十三枚布币,这交给你,早晚见到张公子,替我还他!”说着将布币递给他。
“谢谢店家!”苏秦拱手谢过,接过钱,走向大街。
“看来,”苏秦思绪万千,“那日先生所言,当算灵验。昨日刚好届满六十日,我有大喜已是确认,贤弟母亲病危,若依先生所言,怕也是凶多吉少听那店主所说,河西少梁已归秦人,贤弟家乡也必成为秦地了。秦人野蛮,贤弟脾气又躁,万一有个差错,如何是好贤弟既已与我结下金兰之义,贤弟之母,当为我母,贤弟之家,亦为我家,于孝于义,我都不能置身事外!再说,贤弟走了,先生也走了,我正没个去处,何不走河西一趟?”
想至此处,苏秦伸手进袋,摸了下店家刚刚给他的一把铜币,信心十足地大步走去。
走有十几步,苏秦站住,心道:“此去河西,不知何日才能回来,该当去与琴师道个别才是。近日先生授课,明为指导琴室学子,实则点拨的是我,让我受益匪浅呢!”想到此,掉头走向辟雍方向。
苏秦匆匆走到辟雍,见守门老丈从门房里出来,紧忙迎上见礼。老人却如没有看见,笑呵呵地躬身候在门侧,给他个背。
苏秦正自惊诧,辟雍里面传来马蹄声,不一会儿,一辆宫车驶出来。苏秦让到道侧,与老丈一样躬身恭候。
宫车渐渐驶近,驶过大门。
突然,宫车在前面十几步外停下,车中传来一个沉沉的声音:“苏公子!”
苏秦吃一惊,抬头望去,竟是琴师。
苏秦既惊且喜,追前几步,跪地叩首:“晚晚生苏苏苏秦叩叩叩叩”
驭手拿过乘石,琴师吃力地走下,上前将苏秦扶起,退后一步,拱手还个礼,语气哀伤:“老朽见过苏公子!”
见琴师两眼红肿,苏秦大是诧异:“先先生,何何何何事伤伤伤悲?”
琴师抹下泪水,说道:“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哪!”
苏秦急切问道:“何何人欺欺欺欺负先先生?”
“非欺老朽,欺大周天子也!”
苏秦愈加惊讶:“何何人敢敢敢欺欺大大大大周天天子?”
“唉,”琴师长叹一声,“前番秦、魏聘亲,逼迫雪公主远嫁燕邦。此番秦人兴兵洛水,再次相逼,强聘雨公主。娘娘原本有病,经不住这些伤悲,已于昨夜驾崩。雨公主不堪相逼,出宫逃走,迄今生死未明,生死未明啊”
苏秦目瞪口呆,好半日,方才回过神来:“娘娘娘娘驾崩?雨雨雨公主出出逃?”
琴师抬头望天,悲从中来:“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堂堂大周天子,竟遭蛮夷之邦苦苦相逼,国破家亡,妻子离散,天理何在?天理何在”怅然出涕,泣不成声。
“先先先生?”
琴师看向他,以袖抹泪。
苏秦忧心道:“雨雨雨雨公主出出逃,秦秦秦人岂岂岂肯甘甘休?”
“唉,”琴师又是一声长叹,“该没的没了,该走的走了,他们不肯甘休,又能如何?老朽方才得到音讯,那些秦人,已于半个时辰前拔营起帐,走了!”
苏秦嘘出一口气:“走走走了好!”看向琴师,“先先生,您您您这是”
琴师泪水又出:“娘娘爱听老朽古韵,特聘老朽为宫廷琴师,还要老朽教导两位公主习琴。娘娘仙游,老朽这就去为娘娘再奏一曲,永诀”
苏秦恨恨道:“秦秦秦秦人可可可恶!”
琴师以袖拭泪:“唉,世道如斯,徒唤奈何?”向他一揖,“苏公子,老朽就此别过,入宫与娘娘诀别!”
苏秦回揖:“先先生慢慢走!”
琴师登上轺车,驾车离去。
苏秦追前几步:“先先生”
轺车停下。
苏秦追上,一拱手:“晚辈有有一求!”
琴师看向他:“你有何求?”
苏秦扑地,五体投地,声音颤抖:“晚晚辈求求为先先生弟弟弟子”
琴师摇头。
苏秦急了,连连磕头:“先生”
“唉,非老朽不收你,乃时过境迁,为琴不足以立世啊。说起这个,差点儿忘了,老朽方才喊住你,原为这个,让秦人一搅,竟就误了!”琴师从袖中摸出一只锦囊,“苏公子,请收好!”递给他。
苏秦接过锦囊,略怔:“先先生,此此为何何物?”
“是一个童子托老朽转给你的,你可拆开来看!”
苏秦拆开,扯出一块丝绢,上有一诀:“口欲不吃,歌唱吟咏!若想除根,鬼谷云梦!”
苏秦放下丝绢,看向琴师,不解道:“先先生,此此为何何意?”又将锦囊递给琴师。
琴师接过,看一眼,吸一口长气,闭目,良久,长叹一声:“唉—”
苏秦越发糊涂了,挠头问道:“先先生因因何而而叹?”
“时也,运也!你能有此机运,老朽恭贺了!”琴师拱手。
苏秦仍是一头雾水:“什什么机机运?晚辈愚愚痴,请请先先先生指指点!”
琴师声音沉沉的:“机运尽在偈中,你慢慢去悟吧!”将锦囊递还给他,再拱手,“老朽告辞!”
车子扬长而去。
苏秦端详锦囊,一脸疑惑,心道:“童子?”眼前浮出童子与鬼谷子形象,眉头一动,“想是那位白眉老先生指点我哩!歌唱吟咏?口欲不吃,歌唱”
晨起,韩国荥阳的一家客栈里,庞涓拿出钱袋子,倒在几案上,是十几枚一两重的小金饼和一些不同样式的布币。
孙宾洗漱已毕,走过来。
庞涓划拉出十枚小金饼,递给他:“孙兄,你到集市上买辆车,钱不多了,弄个二手的就成,得有点儿看相!”
孙宾笑笑,接过钱,袖入袋中,走出客栈。
不消一个时辰,孙宾赶着一辆新车回到客栈,兴冲冲地走到他与庞涓的住所,敲门。
门一开,孙宾怔了,因为站在门内的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汉子,一身宋商打扮。
孙宾吃一惊,拱手道:“仁兄抱歉,在下敲错门了!”退后一步,仔细察看,分明就是他与庞涓的住所,不禁纳起闷来。
络腮汉子盯住他:“仁兄没有敲错!”
孙宾听出声音,笑道:“嘿,是庞兄呀,你不张口,还真认不出来呢!”
“呵呵呵,”庞涓笑道,“孙兄再细瞧瞧,这身装饰像不像个宋商?”
“宋商?”
“是呀,宋商遍游天下,多我一人又有何妨呢?”
孙宾仔细审看一会儿,笑道:“嗯,挺像呢。”看向他的络腮胡须,“这副胡子哪儿弄来的?”
“呵呵呵,不只是胡子呢!”庞涓从袖囊里摸出一个袋子,打开,里面是不同样式的假胡子、假发、凝胶及其他杂物。
孙宾叹服道:“没想到庞兄有这几下子!”
庞涓恨道:“都是让那个奸贼逼的!”
“嗬,这下到安邑,再没人能认出庞兄了!”
“孙兄,”庞涓一本正经道,“打这辰光起,甭再叫我庞兄了,在下仍然姓龙,名水,是名宋商!”
“好咧。”孙宾夸张地行个大礼,“在下见过龙公子!”
庞涓拿过一身行头,递过来:“请孙兄试试这个,合身不?”
孙宾一看,是一套粗布褐衣,下人穿的。
庞涓回个深揖,语带歉意:“龙公子不能没个仆从,只能委屈孙兄了!”
“好呀好呀,”孙宾一脸兴奋,连连点头,“在下从小到大,还没穿过粗布衣呢!”高兴地穿上,走到镜前左看右看,乐得合不拢口,“呵呵呵,合身,合身,简直像是量身做的!”
庞涓嘘出一口气,给出个笑:“是孙兄体形好,穿啥都合身。”
孙宾学仆从的样子哈腰道:“小人见过主公!”
“哈哈哈哈,”庞涓大笑道,“看来孙兄是没有做过仆从呀!应该是这样,”学仆从见主子貌,躬身哈腰,“公子召小人来,有何吩咐?”
孙宾依样画葫芦:“公子召小人来,有何吩咐?”
庞涓昂首,语气傲慢:“车马置好了吗?”
孙宾朗声应道:“禀公子,置好了!”又做手势,“公子,请到院中验看!”
庞涓走到院中,果见一辆新车停在院中。
孙宾手指新车,脸上挂笑:“公子,此车如何?”
“好车,好车,好车呀!”庞涓上前抚摸车与马,满是欣赏,“马也不错!”转向孙宾,“这得多少钱哪?”
“卖主要金十三两,车八,马五。”
“可你只有十两!”
“许是卖主急需用钱,见在下诚心,就作十两卖了。”
“有这辆车马,嘿!”庞涓不无得意地重重咳嗽一声,拉长声音,“本公子欲走一趟安邑,起程!”
孙宾亦做足姿势,扶庞涓上车:“龙公子,请!” 天下纵横:鬼谷子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