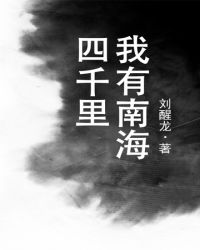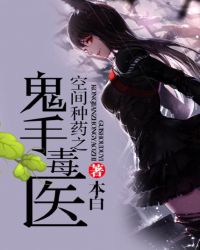任何人毕其一生,总会有几件极为在意的事情。作家也是如此,尽管一生中写作无数,真正让其内心无法割舍,甚至于时常牵挂的作品,或许只有那么几部,至于其他,写了也就写了,是非好歹任由他人说去。而这几部则不同,在我这里《圣天门口》就是这样的作品。尽管出版多年了,也还会有许多无法释怀的挂念。
《圣天门口》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九年十月,成稿于二〇〇五年元月,其间三易其稿,写了又废弃的文字不少于二十万字。刚开始写时,女儿还没有出世,到写作后期,女儿已经能够依在我的怀里,大声念着电脑屏幕上我正用键盘敲出的每一个字。曾经,我很想在扉页写上一句话:献给我的女儿及天下所有渴望长大的孩子!最终我只是将这份心情努力融入这部小说和所有其他小说的写作中。
因为在意,所以在乎。事实上,这是我放下钢笔,拿起电脑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完稿晚于另两部长篇,但开始写作却是最早的。对一个用笔数十年的资深写作者,将笔换成电脑宛如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社会变革,或者说是政治体制改革,她触及的往往是一些根本性的东西。社会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波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换笔在写作中所触及的根本,是写作者在书写汉字时的感觉,从先前的墨水的自然流淌,到后来的键盘叭叭断响,这就像羽毛球运动员,一般人所不能感觉的气流,哪怕是体育馆内多开了一扇门,都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我用了五到六年时间来适应,准确地说,是用《圣天门口》的全部写作来适应。事隔八年,有机会对当初出版的《圣天门口》进行修订时,对照最初的电子版,还能发现当初那些对电脑的不适应所出现的近乎可笑的错误。
改变还来自我对长篇小说文体的挑战。从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最初的几年,文学面对市场时普遍采取妥协姿态。“小长篇”的泛滥是其直接产物。二〇〇四年初,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的潘凯雄来汉公干。深夜突然来电约见。那天深夜,在亚洲大酒店顶楼的旋转餐厅,听说我在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他沉默着什么也没有说。半年之后的又一个深夜,已升任社长的潘凯雄突然来电话,开口就说,你那个百万字的大家伙我要了!那时他并不清楚我写的是什么,除了彼此的信任,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理由。要感谢的还有初版的责任编辑杨柳,对于此书的出版,我曾提出唯一的要求,责任编辑必须杨柳。那时我并不认识她,只是风闻王蒙先生的书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则指定由她责编。
《圣天门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令人满意的。仅说谢谢是无法全部表达一位作家的心情的。但也有遗憾。《圣天门口》初版后,有些气氛不正常。从交出电子书稿后,我就担心书中有些章节难逃斧削。待到墨香扑鼻的样书邮到后,匆匆打开来看,果然,自己最担心的几个章节,几乎尽数删去。后来,与潘凯雄见面,谈及删节文字应该先与我说一声,凯雄无奈地说,与你说,你肯定不同意,但又必须删,所以就不与你说。听着这样的大实话,我只能苦笑。
于我最关心的还是作品中“敌人”一词。如果说《圣天门口》有出众之处,其百万字所描写的近代中国生灵涂炭,纷争不断,却没有一次使用“敌人”一词。当我意识到作为后人,我们不可能再将先辈同胞间的乱战与争斗用“敌人”相称。在初版的《圣天门口》中,有些文字在编辑过程中被重新用“敌人”来表述与形容。这样的失误,当然是我的不主动沟通造成的,而应当在编辑之初,就将自己的思索告知责编。
二〇一二年夏,在亳州与魏心宏聊天,双方不经意地在寄语出版长篇文集的共识。那一刻,就想到给《圣天门口》出全本。心宏兄告诉我,书稿会交给谢锦责编,便更相信自己最近写过的一句话:世间一切偶遇,全是久别重圆。《圣天门口》当初被废弃了近二十万字,与谢锦其时所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弥天》的写作有关。因为答应赶写《弥天》,待回过头来续写《圣天门口》时,发现先前的感觉完全找不到了,而不得不重新开始。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太太,她用了整整半年时间,对照原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初版《圣天门口》进行订正,太太是职业编辑,很多时候她对编辑职责的执着几乎不顾我对笔下文字的独特感情。实际上,很多时候,她是对的。换了别人,也许就迁就了那些不算错误,但也与正确有距离的文字。什么叫一字情深?这也是一种表现吧!
二〇一三年五月于斯泰园 我有南海四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