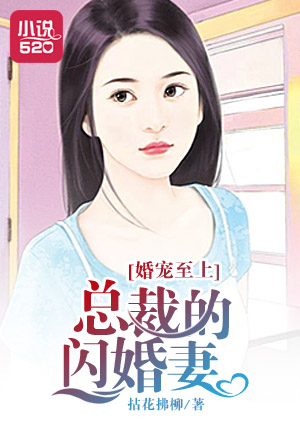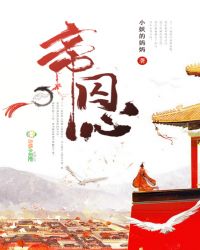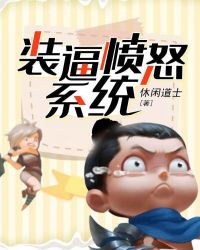§圈子与文学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本书里有一段话:中国人是喜欢画圈子的。这种偏好似乎是被“中国”这两个字所决定。在周代每一个封“国”都是用城墙将自己圈起来的山头。从字形本身来看,“圆”就是在一个圈内用“干戈”镇守住一批人口。
这倒未必,现在喜欢搞圈子的不只是中国人。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是很自然的,无论发达国家和落后地区,大致如此。不如此反倒是奇怪的。相对而言眼下中国这种情况还不算很明显。一次次政治斗争,把“搞小圈子”的名声搞得很臭了。
一提“圈子”就是小的,就让人想到“搞小集团”、“搞独立王国”,拉帮结派,拉一派打一派。其实搞政治斗争的人都擅于拉一派打一派。这个协会,那个团体,还不都是圈子?大家都在圈子里,无非大小而已。
要说“圈子”,在宇宙间地球就是个大圈子,从前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其实是两个小圈子。北约、欧洲共同体、欧佩克组织、东盟、七国首脑会议等等,更是一个个小圈子。越是四分五裂,小圈子就越多。
与之相比,中国的当代文坛,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像样的圈子。
无非是几个人或一批人,文学主张相近,情趣相投,结成一个松散的圈子。或者集结在一个文学口号之下,心照不宣,只是相互联系多一些,对话多一些,相互写些恭维的或名似调侃实则捧场的文章。甚至并非他们本人情愿,而是读者和社会,根据他们的作品和风格,把作家分成若干个圈子。比如,搞纯文学的圈子、搞现代主义的圈子、知青派、传统派、京味、湘军、晋军等等。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一批作家联合起来拍卖手稿,或携手创作电视剧,搞互助组、合作社。团结就是力量,既是生存的需要,又可鼓起一种向生活挑战的勇气。
文学似乎离不开一些圈子,哪个时代的文学总会分成一些圈子。
号称“建安七子”的是不是比较早的一个文学圈子?再加上当时的曹操父子,成了东汉建安文学的主力,对诗、赋、散文的创新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文学史上各种各样的圈子多了,竹林七贤、韩孟诗派、江西诗派、明末清初的复社,以及近代的新月派、现代派、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等。
岂止是文学,孔子死后他创立的儒家分成了八派。到了宋代以后,理学也分成三大派。甚至连庄严的佛教不也有许多派吗?
谁能说出这些派别有什么不好?
相反,我倒认为各种各样的流派丰富了文化园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圈子是少而松,易变。既无纲领,又无组织,多半是出于利益和需要的临时组合,遇有重大挫折便四分五裂,取得了成功也容易分道扬镳。这是由文人的素质和习性所决定的,他们宜散不宜聚。有些作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面对文学,背对文坛。文学圈子同“圈子文学”不是一个概念。历史上一个个文学圈子里的许多作品,同样会受到大众的喜爱,会传之久远。人有圈子,思想有圈子,而作品无圈子。“圈子文学”——似乎是专门写给自己的小圈子看的文学作品。假如不是情书,不是有特殊的原因和目的,那便是一种无奈,一种不得不做出来的清高和孤傲。
没有一个作家又想发表自己的作品,又希望阅读自己作品的人越少越好。没有办法感动众多的读者,便退回自己的小圈子里,如叔本华所言:“大家一起承受不幸,不幸就会减轻。人们似乎认为无聊也是一种不幸,所以聚拢来共同感受它。”既满足自身的需要,又能对抗周围的危险,甚至还可以口吐狂言:我们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不信两千年以后看,我们的作品是为未来的人写的。这话是无法验证的,也无人敢为这话打赌。
文坛上没有永久性的圈子,不断变化,分分合合。文学史是用作品写成的,不是由文人们一个个圈子构成的。如果人们记住了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圈子,也是由于他们的作品冲破圈子,扩散开来,流传下来。
不死的是文学,而不是任何圈子。
圈子的文学未必都能“不死”,被大众喜欢的文学也不一定都是短命。
大师级的作家不需要圈子,他们自己就成一派。往往是大师的弟子们才分派拉圈子。倘是有人“因作品不够,拉圈子来凑”,则无聊了。梭罗在《日记》里写过:“人们所谓的社交美德,亲密友情,通常不过是一窝猪仔的美德:它们挤在一起相互取暖。”
强大的文学不必借助于圈子,而圈子则必须依托文学,打文学的旗号,否则将变成别一样性质的组织和团伙。因此,今后的文学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圈子——这是一点都用不着奇怪的。充满生气、勇于进取的文学圈子,可活跃文坛,也有助于文学的繁荣。
我还相信,有关“圈子文学”的争论也还会继续下去。
1993年9月13日 蒋子龙文集.13,评与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