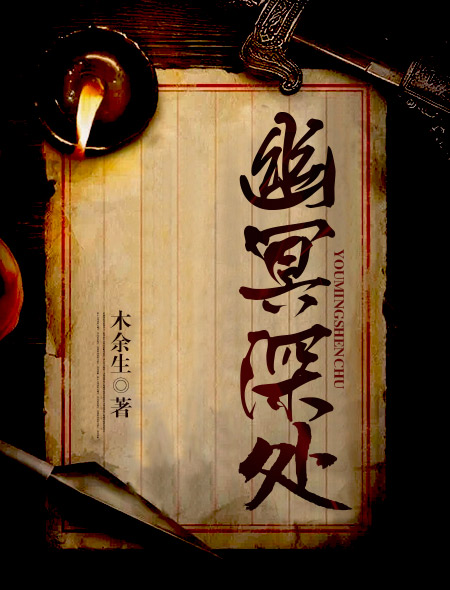随着落雪的迹象一天比一天明显,工地上的民工开始骚动起来。从早到晚都能听到民工们在大呼小叫,一会儿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过年,一会儿又直截了当地说,一年三百六十六天,被他们忙成了四百天,不管怎么说都要回家过个完整的年。虽然民工们没有闹事,指挥部的人还是越来越紧张。
山上不比畈下,一落雪就要封山,哪怕是机耕路也不敢走人。
为了落雪的事,王胜专门来指挥部开了一次会。王胜嘴上说,就是让所有民工留在山上过年,也要一鼓作气地将乔家寨水库建设好。实际上王胜比谁都担心,上万名民工若是真的被大雪封在山上,会闹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和年知广在会上一唱一和,逼着那些说民工们太累的营长们同意连搞几天夜战。并当场给每个营发了两只夜壶外加十斤煤油。
开夜战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腊月二十一,意蜂才回指挥部。
意蜂不仅将宛玉的招工表拿到手了,还将他与宛玉的结婚证也拿到手了。意蜂与宛玉结婚的日子和地点,与王胜和金子荷一样,也是腊月二十二,也是在乔家寨大队部。这些消息都是意蜂宣布的。
意蜂宣布这些事情时,宛玉躲在广播室里不出来。
意蜂说宛玉害羞,要大家别计较。
意蜂还是没管工地上的事,他在指挥部待了一个小时,便带着一个民兵,悄悄地穿过边界,到安徽那边去买东西,准备明晚宴请宾客。
温三和也到边界上转了转。那些买瓜子花生的安徽女子,一见面就笑嘻嘻地说:“秋儿已经回来了,正在家里等着你小温哩!”
温三和听出来她们是在逗自己,也跟着开玩笑:“秋儿要是回来了,肯定先来看我,不会让你们先晓得。”
安徽女子嘘了一声:“湖北佬脸皮就是厚,什么样的话都能说出来。”
温三和一点也不在乎,甚至觉得这话是说意蜂的。
安徽女子要温三和多买点瓜子,她们说,秋儿的父亲母亲一直不喜欢湖北佬,温三和若想做他们的女婿,就得将她们巴结得紧一些,她们会在秋儿父亲母亲面前多说一些温三和的好话。温三和说,他心里倒想这样做,可就是怕她们的丈夫知道,会从此不让她们到边界这边来。温三和得了便宜就跑,那些安徽女子只能在背后说,小心哪一天她们也会像工地的女湖北佬一样,将温三和裤子扒下来,量量他的尺码有多大,能不能让秋儿得到快乐。
天黑之前,女儿尖上的竖井里响了最后几炮。
没过多久,有人将那些用夜壶做成的煤油灯点着了,像撒星星一样挂在工地上各处。
依照事先排定的顺序,今晚轮到温三和值班。温三和往女儿尖走时,工地上所有的民工还在开夜战。负责打竖井的民工也在抓紧时间,将放炮炸松的土运出竖井。
夜越来越深了,一直在工地上转来转去的年知广,亲自下到竖井里看了一番,出来后才将一把钥匙交给温三和。
年知广一走,大坝上挑土和打夯的人群也跟着稀疏起来。
温三和站在女儿尖上,看到松盘营的马营长还在副坝上转悠,便努力地将耳朵对准马营长听过去。一会儿,果然听到马营长随身携带的袖珍收音机传出整点报时声。
工地上的人越来越少。
夜壶灯大概快没油了,忽闪忽闪地随时都有可能被风吹熄。
马营长站在一个记正字的女人后面,用脚尖悄悄地碰着她的屁股。记正字的女人回头笑一下,马营长便离开了副坝。没过多久,记正字的女人便收起手上的账本。一个男人见她摆出一副要走的样子,故意高声叫着,要她将头顶上的夜壶灯取下来,带给马营长。记正字的女人,毫不含糊地回敬那个男人,说是马营长早就发了话,等这盏夜壶灯里的油烧完了,就送给他,让他拿回去装酒过年。
记正字的女人顺着马营长走过的路,一溜小跑地消失在工地外围的黑暗中。
那些夜壶灯像是饿得撑不下去的人,终于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
最后一拨民工扔下手中石硪,喊着哦嗬,疯狂地跑开,将偌大的工地扔给温三和一人。
突然黑暗下来的工地上,有几只烟头在北风中断断续续地跳跃着。温三和正想着,马营长与那个记正字的女人,在这种穿着棉衣也冻得打哆嗦的野地里能做些什么,仍亮着灯光的指挥部里,突然响起一阵熟悉的歌声。
听得出,不是三用机在放唱片,是宛玉亲口在唱。
不管宛玉唱得如何好,温三和也无法找到过去对《阿佤人民唱新歌》的那份美好感觉。宛玉一直在努力地唱着。温三和一开始还能站在女儿尖的最高处听,过了一会,他就用年知广交给自己的钥匙,打开守夜的小草棚,躲避寒风,待在草棚里听。宛玉唱得很忘情,在区广播站时总也唱不出来的那些高音,全都按着节拍一个个地唱出来了。温三和慢慢地有些感动了,并且又想起早先他俩之间的那个约定。
一曲唱完,宛玉又接着从头唱起。
像潮水一样,一阵感动过后,温三和又冷静下来。他实实在在地想,就算这是宛玉在唤自己,也是为了弥补王胜离去后所留下来的空白。王胜不敢得罪乔俊一,已经百分之百地不再理睬宛玉了。随后冒出来的意蜂则是意外中的意外,与这个约定没有任何关系。温三和开始从心里由衷地佩服母亲。母亲说过,宛玉敢嫁意蜂,也有可能嫁给意蜂。在那种宛玉放屁,意蜂都没有机会闻的时候,母亲能做出这样的预言,并最终得以应验,足以证明她看人看事能入木三分。
一想到这些,温三和就觉得全身发冷。
草棚里放着一床用来值班的公共棉被。温三和正要打开棉被钻进去,手上忽然感觉到一种特别的冰凉。他用手电筒对着一照:棉被上有一块还没完全干透的精斑。温三和觉得很不好意思。明知不会有别人,还要将手电筒向草棚门口照了一下。回头再用手电筒往棉被上照射时,温三和发现棉被上竟有十几块边缘呈黄色,中间却是乳白的斑块与斑点。温三和冲着棉被愣了一下,然后极为生气地将棉被狠狠地踢了几脚。棉被滚了几下,空出来的稻草上露出一只花布角。温三和下意识地伸手一扯:一块揩过某种潮湿东西的花手帕,结成一团地悬在眼前。到这一步,再笨的人也明白:昨天夜里,有贪欢的男女在这里疯狂过。按照指挥部的排序,在温三和之前值班的是意蜂,因为意蜂没回来,只好由年知广顶替。
温三和的脑袋在一瞬间里胀得太大了,很多事都没法去思索,只能不停地回忆乔俊一曾经说过的话:男人心理压力太大了,最好经常找个女人睡一睡。年知广都这样了,那么在樟树坳的父亲哩!他也会这样吗?
草棚外像是有人在行走。
温三和一怔,正要出去看看,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
温三和厉声喝问:“干什么的?”
金子荷站在黑暗中柔柔地说:“别这么大声说话。”
温三和用手电筒照了一下金子荷的脸和身子。
金子荷将脸扭了一下避开手电筒的光亮,并没有想钻进草棚的意思。
金子荷说:“我晓得今天是你值班,我想到竖井里呆一下。”
温三和说:“竖井里黑咕隆咚的,还死过人。你一个人下去干什么?”
金子荷说:“我想下去哭一场。”
温三和心里直想笑:“女人哭嫁还要躲进地底下,难得你能想到这一点!”
温三和将搭在草棚外面的一架梯子,搬起来,放进竖井里。
他还没说请,金子荷就顺着梯子下到竖井深处。
转眼间,一缕哭声就从地下传出来。
温三和觉得很有趣,那声音就像是在井壁四周碰撞了几次,然后打着旋飘飞上来的。在这样感觉里,温三和一次次地想到夏季里常在学校操场以及农民的稻场上舞蹈的小旋风。几分钟后,金子荷的哭声发生了变化。不再飘飞,而是从心肝肺腑中一把把地掏出来,掷在地上,再反弹起来,像金属声一样尖锐锋利。温三和觉得情形不对,他用手电筒往竖井里照了几次,井底没有人,金子荷显然钻进哪个子洞里了。
金子荷大声地哭了半个小时后,终于喘了一口气。
温三和在上面听得都很累,以为她哭够了该歇下了。
他刚刚将绷得紧紧的神经放松下来时,一阵天崩地裂般的哭声从竖井里传出来。伴随着哭泣声的还有一声声叫喊:“老天呀!你让我去死吧!”
温三和一下子慌了手脚,他想也没想,就跳进竖井,三下两下地攀到井底。
金子荷哭得更厉害了。温三和还没站稳,金子荷就扑上来,将他抱得紧紧的,不停地大叫:“倪老师,你为什么要跑去坐牢呀!快来救救我吧!”
温三和用力推了几次也没有将金子荷从怀里推开。
贴着金子荷的耳朵,他大声地说:“我不是倪老师,我是温三和,倪老师是你的老师,我是你的同学!”
金子荷仍旧没有松开的意思,嘴里哭喊的内容却变了。“你这个挨千刀、挨万刀的温三和,我又没有请你来管我的闲事,谁要你自作聪明。我早就想好了,就让宛玉在前面替我挡着,她想和王胜怎么谈恋爱都行,我就可以趁机将自己的心藏起来。那样多好!你以为你是帮我。你晓不晓得,我这辈子就要毁在你手里了!到了这种地步,你说我有什么理由不和王胜结婚。你杀了我吧!要不你就将我强奸了,我恨王胜,你要不强奸我,我就没办法和王胜在一床被窝里睡觉,也没办法和他在一只锅里吃饭。”
说着,她像那个在工地上脱温三和裤子的女人,张开嘴,在温三和肩膀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温三和将金子荷抱起来,猛地抖了几下,并大叫一声:“金子荷,你疯了吗!”
这一声吼终于让金子荷平静了些,抱着温三和的手臂也柔软了很多。
片刻后,金子荷小声问了一句:“温三和,真是你吗?”
温三和说:“不是我还是谁哩!”
过了一阵,温三和又说:“我做梦也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
见金子荷不做声,温三和再次说:“你不要将问题的责任全推到我身上。只要你不想要乔俊一做靠山,你就可以不和王胜结婚!”
金子荷喃喃地说:“没有乔俊一,这辈子我就别想有前途。”
温三和大声地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倪老师有没有跟你说过,上大学的不能总是那些只会胡闹的人。只要我们有信心,说不定哪天机会就来了!”
金子荷继续喃喃地说:“你还没有完全了解倪老师,我晓得他,他说这话不仅是麻醉你,而且还有麻醉自己的作用。若不这样,他就没办法活下去!”
这句话一说出来,两个人突然不做声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金子荷才重新开口说话:“温三和你愿意帮我吗?”
温三和说:“倪老师同我说过多次,要我有机会时帮帮你。倪老师就是没有这样说,我也会帮你的。”
金子荷小声地说:“我想过,这会儿只有你能帮我,你要是不帮我,我就没勇气同王胜结婚。”
温三和说:“既然你想通了,要我做什么,你可以尽管说。”
金子荷又不做声。片刻后,她将一只手伸到温三和的手上,稍停一阵,才将它拿起来,放在自己胸前的一只纽扣上。温三和已经不会想别的了,黑暗中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那是金子荷的身子在微微颤动。温三和突然明白在自己与金子荷之间将要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心里一哆嗦,几个指头同时抖了起来。金子荷的棉衣很旧,纽扣与扣眼之间的空隙很宽松,温三和的手指几乎没做什么,棉衣上的第一只纽扣就被解开了。手电筒的光亮很弱,竖井里一派朦胧。一只影子般的手伸了过来。温三和每解开金子荷衣服上的一粒纽扣,就感到自己身上的纽扣也有一粒被解开了。棉衣被解开了!卫生衣也被解开了!最后的衬衣也被解开了!
一股女人肉体的芬芳炽热地扑过来!
温三和从没想过下一步该怎么做,天赋的本能让他准确地将自己的手指清晰地从那块属于自己人的滚烫肌肤上拂过。就在这一刻里,温三和的身子突然膨胀起来,他粗鲁地将自己的手折回来,实实在在地落在那处像火山一样隆起的肌肤上。那是一只没有任何遮掩的乳房,在它的近处,另一只乳房也很快地挺立在温三和的掌心里。温三和的思想和身体已经失控了,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迎上去。金子荷的胸脯像一只烧得正好的烘篮。温三和是一个穿着单衣过冬,而且正值饥寒交迫的男人,只要有烘篮在手边,他就无法不去理会那份温暖。就像是两只不需要桨与舵的小船,只要追随着相同的风,追逐着相同的浪,它们总会有共同的海湾。温三和抱着金子荷倒在地上,一股喷涌而出的泉水,很自然地顺着男人溪流,汇进它唯一想去的女人那汪深潭。金子荷的身子成了起伏的高山与深谷。温三和觉得自己成了山谷间一朵忽轻忽重的云,心里的风一刮起来,就不停地起起伏伏、沉沉浮浮。金子荷在不停地尖叫,温三和没有去想她在叫什么,他又听见郑技术员好久以前说话的声音:金子荷的乳房真的长在快要挨近脖子的地方,两颗坚硬的乳头距离近到真的可以相挨着的地步。而且金子荷的腰身屁股也真的像装了弹簧一样,温三和用自己的身子刚刚将它压下去,它即刻就挺起来,早早地等在空中。
温三和也想到一句可以使自己乱叫乱喊的话,每一次冲向金子荷时,他都会从全身肌肉里挤出三到四个字:“郑技术员——是个流氓——不教技术——教做爱——我现在也——做爱了——你该满意——了吧!”喊了几遍,温三和身子里从大肠到小肠,直到嗓门和舌根,一根筋似的抽搐起来。他还没来得及细想,所有的血液已经汇到一起,他昂起头,挺起腰杆,朝着金子荷的体内山崩地裂般喷发而去。如同那次在落令河边听到的枪响,又如同那天从这座竖井里爆发出来的哑炮,金子荷惊天动地地叫了一声:“倪老师——!”然后像一根绷直的弦,紧紧地挂在弓一样的温三和身下,直到最后一刻才和温三和一起坍塌在地。
温三和相信,在所有这些之后,自己很快就清醒过来。
竖井里响起金子荷正在离去的声音。
“我走了。十二点时,大队干部要到一起开会,研究年终分配问题。”
“你不能与王胜结婚了,你得嫁给我!”
“这不可能。我与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刚刚——”
“你还没想明白?有时候你不是你自己。有时候我也不是我自己。”通向井口的梯子有节奏地响起来了。一开始声音很沉重,到了高处反而轻盈起来。温三和痴痴地听着,当吱呀之声完全消失后,他恍惚察觉,这是一条人在升向天堂时的必由之路。坐在地底下,高大而坚实的女儿尖并没有压着他。他不知道让自己窒息的紧迫从何而来,他心里也没有好好思考其原因的念头。
也许是离地心的烈火近了些,竖井里很温暖,身边那些由爆炸形成的砂土中,散发着已经与岩石融为一体的白垩纪原野浓郁的芬芳。
那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处女之香!
心醉了,人却不醉。
心里感受着清甜,却不需要肉体的直觉与质感。
从炸药中释放出很多硫磺也没用,在长了根的白垩纪面前,种种的异味只能蛰伏在处女之香的脚底。
也许是夜深了,女儿尖上的风大起来。
大风刮起沙粒,接连不断地掉进洞口。
温三和听到竖井旁草棚的门响了一下。
他继续呆坐在洞底,只当是风吹的。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竖井旁出现了人的动静。
一个女人小声地冲着竖井井口叫了一声:“温三和!”
没过多久,女人又在上面叫了一声:“温三和!你在底下吗?”
听出是宛玉的声音后,温三和随口应了一声。
宛玉也听到温三和声音了。从竖井井口下到井底的途径,是由三架梯子交叉拉力完成的。朦胧之中,温三和看见一只浑圆的屁股,在自己的头上忽左忽右地摇摆着。他毫无欲望地望着那只屁股,并确信这就是那只自己曾经抚摸过,后来又被王胜抚摸过,并且很有可能已经被意蜂抚摸过的屁股。
井底很黑,温三和摸了好几把,也没发现那些被金子荷随手甩到哪儿去的衣服。等到他想起应该将最后那节梯子搬开时,从宛玉手里发射出来手电筒光束已落在他那赤裸的身上。
竖井井底的空气微微颤了一下。
宛玉差一点没有惊叫出来。
“我睡不着,心想,你一定在等我。所以,我就来了。”
“你把手电筒关了,不要这样照着我!”
“可是我很早就想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你错了,我这样不是给你看的!”
“我已经让你看够了,我晓得你早就想要我的身子。”
说着话,宛玉就开始解自己的衣服。温三和伸手从井壁上抓起一把沙土掷过去。宛玉冲着他回眸一笑,双手交叉抓住毛衣的下摆向上一带,半截雪白的身子就露出来。宛玉将自己的头从毛衣里扯出来后,剩下的事她要温三和来做。
“你这样子,还有精力陪三个男人玩!”
“你不要管别人,其实我真心喜欢的只有你。”
“要是我不再喜欢你呢?”
“除非你成了圣人。我们的暗号你忘没忘?”
“是那首《阿佤人民唱新歌》?”
“是的,我刚才一直在唱,你听到了吗?”
“说出来你不会相信,我已经不喜欢这首歌了!”
宛玉将手电筒的光束,缓缓地经由温三和的胸膛和肚脐,再顺着大腿一路滑下去。到了膝盖附近,便又开始回升。几次反复后,手电筒的光束突然消失了。等到它再出现时,宛玉已经将自己身上的衣物全部褪光了。宛玉的身子一点也不冷,像条火蛇一样,缠缠贴贴,不停地在温三和身上摩擦着。温三和的身子上没有一处是暖和的。特别是那刚刚被金子荷的体液淋湿过,又在风干过程中被带走许多热量的下身,更是像冰一样。不管宛玉身上对应之处如何地喷着火焰,仍旧是板着一副与其无关的冰凉面孔。温三和觉得那股始终在竖井井口盘旋的北风,终于吹到井底了。就像那几盏挂在工地上的夜壶灯,宛玉身上的烈火眼见着被寒风一点点地吹熄了。她从温三和的怀里退出去,然后快如闪电地将自己穿好了。在开始顺着梯子往上爬之前,宛玉对温三和说了一句,让人胆寒的话。
“假如我在明天的结婚典礼上突然悔婚,意蜂会将你一家送进牢里的。”
说着话时,木梯响了一下,紧接着又响了一下。
温三和的心里突然冒出一股原始的冲动。
“宛玉,你走不了,我要强奸你!”
温三和一边叫,一边将宛玉从梯子上拖下来,用力地摔在地上。
宛玉静静地躺在那里,一束手电筒的光亮从高高举起的手中落下来,将那朵盛开在女人身体最深处的墨菊照得铮亮。温三和久久地注视着它,直到它像一朵真正的花蕊那样完全开了,他才开始那坚忍不拔的挺进。宛玉完全没有抵抗。温三和很生气,一遍遍地说,不许宛玉感到快活,他要宛玉觉得痛苦。每说一次,宛玉身体的反应就激烈一分。温三和觉得自己身子像是被一条蛇缠上了,一种莫名苦楚在心里弥漫起来。就在温三和将要倒塌之际,宛玉熟练地翻了一个身,趴到上面。憋在温三和心里的那些话再也叫不出来,他想将自己从宛玉的身下摆脱下来,潜意识里又有百般的不舍。宛玉蹲在自己的身上,那样子就像座山雕在杨子荣的马刀下不停地蹦跳。温三和一遍遍地想着曾经被女人强奸过的马为地,直到宛玉满意地抽身站起来,他还没弄明白,到底是自己强奸了宛玉,还是宛玉强奸了自己。
临走时,宛玉非常认真地亲了温三和,一边亲一边伤感地说了几句谢谢之类的话。
宛玉走了,连同长木梯的吱呀声一起消失了。留下一只不算太大,却也不小的窟窿,缀在没有星光的天上。
几颗冰凉的雨滴从窟窿里飘落下来。
不大的寒意一下子闯进温三和的心里。
温三和在竖井里一直待到有查夜的小分队民兵过来唤他时,才从里面爬起来。此刻的天空正处在黎明的边缘,他对在黑暗中什么也没发现的民兵们说,这种时候,凡是空着暖被窝,不让男人进去的女人都是阶级敌人。民兵们一个个放声大笑,直到笑够了才夸温三和太有思想了,应该为此再写一首诗。
天亮之后,天上的雨开始下成串了。
温三和没有地方去,只好钻进被几棵松树荫护着的厕所里。他刚蹲下,年知广就跟了进来。两个人紧挨着蹲了片刻后,年知广从上衣荷包里掏出一封信,一声不吭地塞进温三和的手里。温三和一看信封上的字是倪老师写的,立即紧张起来。年知广像是知道温三和要说什么,他有意无意地使了个眼色。
“不要问我这信是从哪儿来的。看完后,烧了它。”
说完这句话,什么也没拉出来的年知广便提着裤子走了。
写明了交给温三和的信,已经被人拆开过。
温三和顾不了这些,他迫不及待地抽出信笺。雪白的信纸上除了一道“求X如何才能等于80”的数学公式,别的什么也没有。
温三和觉得这道数学公式很熟悉,特别是其中的1400更像是在哪儿见过。
正在用心琢磨时,一个安徽女子撩开挂在厕所门口的麻袋,闯了进来。见到温三和,那个安徽女子愣愣地退出去时,嘴里连说了几句,她问过有人没有,温三和怎么不回答。
安徽女子大概走到指挥部门口了,她大声地问:“听说这儿有人要结婚,想不想要猪肉、瓜子等东西请客,如果想要,我可以帮忙在安徽那边买好送来。”
意蜂一定从广播室里出来了,他用很响亮的声音回答:“是我要结婚。我不要你们安徽的东西,你们安徽的东西,都是资本主义的草,吃下去肚子不疼头就会疼。”
见话不投机,安徽女子转身回到厕所门口。
等着温三和出来了,安徽女子对他说:“秋儿到现在还没回来,他家里的人着急,锁上门上安庆找她去了。”
安徽女子还说:“要是秋儿出事了,真不晓得是谁的责任!”
温三和说:“你们安徽不是什么都好吗?怎么会出事哩!”
安徽女子说:“我们安徽百事都比你们湖北好,就只一宗不好:男人多,女人少。所以时常有女人被骗子贩卖。”
温三和往工地方向走了几步。
已经钻进厕所里的安徽女子大声叫起来:“你们湖北佬的厕所总是这样臭,肯定一日三餐没吃多少油。”
冷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
温三和的心思迅速回到倪老师的怪信上。在工地上转了一圈后,温三和突然想起,县公安局的李胖子和县中队的马指导员曾经让自己看过一道数学题。他匆匆地赶回指挥部,从自己的枕头下面翻出那本《战地新歌》,找到夹在其中的那张纸一看,果然与倪老师信中唯一所写的数学题一模一样,也有一个非常晃眼的“1400”,也是“求X如何才能等于80”。温三和拿出钢笔,按照读书时老师教的方法,先计算出这道题的得数,随后又验算了一遍。看上去结果是正确的,温三和却难以相信,他觉得倪老师不会无缘无故地写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数学题,其中一定含有更多的东西。
当温三和为这不知所指的数学结果绞尽脑汁时,意蜂正在隔壁广播室里不断地催促,要宛玉赶紧随自己去供销社买的卡和的确良布。意蜂已经找好了裁缝,现在将布送去,还能赶着做两套新衣服。意蜂知道王胜家给金子荷做了一件灰色的卡上衣和一件蓝色的的确良裤子。意蜂说,他不能让自己的新娘在结婚典礼上显得比王胜的新娘寒碜。宛玉扭扭捏捏的,像是不肯随意蜂出门。意蜂说得口干舌渴后,终于将气撒到温三和的头上。他从广播室里出来,径直走到温三和的身后,不怀好意地要求温三和马上请假回家去。
温三和的心思还没转过来。
他说:“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到时候再一起回去。”
意蜂探头看着那些稀奇古怪的X和80,嘴里说:“你这样子,简直就是不想回家过年了!”
意蜂的话音一落,温三和的心里便猛地一紧。他下意识地将摊在床上东西拢到一起时,不小心让倪老师的信闪了一下。
意蜂像是发现了,一边伸手来抢,一边说:“我有一封信丢了。你给我看看。是不是偷了我的。”
温三和将意蜂的左手扒到一边,意蜂的右手又伸过来。
意蜂说:“我跟你明说,那信是逮捕姓倪的那天,从他身上搜到的。我们一直在分析它是什么方面的罪证!”
这时,隔着墙,宛玉大声叫着意蜂:“我跟你去做衣服就是,干吗要找别人出气!”
见意蜂没有动,宛玉跨过两道门槛,生生地将他扯走,嘴里还说:“温三和是喜欢过我,我也喜欢过他,可这种喜欢是姐弟之间的喜欢,与你没有关系。你要是冲着温三和吃醋,往后你只有成天弄根绳子将我系在你的裤带上。”
意蜂心有不甘,却经不住宛玉用力扯两下。
临出门时,宛玉回头深深地看了温三和一眼。
“你听意蜂的话没错,回家去吧,家里总有你想要做的事。”
温三和不敢耽误,他往火盆里添上几只在窑里没有烧透的栗炭,然后借口烟太浓,端起火盆走到屋外。北风一吹,从那些没有烧透的栗炭里窜出一股黑红色的火苗。温三和将倪老师写给自己的信,扔进火里时,已经走到山坡上的意蜂正好回头看见了。
意蜂想往回跑,却被宛玉死死扯住。
宛玉大声地问意蜂:“今晚上的婚,你还想不想结!”
意蜂挣扎了几下后,还是悻悻地走了。
山坡上留下宛玉最后一眼回望时飘落下来的许多忧伤。
几个来指挥部领炸药的民工,从旁边走过时,故意将一节只有一寸多长的导火索扔进火盆里。燃着的导火索咝地一声,将火盆里炭灰冲得老高。等温三和反应过来,民工们已经跑远了。因为有雨,沾在身上的炭灰越拍打越显眼。试了两下,温三和正要放弃,年知广不知什么时候走近来,轻轻地笑了一下。
温三和心有不甘地冲着远去的民工说:“哪天认出他们了,一定要想办法扣他半个标工。”
年知广说:“要是没下雨,就是倒在栗炭灰里打个滚,爬起来拍一拍也就没事了。”
顿了一下,年知广抬起头来望着阴沉沉的天空说:“这种毛毛雨,能有多少降雨量?能增加多少库容的水?”
听着这没头没脑的话,温三和心里像插进一把钥匙那样响了一下。
他用目光盯着年知广。
年知广却不再吭声了,弯下腰抱起仍在冒着黑红色火焰的火盆,径直走进大门。年知广像是捡了个大便宜,一只脚还在外面,就冲着屋内高喊,让中午不要打他的米,他要留着肚皮,晚上到王胜和意蜂的婚宴上多装一些肉。
温三和没有心思听年知广开玩笑,他感到有种很重要的东西正在自己思想深处萌芽。他甚至听得见,这种萌芽像春天的竹笋在地底下往外冒一样,发出叭叭的拔节声。随后的某个瞬间里,温三和终于想起来:倪老师信中所写的数学题中的1400,正好契合乔家寨大队的年平均降雨量一千四百毫米!温三和记起来了,早先郑技术员非要自己多看看的,挂在乔家寨大队部墙上的那幅示意图上,就是这样标示着的。温三和将潮湿的脸抹了一把,转身跑进屋里,重新摊开那道数学题。现在,温三和完全明白了。倪老师用普通人都会的方式,来计算乔家寨水库的库容。温三和相信,这道数学题预先给予的结果80,就是自己在乔家寨听说过无数遍,并且自己也无数遍对别人说过的水库总库容。倪老师只是没有给出得数的单位,如果倪老师将80写成80万立方米,温三和就不会花费如此多的心机。数学题中的1400,无疑就是年降雨量了。那个X,毫无疑问是代表自己一直未知的乔家寨水库的承雨面积。
温三和冲到外屋,大声地问:“有谁晓得这座水库的承雨面积是多少?”
正在吃早饭的十来个人,全都愣了。片刻之后才有人说:“你是水电局派来的技术人员,这个问题要问你自己。”
温三和正不知如何回应,年知广说:“我只晓得乔家寨的总面积是多少平方公里。”
温三和说:“我也晓得乔家寨的总面积是多少平方公里,我要的不是它!”
年知广不动声色地说:“大家不是都在宣传,这座水库修成后,将会有效地控制乔家寨全大队三分之一的来水量吗?”
到这一步,温三和已经不需要再用笔了。他在心里默算过一遍,随后又拿出地区水工队老何、老向送给自己的那本《小流域水利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对照着再默算了一遍。温三和实在不敢相信,按照乔家寨水库80万立方米的库容计算,必须有相当于乔家寨大队总面积的承雨面积,才有可能让水库库容百分之百地发挥作用,然而实际情况是,乔家寨水库只控制了乔家寨大队三分之一的来水面积。
温三和忍不住吃起惊来:“照这样计算,乔家寨水库将有三分之二的库容永远只能装阳光和空气!”
见大家都不做声,温三和再次叫道:“照这样计算,先前的小水库就够用了,根本就用不着再扩建!”
话音刚落,大家便纷纷放下筷子,拿起没有吃完的馒头,像受了惊的鱼儿一样,拥挤着往外走,顷刻间便在门口消失得无影无踪。
年知广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坚持将该吃的东西吃完了。
临出门时,年知广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年头,好多东西都得藏起来,若不藏起来,说不定哪天自己的身家性命就保不住了!”
屋里的栗炭火烧得很旺,温三和伸出双手独自享受这份温暖,心里却是冰凉的。
突然之间,他明白了很多东西:年知广在工程的后期执意要往核心墙里填进黄沙土,是因为他早就明白这座水库的一半以上的库容是用来装所谓“精神”的。乔俊一可以放心地看着清一色的黄沙土被挑进核心墙,刘局长可以放心地将一座动员了万余民工的水库工程交给刚出校门的高中生,二〇一首长对着军用地图看了一眼便带着最看重大寨精神的部队一走了之,郑技术员临走前发表的那番关于男女性事的高论——一切的一切,都在昭示着,这些身处要冲的人,早就了解乔家寨水库的虚与实。
温三和刚明白一些事情,马上又陷入更深的迷惘。这么多人中,只要有一个人说出乔家寨水库的真相,如此成千上万的民工,就不用白白花费一个冬天,来做这种除了劳民伤财,再无半点功效的劳动。 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