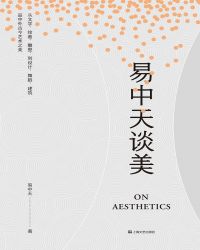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易中天谈美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CHAPTER 05
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构成
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民族,生命活力是中国艺术精神最核心的内容。体验着生命的是情感,传达着情感的是意象。意象圆融物我,是情感的理性化;线条抽象单纯,最能体现理性精神。因此,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结构,就可以概括为这样由内向外的五个层次:最核心最内在最深层的是生生不息运动不已的生命活力;其次是与天地同和、有节奏有韵律的情感律动;第三是主客默契、心物交融、情景合一的意象构成;第四是无偏、有节、尚中、美善合一的理性态度;最后是抽象、单纯、韵味无穷的线条趣味。它们分别对应着气、情、象、法、言五个范畴。如果借用最具代表性的几种艺术样式来作象征,则可以艺术地描述为舞蹈气势、音乐灵魂、诗画意境、建筑法则和书法神韵。
〚一〛生命活力
以生命的眼光看世界,把包括从自然到艺术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看作活生生的生命体,这是中国人的哲学观,也是中国人的艺术观。《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宇宙观的哲学表现;讲究风力、骨力,则是这种宇宙观的艺术表现。中国艺术历来讲风骨。《文心雕龙》有“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之说。什么是风骨?我以为风骨都本之于气。气动万物就是风,动而有力就是骨,它们都代表着一种永不消亡的生命活力。风以其动感表现其“活”,骨则以其坚挺表现其“力”,所以风骨也就是活力。具体到艺术,则风讲动人之情和飞动之势,骨讲立人之本和内聚之力。中国古代优秀的艺术作品,无论何种样式、形态、风格,都无不讲究风骨,讲究活力。或者说,讲究气势。
气势,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核心就是气。有气才有势,而气象万千、气韵生动也和气势磅礴一样,向为中国美学推崇和赞许。对于中国艺术来说,气,往往比情(内容)和采(形式)还要重要,还要根本。所以,在创作中,元气淋漓、大气磅礴、法备气至、神完气足者为尚,索莫乏气、骨气不足、乏其生气、气竭声衰者为劣。绘画要“气韵生动”,作文要“一气呵成”,都是这个道理。
什么是气?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中的气,其实也就是生命或生命本体。作为生生不息、弥伦万物的生命本体,它往往又被称为“元气”。实际上,它无非是人能够感觉到而不能科学表述的生命力或生命感。但是,这种生命力或生命感,却易于为艺术尤其是易于为舞蹈所体验。闻一多先生在其著名的《说舞》一文中曾极其深刻地指出:“舞是生命情调最直接、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在这种表现中,舞蹈者通过自己人体的律动,可以体验到一种生命的真实感,而观赏者受其感染,也得到同样真实的生命感。闻先生认为,舞蹈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也就是说,舞蹈,乃是最宜于表现生命活力的一种审美形式和艺术样式。
因此,中国的许多艺术都接近于舞蹈,趋向于舞蹈,有着舞蹈的气势,甚至可以广义地看作是舞蹈。其中,最典型的是书法、绘画和戏剧。中国书法和绘画中的狂草和写意简直就是纸上的舞蹈。雪白平展的宣纸有如灯光照射的舞台,柔韧飞动的毛笔有如长袖善舞的演员,艺术家凝神运气,泼彩挥毫,墨花飞溅,笔走龙蛇,酣畅淋漓,气象万千,其制作过程本身便极具表演性和观赏性。难怪张旭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悟笔法,吴道子作画要请裴将军舞剑以助壮气。至于戏曲,则更是以舞蹈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歌舞演故事”,正是中国戏曲不同于西洋戏剧的民族特征之一。西洋的戏剧,话剧是话剧,歌剧是歌剧,舞剧是舞剧,而中国的戏曲,却集诗、歌、舞于一体。不但唱的时候要舞,不唱的时候,其舞台动作,也是节奏化程式化亦即舞蹈化的。舞蹈性,几乎成了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特性,而作为中国艺术精神内核的生命活力,也就可以象征性地描述为“舞蹈气势”。
〚二〛情感节律
对生命活力的感性体验、审美体验和艺术体验只能是一种情感,而热爱生命的民族必然重情。什么是“情”?“情”这个字,从“心”从“青”,而“青”则是草木的春色,是植物生命力的象征。对于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农业民族来说,“青”无疑是一种美丽的颜色。故天空之美者曰青天,季节之美者曰青阳,妇人之美者曰青娥,年华之美者曰青春。在汉字中,从“青”之字,不少都带有“美”的意思。比如日之美者曰晴,水之美者曰清,言之美者曰请,而心之美者曰情。这样说来,则“情”,也就可以理解为“心灵的绿色”“心灵的美丽”和“心灵的活力”了。
艺术不能没有美,也不能没有生命活力,所以艺术不能没有情。中国艺术十分重情。《礼记·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由音乐理论揭示出来的艺术的情感特征,是中国美学的核心。中国的艺术创作、艺术欣赏、艺术理论和艺术精神,一以贯之的就是一个“情”字。不但音乐是情感的表现与传达,诗、舞蹈、戏剧,甚至绘画、书法、雕塑、建筑,也无不是情感的表现与传达。在中国人看来,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是不能算作艺术家的,一件没有人情味的作品也是不能算作艺术品的,而一个没有人情味的自然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中国人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强调自然的客观性、外在性和疏远性,而是更看重自然的向人性、宜人性和拟人性。也就是说,更看重人与自然的情感性。因此,中国艺术的逻辑,就是情感的逻辑;中国艺术的真实,就是情感的真实。依此真实,就不必拘泥于外形的酷似、物理的真伪;依此逻辑,就可以反丑为美、起死回生。抽象、写意,是不求外形的酷似;夸张、变形,是不辨物理的真伪;《文心雕龙》所谓“鸮音之丑,岂有泮林而变好;荼味之苦,宁以周原而成饴”,是反丑为美;汤显祖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是起死回生。
这样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生存空间无疑是一个充满了音乐情趣的时空综合体。在这里,空间方位(东西南北)往往变成了时间节奏(春夏秋冬)甚至情感节奏(喜怒哀乐)。郭熙《林泉高致》提出的“三远法”(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中国的艺术家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世界。的确,在摆脱了物象的束缚和摒弃了物理的限制后,世界对于艺术家,就几乎只剩下节奏和韵律。首先是道的节奏、元气的节奏和心灵的节奏,然后表象为艺术,成为抽象的色、线、形、体、音的节奏,和具象的时、地、人、物、景的节奏。至于笔墨的节奏和四声的节奏,则更为中国艺术所独有。
如果说节奏较多地注意到量的变化,那么,韵律便更多地注意到质的不同。节奏更多自然性,韵律则更多人为性。从节奏提升到韵律,也就是从自然提升到艺术。所以,韵律也必然为中国一切艺术所共有。绘画讲“气韵”,书法讲“神韵”,诗词讲“韵外之致”,音乐讲“流风余韵”,戏曲讲“韵味无穷”。韵或韵味,往往是比一般意义上的“美”更重要的东西。
什么艺术最重情感,最讲节奏和韵律?音乐。在中国人看来,音乐和天地宇宙一样,都是既节奏井然,又韵味无穷的。这就是和谐,这就叫“大乐与天地同和”。因此,重情感、讲节奏、讲韵律、讲和谐的中国艺术,便都贯穿着音乐的灵魂并接近于音乐:书法绘画的笔墨是视觉化的音响,诗词是无伴奏的独唱,建筑和园林则或者是黄钟大吕的交响,或者是丝竹弦管的奏鸣。中国艺术的世界,是一个音乐的世界;而中国艺术精神美学构成的第二个层次——情感节律,也就无妨称之为“音乐灵魂”。
〚三〛意象构成
主观的、仅属于个人的情感只有在对象化以后,即只有借助于“象”,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得到普遍的传达。因此,中国艺术便必然以情感为生命,以意象为构成。象,是中国美学又一个重要范畴。中国美学的“象”,从来就不等于西方美学的“形象”,毋宁说是“有象无形”“去形存象”。《易·系辞》说:“见(现)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现象”不等于“形器”。形器(形)是事物的实体,而现象(象)则是事物的表象。对于艺术来说,事物的实体是不重要的,重要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表象作为事物的反映,是一种心理现象,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它可以在人的头脑中复现,这就是回忆;也可以在人的头脑中运动、变化、重组甚至创造,这就是想象。心理学的研究证明,人在回忆和想象时,往往伴随着情感。对于惯常用情感眼光看世界,又区分了实体(形器)和表象(现象)的中国艺术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于是,“象”在中国艺术这里,就不但不是“形象”,也不单单只是“表象”,更重要的还是“意象”。
意象是抽离了“形体”又蕴含着“情意”的表象,或者说是“有情感的表象”。但必须特别指出,意象决不是意与象的两两相加或简单契合,而是意中有象,象中有意,物我同一,主客包容,既非纯客观的如实摹写(如西方古典艺术),也非纯主观的自我表现(如西方现代艺术)。显然,这是中国独有的宇宙观、哲学观在艺术中的体现。
意象是中国独有的美学范畴,意象造型观也是中国独有的艺术观念,而诗画艺术则是这种艺术观的集中表现。“赋比兴”作为中国诗歌的金科玉律,“传神写意”作为中国绘画的传统观念,都涉及意象问题。前者讲意象的目的(传达情感),后者讲意象的特征(不求形似)。因为不求形似,所以更注重笔墨(笔墨比物象更接近审美心灵);因为传达情感,所以要借助意象(意象比概念更易于传达情感)。情感靠意象传达,意象靠笔墨构成,情感—意象—笔墨,这就是中国诗画艺术的基本结构。无疑,在这里,意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中间环节。一般地说,中国诗更重情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画更重笔墨(具其彩色则失其笔法),但它们都离不开意象。正因为它们都以意象为美学构成,所以中国诗常有画境,中国画也常有诗意。这样,意象就作为一个中介,把诗和画统一起来了。如果说,西方美学讲究的是诗画对立,那么,中国美学追求的则是诗画一体的“诗情画意”,是情景合一的“诗画意境”。
所谓“诗画意境”,就是主客默契,心物交融,对象中有自我,自我中有对象的那样一种境界。中国的诗和画都追求这种意境。中国的诗论讲究的是“情景合一”,中国画论讲究的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哲学观,情景合一是中国人的艺术观。在这两种观念的主宰下,中国艺术家无论是以“移情”的态度看待自然(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还是以“直觉”的方式把握对象(情景合一,自得妙悟),都不难达到这一境界。
所以,中国的其他艺术,也和诗画艺术一样,有了一种交融物我、综合时空的审美特征。书法就其表现方式而言,是空间的;就其观赏方式而言,却是时间的。在书法作品中,静态的空间结构往往转化为流动的时间节律,从而既与观赏者的审美心理“同构”,又与之“同律”。 戏曲亦然。漫长的时间,辽阔的空间,仅仅表现为几个极其精彩优美的动作和身段。这和杜诗所谓“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和国画《百花齐放》将不同地域不同季节开放的花画在同一画面,是一个道理。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法,更是一种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就其化空间为时间而言,是音乐的;就其化时间为空间而言,是舞蹈的;就其融主观客观、对象自我、表现再现于一体而言,则是诗和绘画的。总之,它是中国艺术独有的一种境界。
〚四〛理性态度
情感的对象化或者说意象化,也就是情感的理性化和形式化。因此,理性态度便是中国艺术不可或缺的精神。如果说生命活力主要表现于舞蹈,情感节律主要表现于音乐,意象构成主要表现于诗和绘画,那么,理性态度便主要表现于建筑。建筑是艺术中的哲学。所谓“建筑法则”,就是哲学的法则,理性的法则。
一般地说,西方的艺术更近于宗教,中国的艺术则更近于哲学。中国的哲学主要是伦理学的,而非逻辑学和宗教学的。中国建筑的代表作,也主要不是供神使用的祭坛和教堂,而是供人居住的宫殿和园林。即便寺庙建筑,也像中国的宗教一样,较少天国色彩而极富人间气息。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宫殿府邸、园林别墅、寺观坛庙,正好分别对应着中国的三大哲学流派——儒、道、释。
儒道释三家哲学的共同特点,是都讲辩证法。表现于建筑这种分割空间的艺术,则首先是如何处理充实与空灵的关系问题。大体上说,儒家讲充实,道家讲空灵,佛家既讲充实,又讲空灵。或者说,强调经世济民,注重实用价值的讲充实;强调超凡脱俗,注意审美趣味的讲空灵;而主张“立地成佛”的则既讲充实,又讲空灵。具体到艺术,大体上是舞蹈、雕塑、绘画讲充实,音乐、书法、诗讲空灵。再具体到建筑,则宫殿府邸讲充实,园林别墅讲空灵,寺观坛庙既讲充实,又讲空灵。中国的寺庙建筑形式多如宫殿,却又多建于山林之中,便正是这种观念所使然。
可见,充实与空灵,乃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可以而且应该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并统一于同一艺术样式或艺术作品之中。中国的宫廷建筑多留空地甚至还要穿插园林。中国画画面多留空白,戏曲、舞蹈不用或少用布景和道具,雕塑多不注重细部,是为了求空灵;园林要“借景”,诗要“咏物”,书法偏重“中锋”,是为了求充实。总的来说,中国艺术的法则是亦虚亦实,虚实相生。虚不是空虚和虚无,实也不是僵化和刻板,而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空灵的风格表达着充实的内容,沉着的风骨表现为飘逸的情趣,就像中国许多建筑都有着稳重的石基和灵动的飞檐一样。
中国艺术之所以既讲充实又讲空灵,是因为它既要讲格调,又要讲趣味。有格调则典雅,有趣味则高雅。反之,无格调则鄙俗,无趣味则粗俗。要言之,格调关乎道德,而趣味关乎审美。格调与趣味的统一,也就是道德与审美的统一。在中国人看来,不道德的东西是不美的。反之,善的也必定是美的。美善合一,也是中国艺术的精神之一。一个人,如果道德高尚,内心充实,格调也就一定高;如果超凡脱俗,飘逸虚灵,趣味也就一定雅。人如此,艺术品亦然。
但是,格调与趣味,毕竟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不同的艺术家,就各有侧重。大体上说,中国美学前期重格调,后期重趣味;诗重格调,词重趣味;楷书重格调,行草重趣味;宫廷建筑重格调,民间园林重趣味;尊孔孟者重格调,近庄禅者重趣味,等等。然而偏重则可,偏废则不可。只讲格调不讲趣味,便难免失之呆板;只讲趣味不讲格调,便难免失之轻浮。这两种倾向,都不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所赞同。
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崇尚的,乃是一种无偏、有节、尚中的理性法则和理性精神。这是中国建筑的法则和精神,也是中国一切艺术的法则和精神。中国艺术作品中表现的情感,往往带有伦理色彩,奋发而不激越,忧伤而不绝望,欢欣而不迷狂,悲哀而不凄厉。中国艺术的形式,也极重规矩和法度,比如诗词曲讲格律、山水画讲皴法、戏曲和舞蹈讲程式等等,都是。虽然也有“无法之法,是为至法”的说法,但这里的“无法”其实仍然是“有法”,只不过对“法”的运用,已经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因此看似“无法”而已。更何况,所谓“无法之法,是为至法”,岂非一种很高的哲学境界?
〚五〛线条趣味
最能体现理性精神的审美形式是纯净的、线条化的艺术语言。与色彩相比,线条确实要更理性一些。对色彩的把握往往只需要感觉,对线条的把握却多半需要理解。中国不但有纯粹的线条艺术——书法,而且中国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接近于书法,有着书法的神韵。所以,四六骈文终于不再行时,金碧山水也逐渐让位于水墨山水,小说多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戏曲也把布景道具减到不能再减。总之,中国艺术总是尽量用纯净的线条、洗练的笔法和抽象的程式来表现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因此,它们都可以广义地看作是一种“线条艺术”。或者说,以“线条趣味”来造型的艺术。
当艺术主要由线条语言或线条化的语言来造型时,它体现和造就的审美趣味,也就必然是一种线条的趣味。“抽象”是这种趣味的第一原则。如果说中国画的抽象是“抽而有象”,那么,书法就差不多可以说是“抽而无象”。严格说来,以象形为本源的汉字,只是书法的素材,而不是书法的本质。书法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线条的艺术,而线条恰恰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唯其如此,书法才终于由比较“像”的篆隶,发展为不那么“像”甚至根本“不像”的行草。
抽象造就的艺术风格是单纯。书法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没有具象形象,没有光影、明暗、透视,也几乎没有色彩,可以说是单纯得不能再单纯。单纯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品位,也是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这种境界可以一直追溯到《周易》美学:“上九,白贲无咎。”贲即文饰。白贲,即饰极返素的无饰之饰。文饰是繁复,文饰到极点以不文饰为文饰,就是单纯。这就叫“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可见平淡不是枯淡,单纯也不是单调,而是把绚烂和繁复当作被扬弃的环节包含于自身之中。它是一种更高的品位。它是书法艺术的追求,也是中国一切艺术的追求。比如中国画不求形似,是抽象;多用水墨,是单纯。
线条艺术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抽象单纯的线条固然更有利于艺术家们挥洒自如地充分表现,也同样有利于欣赏者们浮想联翩地自由想象。诚然,对线条的感受、领会、理解和把握较之其他艺术语言要间接得多、困难得多,但正是由于这种间接性,才不但给欣赏者留下了自由想象的余地,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不但要“看得懂”书面、画面、字面上的东西,更要“看得出”书面、画面、字面以外的东西。在中国美学看来,前者其实是不重要或不那么重要的,后者才是精髓所在。这一点,最能为书法的欣赏所证明: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审美能力,那么,除了看见几个半生不熟的汉字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线条外,你还能看见什么?书法毕竟不是写字,也并不仅仅只是字写得好。其不同之处,便正在于真正的书法艺术作品,不但要有好看的视觉形象,更要有“神韵”。正因为这个东西是字面以外的,是“非以目视”甚至“难以言传”的,才名之以“神”而谓之以“韵”。
这个“不可目视,只可意会”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就是中国美学一讲再讲的言外之意、声外之音、画外之象、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它们表达的也许正是这样一个艺术的辩证法:最抽象的语言往往最能表现微妙的情感,最单纯的形式往往最能蕴含丰富的内容。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所谓“一以当十,以少胜多”,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正是中国艺术棋高一着之所在。同样,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其美学意义也正在于此。也就是说,所谓“希声之音”和“无形之象”,其实就是“神韵”。它当然并非为书法所独有。中国的诗、散文、音乐、绘画,甚至建筑、舞蹈、戏曲、小说,都讲神韵。但因为书法最集中最典型地表现了这一审美特征,因此我们还是象征性地把它称之为“书法神韵”。
从“生命活力”到“线条趣味”,其中有着必然的、逻辑的联系。源于生命本体的生命活力(气),只有通过情感体验(情)才能变成审美对象,藏于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只有通过意象构成(象)才能变成艺术。情感的节律实际上也就是生命的节律,意象的构成实际上也就是情感的构成。生命节律转化为情感节律,就是由隐性的东西转化为显性的东西;而情感节律转化为意象构成,则是由个体性体验转化为社会性传达。在这里,意象构成显然是一个中间环节,把最内在、最深层、最隐秘的东西和最外在、最表层、最直观的东西联系起来了。意象构成的原则是一种理性的原则(法),理性原则和理性态度体现于审美形式和艺术形式,就必然诉诸纯净的、线条化的艺术语言(言),并造就和形成一种中国独有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趣味——线条趣味。线条趣味是抽象的、单纯的、韵味无穷的。为什么线条趣味会有这样的品味?就因为它是对生命活力理性的、意象的和情感的体验和表现啊!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易中天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