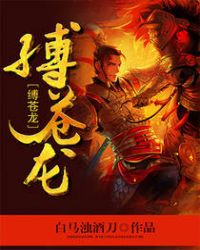“那该如何?哀家总也不能看着我的荣儿受苦!”
老太监呵呵一笑,道:“以太后之力,临江王哪怕就是一个街头小乞儿,想要他荣华富贵也是不难。既然皇上早已经将荣殿下从太子之位废成了临江王,那么自然是不会再想让他卷入皇位争夺的漩涡之中。再说了,太后您老人家不也是不在意荣殿下将来能不能继承皇位的吗?”
“哀家虽然疼爱荣儿,可是荣儿太过于顽劣,确实不合一国之君的风范。哀家只是希望他能一生富贵,一生平安就好了。”
“如此的话,太后的意思其实是和皇上的意思是一样的。您只要不与临江王相认,便是表明了自己在这将来皇位继承上的态度,太子那边自然便是放心的多了。这样即使是太后您待他再好,太子那边想必也不会再为难临江王的了。
将来,太后您再暗中扶持一下临江王,让他再博个功名,封侯拜将,一生的荣华富贵便也是享用不尽了!
而依奴才之见,临江王现如今无论如何也不愿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想必也是在像太子殿下他们表态呢。”
窦漪房深深叹了一口气,道:“亲人不能相认,你说这算是什么事,不过倒也是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说完,窦漪房还是不放心,忽然又问,“这个世界上到底会不会有两个长得极像的人呢?”
“长得极像的或许会有,可是若论长得一模一样的,除了孪生兄弟之外,奴才还从未听说过世界上会有这等奇事。太后还是担心奴才眼花看走眼了吧?”
“可惜哀家瞎了,否则荣儿再顽劣,又岂能瞒过哀家?”
“其实,据奴才打探,皇上那日确实是和殿下滴血认亲过了,殿下的身份想必已经无误才是。只是,太后您要是还不放心的话,或许还可以从其他方面佐证一下。”
“其他方面佐证?”窦漪房想了想,忽然笑逐颜开,惊喜道,“对了,荣儿的屁股上有一个很小的胎记,没有几个人注意到,你将他裤子脱下来,哀家一摸便知!”
“喏!”
刘嵘远远地看着他二人在一边嘀嘀咕咕,却是始终也听不清到底说了什么。正在独自纳闷的时候,却是忽然见得黄公公带着几个小宫女笑意盈盈地走了过来,然后奶声奶气地命令道:“太后有旨,快把临江王的裤子脱了!”
“喏!”
小姑娘们齐齐答应一声,便是一拥而上,在刘嵘手足无措的呼救声,以及李敢卫青他们想笑又不敢笑强憋着的表情之中,将刘嵘下面脱了个精光。
李雨昔好奇地伸头一看,却是忽然又被陆小璇羞红着面颊急急遮住了眼睛,轻斥道:“姑娘家,见不得!”
而此时此刻,窦漪房亦是在一个婢女的搀扶下,急忙走到被众人摁住的刘嵘身边,轻轻蹲下身,拧着眉头,干枯的老手在刘嵘紧绷的菊花周边摸了半天,忽然间便是眉头舒展,笑逐颜开道:“摸到了,摸到了!”
被一个老妇人强行在菊花附近摸了一圈儿又一圈儿,刘嵘痛不欲生,无助的眼神看向李敢、卫青他们,望见的有戏谑有欢心,却是偏偏没有同情。
窦太后口口声声说找到了,却是依旧对刘嵘的屁股爱不释手。刘嵘大喊大叫说自己不是她孙子,老太太开心地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连连点头应和说“不是,不是。”但是那脸上表情却分明是高兴地绽成了一朵老花。
刘嵘欲哭无泪,老太太越是这样,自己也越是百口莫辩了!但愿有一天真相大白之后,这老太太不要怪罪自己诓骗了她才好。
在窦太后的诏令之下,自然是没有人敢于再拦着刘嵘。不光是刘嵘提前出了这大牢,老太太一高兴,当场特赦长安大牢,无论是偷鸡摸狗的,还是杀人越货的,全部一涌而出,吓得长安大街上的大商小贩,人人避而远之,连多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
窦太后虽然没和刘嵘认亲,但是又怎能放心他一个人在宫外漂泊?自然是让宫女太监们一拥而上,将其塞进了马车里面,载着往皇宫而去。
长安城中因为放了流民进来,各个角落里都有人搭棚造锅,等待着朝廷开仓放粮,好生火做饭。长安居民与城外流民争斗纠纷,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其实,在这之前,即使是匈奴人兵临城下的时候,这些关中流民也不过是在长安近郊避乱聚居而已,朝廷一边救济安抚,一边却是严守城门,绝对不允许这么多的流民涌进长安,坏了城中正常的生活秩序不说,倘若有几个匈奴细作混杂其中钻进来,也是一个不小的麻烦。但是这一回,在长安城内外守军换防时,趁着大开城门的这一眨眼工夫,早早候着的流民便是一拥而上,近十万人推推搡搡,城门守军一时没了主意,又没有得到上边武力驱逐的命令,这才陡然间失了秩序,放进了近十万流民。
朝廷大为震惊,但是事已至此,在撤了几个城门守将之后,便也是没了办法。
刘嵘坐在马车里穿过长安大街时,远远看着大将军周亚夫正亲自带领人马驱逐流民,足可见问题之严峻。可是长安城外有匈奴人追杀,哪有人愿意走?士兵们见流民们拖家带口,无衣无粮,都是乡里乡亲的,心中也甚是同情,驱逐时也并不卖力,一路上跑跑丢丢,几万人赶到城门时便是只剩下寥寥几千人,再回头一看,大街小巷又尽是挤满了流民百姓。
李敢跟在刘嵘的车辇旁边,看着被士兵们驱逐的乱跑一通的流民们,慨然叹道:“唉,朝廷也真是的,这么多流民,没吃没喝的,往哪里赶呀?长安城这么大,就让他们随便找个空地暂时安置下来,又有什么关系呢?”
卫青白了他一眼,嘲讽道:“我说李敢,你顶着个脑袋莫非就是为了看起来显得高些吗?你也不用脑袋想一想,这十余万流民,不多说,其中哪怕只是掺杂了三五千匈奴人,等到天一黑,他们在暗地里到处杀人放火,把这长安城一搅乱,军臣大军再全力攻城,到时候里应外合,这长安城可就危险了!”
刘嵘闻言也是把头从马车帘子里伸出来,赞同道:“卫青说的不错啊,得赶紧想个办法把这些流民带到城外才行,这掺杂其中的匈奴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万一到时候再偷偷袭上城楼,打开了城门,那军臣大军一涌而进,不过一夜,长安城便尽是一片瓦砾了!”
“既然如此,那就调兵全部往外赶,谁不走就是匈奴人奸细,全都一剑杀了!我敢保证,不用半个时辰,这长安城就是一个流民也没有了!”
“杀你个大头鬼!”刘嵘想伸手揍那因为提出了这么一个高效可行的方案而洋洋得意的李敢,无奈他离得太远,揍了几个空手,一怒之下抄起自己的一只鞋便是朝他脑袋上砸去。臭鞋砸到李敢榆木般的脑袋上而后又弹向一边,被几个流民家顽皮的孩子一脚又当皮球似的踢了几丈远。
“快给我捡回来!”刘嵘大喝一声,李敢又连忙屁颠屁颠地冲过去,和那一帮毛头小孩子撕扯在一块儿。
“匈奴人要是混进来的话,定然会通过各种手段蛊惑流民,竭尽全力不让他们出城以作为自己在城中的掩护。所以说如果不加分辨地滥杀的话,绝对是不可行的。”
“你说的对,卫青。”刘嵘点了点头,继而又是长吁了一口气,为了长安城的安全,朝廷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些流民在长安城过夜。倘若黄昏之前还驱逐不完,想必也只能使用极端手法了!刘嵘为这些流民感到担心,却也惦记着长安城防的安全,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两全其美的主意,真是左右为难。
正当刘嵘为此唉声叹气的时候,窦太后的銮驾却是忽然停了下来,刘嵘好奇往前一看,只见一个少年约莫十七八岁,虽然衣着看起来与其他人并无多大差异,但是做工精致,协调优美,整个人看起来仪表堂堂,气度不凡,虽然年轻,但仍旧给人一种沉稳如山,深邃如渊的感觉。
这年轻人此时正躬身作礼,迎于窦太后銮驾之前。
“不知太后驾到,不肖孙未能远迎,还请太后恕罪!”
“哦,是太子啊,哀家只是路过,也并不知太子在这里,算不上罪过。只是今天既然是遇见,有一人,哀家还是替你引见一下吧。”
“太后……”黄公公刚想上前劝阻,却是听得窦太后喝道,“你不要多言,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让荣儿过来,与他现如今的太子兄弟照会一下。”
“喏。”
黄公公唯唯而退,不过一会儿,就是将只穿着一只臭鞋,却将另一只臭脚露于外边的,比起周遭流民还有不堪的刘嵘给带了过来。
李敢捧着一只臭鞋跑过来,脸因为憋气而涨得通红,想上前却害怕冲撞了太后的銮驾又不敢上前,一时间进退维谷,说实话,他实在是太想将这只臭鞋还给刘嵘了! 缚苍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