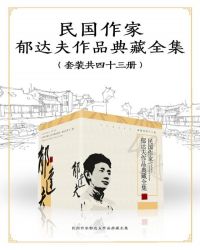下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民国作家郁达夫作品典藏全集(套装共四十三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下
寒空里刮了几日北风,本来是荒凉的扬州城外,又很急速的变了一副面相。黄沙弥漫的山野之间,连太阳晒着的时候都不能使人看出一点带生气的东西来。早晨从山脚下走过向城里运搬产物去的骡儿项下的那些破碎的铁铃,又塔兰塔兰地响得异常的凄寂,听起来真仿佛是在大漠穷荒,一个人无聊赖地伏卧在穹庐帐底,在度谪居的岁月似的。尤其是当灯火青荧的晚上,在睡不着的中间,倚枕静听着北风吹动寺檐的时候,我的喜欢热闹的心,总要渴念着大都会之夜的快乐不已。我对这一时已同入葬在古墓堆里似的平静的生活,又生起厌倦之心来了。正在这一个时候,我又接到了一封从故乡寄来的回信。
信上说得很简单,大旨是在告诉我这一回分家的结果。我的女人和小孩,已搬上坟庄去住了,田地分到了一点,此外就是一笔现款,系由这一次的出卖市房所得的,每房各分得了八百元。这八百元款现在还存在城里的聚康庄内,问我要不要用。母亲和二房同住,仍在河口村的老屋里住着。末了更告诉我说,若在外边没有事情,回家去一趟看看老母也是要紧的,她老人家究竟年纪老了,近来时常在患病。
接到了这一封信,我不待第二次的思索,就将山寺里的生活作了一个结束。第二天早晨一早,就辞别了方丈,走下山来。从福运门外搭汽车赶到江边,还是中午的时候,过江来吃了一点点心,坐快车到上海北站,正是满街灯火,夜市方酣的黄昏八九点之交。我雇了一乘汽车,当夜就上各处去访问了几位直到现在还对我保持着友谊的朋友,告诉他们以这几个月的寂寥的生活,并且告诉他们以再想上上海附近来居住的意思。朋友中间的一位,就为我介绍了一间在虬桥路附近的乡下的小屋,说这本来是他的一位有钱的亲戚,造起来作养病之所的。但等这小屋造好,病人已经入了病院,不久便死去了。他们家里的人到现在还在相信这小屋的不利,所以没有人去居住。假若我不嫌寂寞,那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搬进去住的。我听了他的说明,就一心决定了去住这一间不利的小屋,因而告诉他在这两三天内,想回故乡去看看老母,等看了老母回来马上就打算搬入这一间乡下的闲房去住,请他在这中间,就将一切的交涉为我代办办好。此外又谈了许多不关紧要的闲天,并上两三家舞场去看了一回热闹,到了后半夜才和他们分了手,在北站的一家旅馆内去借了一宵宿。
两天之后,我又在回故乡去的途上了。可是奇怪得很,这一回的回乡,胸中一点儿感想也没有。连在往年当回乡去的途中老要感到的那一种“我是落魄了回来了”的感伤之情都起不起来。
当午前十一点的时候,船依旧同平日一样似的在河口村靠了岸。我一个人也飘然从有太阳晒着的野道上,走回到那间朝南开着大门的老屋里去。因为是将近中午的缘故,路上也很少有认识的人遇见。我举起了很轻的脚步,嘴里还尖着嘴唇在吹着口笛,舒徐缓慢,同刚离开家里上近村去了一次回来的人似的在走回家去。走到围在房屋外围的竹篱笆前,一切景象,还都同十几年前的样子一样。庭前的几棵大树,屋后的一排修竹,黑而且广的那一圈风火围墙,大门上的那一块南极呈祥的青石门楣,都还同十几年前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分别。直到我走尽了外圈隙地,走进了大门之后,我的脚步便不知不觉地停住了。大厅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本来是挂在厅前四壁的那些字画对联屏条之类,都不知上哪里去了。从前在厅上摆设着的许多红木器具,两扇高大的大理石围屏,以及锡制的烛台挂灯之类,都也失了踪影,连天井角里的两只金鱼大缸都不知去向了。空空的五开间的这一间厅屋,只剩了几根大柱和一堆一眼看将起来原看不大清爽的板凳小木箱之类的东西堆在西首上面的厅角落里。大门口,天井里,同正厅的檐下原有太阳光晒在那里的,但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气突然间侵袭上了我的全身。这一种衰败的样子,这一幅没落的景象,实在太使我惊异了。我呆立了一阵,从厅后还是没有什么人出来,再举起眼睛来看了看四周,我真想背转身子就举起脚步来跑走了。但当我的视线再落到西首厅角落里的时候,一个红木制的同小柜似的匣子背形,却从乱杂的一堆粗木器的中间吸住了我的注意,从这匣子的朝里一面的面上波形镶在那里的装饰看起来,一望就可以断定它是从前系挂钉在这厅堂后楼上的那个精致的祖宗堂无疑。我还记得少年的时候,从小学校放假回来,如何的爱偷走上后楼去看这雕刻得很精致的祖宗堂过。我更想起当时又如何的想把这小小的祖宗堂拿下来占为己有,想将我所爱的几个陶器的福禄寿星人物供到里头去过。现在看见了这祖宗堂的被乱杂堆置在这一个地方,我的想把它占为已有的心思一时又起来了,不过感到的感觉和年少的时候却有点不同。那时候只觉得它是好玩得很,不过想把它拿来作一个上等的玩具,这时候我心里感到的感觉却简单地说不出来,总觉得这样的被乱堆在那里还是让我拿了去的好。
我一个人呆立在那里看看想想,不知立了多少时候,忽而听见背后有跑得很快的脚步声响了。回转头来一看,我又吃了一惊。两年多不见的侄儿阿发,竟穿上了小操衣,拿着了小书包从小学里放学回来了。他见了我,一时也同惊极了的一样,忽而站住了脚,张大了两眼和那张小嘴,对我呆呆注视了一会。等我笑着叫他“阿发,你娘哩!”的时候,他才作了笑脸,跳近了我的身边叫我说:
“五叔,五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娘在厨下烧饭罢?爸爸和哥哥等都上外婆家去了。”
我抚着他的头,和他一道想走进厨下去的中间,忽儿听见东厢房楼板上童童的一声,仿佛是有一块大石倒下在楼板上的样子。我举起头来向有声响的地方一看,正想问他的时候,他却轻轻地笑着告诉我说:
“娜娜(祖母)在叫人哩!因为我们在厨下的时候多,听不出她的叫声,所以把那个大秤锤给了她,教她要叫人的时候,就那么的从床上把铁锤推下来的。”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东北角的厅里果然二嫂嫂出来了。突然看见了我和阿发,她也似乎吃了一惊,就大声笑着说:
“啊,小叔,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五婶正教长生送了一篮冬笋来,他还在厨下坐着哩,你还没有回到庄屋里去过么?”
“是刚刚从轮船上来的。娘哩?还睡在那里么?”
“这一向又睡了好几天了,你却先上厨下去洗个面喝口茶罢,我上一上去就来。”
说着她就走上了东夹弄里的扶梯,我就和阿发一道走进到了厨下。
长生背朝着外面,驼了背坐在灶前头那张竹榻上吸烟,听见了我和阿发的脚步声,他就立了起来。看见了我,猛然间他也惊呆住了。
“噢,和和……,五五……,你你……”
可怜急得他叫也叫不出来,我和阿发,看了他那一种惊惶着急的样子,不觉都哈哈哈哈的笑起来了,原来我的乳名叫作和尚,小的时候,他原是和尚和尚的叫我叫惯的,现在因为长年的不见,并且我也长大了,所以他看见我的时候,老不知道叫我作什么的好。我笑了一阵,他的惊惶的样子也安定了下去,阿发也笑着跑到灶下去弄火去了,我才开始问他:
“你仍和我们住在一道么?庄屋里的情形怎么样?”
他摇了摇头,作了一副很认真的样子,对我呆视着轻轻的问说:
“和和……五,五先生,我那信你接到了么?你……你的来信,我也听见说了,我很多谢你,可是我那女儿,也在叫我去同她们住。”
说到这里,二嫂嫂已从前面走了进来,我就把长生撇下,举起眼睛来看她。我在她的微笑的脸上,却发见了一道隐伏在眉间的忧意。
“老人家的脾气,近来真越变得古怪了。”
她微笑摇摇头说。
“娘怎么样,病总不十分厉害吧?”
我问她。
“病倒没有什么,可是她那种脾气,长生吓,你总也知道的罢?”
说着她就转向了长生,仿佛是在征他的同意。我这回跑了千把里路,目的是想来看看这一位老母的病状的,经嫂嫂那么的一说,心里倒也想起了从前我每次回来,她老人家每次总要和我意见冲突,弄得我不得不懊恼而走的种种事情,一瞬间我却失悔了,深悔我这一回的飘然又回到了故乡来。但再回头一想,觉得她老人家究竟是年纪大了,象这样在外面流离的我,如此的更和她能够见得几回的面。所以一挺起身,我就想跑出前厅上楼去看看她的病容。但走到了厅门边上,嫂嫂又叫我回去说:
“小叔,你是明白的人,她老人家脾气向来是不好的,你现在还是不去看她罢,等吃了饭后,她高兴一点的时候再去不迟。”
被嫂嫂这么的一阻,我却更想急急乎去见见她老的面了,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出前厅,跑上了厢楼。
厢楼上的窗门似乎因为风多都关闭在那里,所以房里面光线异常的不足。我上楼之后,就开口亲亲热热地叫了一声“娘!”但好久没有回音。等我的目光习惯了暗处的光线,举目向床上看去的时候,我才看出了床上的帐子系有半边钩挂起在那里的,我们的那位老母却背朝着了外床,打侧睡在棉被窝里。看了她半天的没有回音,我以为她又睡着在那里了,所以不敢再去惊动,就默默的在床前站立了好一会。看看她是声息也没有,一时似乎是不会醒转来的样子,我就打算轻轻走下楼来了,但刚一举脚,床上我以为是睡着的她却忽而发了粗暴的喉音说:
“你也晓得回来的么?”
我惊异极了,正好象是临头被泼了一身冷水。
“你回来是想来分几个钱去用用的罢?我的儿女要都是象你一样,那我怕要死了烂在床上也没有人来收拾哩!哼,你们真能干,你那媳妇儿有她的毒计,你又有你的方法。今天我是还没有死哩,你又想来拆了我的老骨头去当柴烧了么?我的这一点金器,可是轮不到你们俩的,老实先同你们说了罢?”
我听了她的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毒骂,真的知觉也都失去,弄得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凝结住了。身上发了抖,上腭骨与下腭骨中间格格地发出了一种互击的声音。眼睛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了,黑暗里只瞥见有许多金星火花,在眼前迸发飞转,耳朵里也只是嗡嗡地在作怪鸣;我这样惊呆住兀立了不晓得有多少时候,忽而听见嫂嫂的声音在耳朵边上叫说:
“小叔,小叔,你上下面去吃饭去罢!娘也要喝酒了啊。”
我昏得连出去的路都辨不清了,所以在黑暗里竟跌翻了几张小凳才走出了厢楼的房门,听见我跌翻了凳子的声音之后,床里面又叫出来说:
“这儿的饭是不准你来吃的,这儿是老二的屋里,不是老屋了。”
我一跑下楼梯,走到了厅屋的中间,看见长生还抬起了头驼着了背很担忧似的在向厢房楼上看着。一见了他的这一副样子,我的知觉感情就都恢复了,一时勉强忍住得好久的眼泪,竟扑漱漱滚下了好几颗来。我头也不回顾一眼,就跑出了厅门,跑上了门前的隙地,想仍复跑上船埠头去等下午那一班向杭州出发的船去。但走上村道的时候,长生却含着了泪声,在后面叫我说:
“和和……和……,五先生,你等一等……”
我听了他的叫声,就也不知不觉的放慢了脚步,等他走近了我的背后,只差一两步路的时候,我就一边走着一边强压住了自己啜泣的鼻音对他说:
“长生,你回去罢,庄屋里我是不去了。我今晚上还要上上海去。”
在说话的中间他却已经追上了我的身边,用了他的那只大手,向我肩上一拉,他又呐呐的说:
“你,你去吃了饭去。他们的饭不吃,你可以上我女儿那里去吃的。等吃了饭我就送你上船好了。”
我听了他这一番话,心里更是难堪了,便举起袖子来擦了一擦眼泪,一句话也不说,由他拉着,跟他转了一个方向,和他走上了他女儿的家中。
等中饭吃好,手脸洗过,吸了一枝烟后,我的气也平了,感情也回复了常态。因为吃饭的时候,他告诉了我许多分家当时的又可气又可笑的话,我才想起了刚才在厅上看见的那个祖宗神堂。我问了他些关于北乡庄屋里的事情,又问他可不可以抽出两三日工夫来,和我同上上海去一趟。他起初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后来等我想把那个大家不要的祖宗堂搬去的话说出之后,他就跳起来说:
“那当然可以,我当然可以替你背了上上海去的。”
等他先上老屋去将那个神堂搬了过来,看看搭船的时间也快到了,我们就托他女儿先上药店里去带了一个口信给北乡的庄屋,说明我们两人的将上上海。
那一天晚上的沪杭夜车到北站的时候,我和他两个孤伶仃的清影,直被挤到了最后才走出铁栅门来,因为他背上背着那红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仿佛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挤了,致这神堂要受一点委屈。
第二天的午前,我先在上海将本来是寄存在各处的行李铺盖书架桌椅等件搬了一搬拢来,此外又买了许多食用的物品及零碎杂件等包作了一大包。午后才去找着了那位替我介绍的朋友,一同迁入了虬桥路附近的那间小屋。
等洗扫干净,什器等件摆置停当之后,匆促的冬日,已经低近了树梢,小屋周围的草原及树林中间,早已有渺茫的夜雾濛濛在扩张开来了。这时候我那朋友,早已回去了上海,虽然是很小,但也有三小间宽的这一间野屋里只剩了我和长生两个。我因为他在午后忙得也够了,所以叫他且在檐下的藤椅子上躺息一下吸几口烟,我自己就点上了洋烛,点上了煤油炉子,到后面的一间灶屋里去准备夜饭。
等我把一罐牛肉和一罐芦笋热好,正在取刀切开面包来的时候,从黑暗的那间朝南的起坐室里却乌乌的传了一阵啜泣的声音过来。我拿了洋烛及面包等类,走进到这间起坐室的时候,哪里知道我满以为躺坐在檐下藤椅上吸烟的长生,竟跪坐在那祖宗神堂的面前地上,两手抱着头尽在那里一边哭一边噜噜苏苏动着嘴似在祷告。我看了这一种单纯的迷信,心里竟也为他所打动了,在旁边呆看了一忽,把洋烛和面包之类向桌上一摆,我就走近了他的身边伏下去扶他起来叫他说:
“长生,起来吃饭罢!”
他听了我这一声叫,似乎更觉得悲伤了,就放大了声音高哭了起来;我坐倒在椅上,慢慢的慰抚了半天,他才从地上立起,与我相对坐着,一边哭一边还继续的说:
“和尚,我实在对老东家不起。我……我我实在对老东家不起。……要你……要你这样的去烧饭给我吃。……你那几位兄嫂,……他们……他们真是黑心。……田地……田地山场他们都夺的夺争的争抢了去了……只……只剩了一个坟庄……和这一个神堂给你们。……我……我一想起老东家在日,你们哥儿几个有的是穿有的是吃……住的是……是那间大厅堂,……到现在你……你只一个人住上这间小……小的草屋里来,……还要……还要自己去烧饭……我……真对老东家不起……”
对这些断续的苦语,我一边在捏着面包含在嘴里,一边就也解释给他听说:
“住这样的草舍也并不算坏,自己烧饭也是很有趣的。这几年也是我自己运气不好,找不到一定的事情,所以弄得大家都苦。若时运好一点起来,那一切马上就可以变过的。兄嫂们也怪他们不得,他们孩子又多,现在时势也真艰难。并且我一个人在外面用钱也的确用了太多了。”
说着我又记起了日间买来的那瓶威士忌酒,就开了瓶塞劝他喝了一杯,教他好振振精神,暖和一点。
这一餐主仆二人的最初的晚餐,整整吃了有四五个钟头。我在这中间把罐头一回一回的热了好几次。直到两人喝了各有些微醉,话到伤心,又相对哭了一阵之后,方才罢休。
第二天天末又起了寒风,我们睡到八点多钟起来,屋前屋后还满映着浓霜;洗完了手脸,煮了两大杯咖啡喝后,长生说要回去了,我就从箱子里取出了一件已经破旧的黑呢斗篷来,教他披,要他穿上了回去。他起初还一定不肯穿着,后来直等我自己也拿了一件大氅来穿上之后,他才将那件旧斗篷搭上了肩头。
关好了门窗,和他两人走出来,走上了虬桥路的大道,同刀也似的北风吹得更猛了,长生到这里才把斗篷扯开,包紧了他那已经是衰老得不堪的身体。搭公共汽车到了徐家汇车站,正好去杭州的快车也就快到了。我替他买好了车票,送他上月台之后,他就催我快点回到那小屋里去,免得有盗贼之类的坏东西破屋进去偷窃。我和他说了许多琐碎的话后,回身就想走了,他又跑近了前来,将我那件大氅的皮领扯起,前后替我围得好好,勉强装成了一脸苦笑对我说:
“你快回去罢!”
我走开了几步,将出站台的时候,又回过来看了一眼,看见他还是身体朝着了我俯头在擦眼睛。我迟疑了一会,忽儿想起了衣服袋里还搁在那里的他给我的那封厚信,就又跑了过去,将信从袋里摸了出来,把用黄书纸包好的那张五圆纸币递给他说:
“长生,这是你寄给我的。现在你总也晓得,我并不缺少钱用,你带了回去罢!”
他将搁在眼睛上的那只手放了下来,推住了我捏着纸币的那只右手,呐呐的说:
“我,我……昨天你给我的我还有在这儿哪!”
抬头向他脸上瞥了一眼,我看见有两行泪迹在他那黄黑的鼻坳里放光,并且嘴角上他的那两簇有珠滴的黄胡子也微微地在寒风里颤动。我忍耐不住了,喉咙头塞起了一块火热的东西来,眼睛里也突然感到了一阵酸热。将那包厚纸包向他的手里一掷,轻轻推了他一下,我一侧转身就放开大步急走出了车站。“长生,请你自己珍重!”我一边闭上了眼睛在那里急走,一边在心里却在默默的祝祷他的康健。
一九二九年一月作
原载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大众文艺》第四期 民国作家郁达夫作品典藏全集(套装共四十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