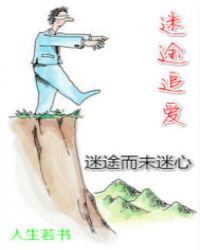27 愚蠢行为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从华尔街到硅谷(套装共9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27 愚蠢行为
奥马哈,新贝德福德 1964—1966年
霍华德去世6个星期以后,沃伦做出了让人出乎意料的举动。这次绝非钱那么简单。他认为既然美国运通公司做错了,就应该承认并且赔偿损失,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已经提议给银行6000万美元以解决问题,并且表示公司在道义上负有责任。可是一部分股东提起诉讼,认为美国运通公司应该保护自己而不是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巴菲特提出,他代表管理层的想法去做证,以解决目前的问题,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
我们觉得,三四年后这个问题也许会提升公司的形象。因为它建立了远超过一般商业企业的金融正直和责任标准。
但是,美国运通公司并不愿意为了成为榜样而出这笔钱,它仅仅想躲避败诉的风险,因为那会给公司的股票蒙上阴影。它的客户们也毫不在意,“豆油丑闻”并没有在他们心中留下足够的印象。
在给美国运通公司总裁霍华德·克拉克的信中,巴菲特指出了公司面临的两条路。他还在信中表示,美国运通公司应该负起责任并且赔偿银行6000万美元,“比起否认其附属机构的行为,这样做要重要得多”。他将这6000万美元描述成就像在邮寄中弄丢的红利支票,从长期看是无关紧要的。
苏珊曾经不小心将红利支票扔进了炉子,可她一直没有勇气将这个意外告诉丈夫。现在,如果她知道丈夫竟然如此绅士地处理邮寄中搞丢的6000万美元红利支票,一定会感到非常震惊。那么,现在巴菲特为什么会对美国运通公司是否拥有“远超过一般商业企业的金融正直和责任标准”感兴趣呢?正直的名声对一个企业更重要的想法从何而来?为什么沃伦想去做证?他已经有和他父亲一样的诚实,现在看起来他还继承了霍华德对原则问题大发评论的喜好。
巴菲特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所投资的公司的管理。但是,在过去他并没有试图将他的投资公司转化成教堂,在募捐的时候还可以讲道。而现在,他没有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霍华德·克拉克的门口,游说后者要保持坚定的立场,尽管已经有部分股东提起了诉讼。
我有个习惯,喜欢顺便走访别人,和不同的人谈话。有一次,霍华德对我说,如果我能再多留意一下组织结构,那就更好了……他说这些是很善意的。 注释标题 ‘I'm not a hundred percent sure of that. I’ve been told that by other people,so it's hard to remember. But I'm pretty sure it was Howard Clark.’
似乎是为了确认巴菲特的感觉——道德上的诚实、正直也有金融价值——美国运通公司在付清了和解费用,股价一度下滑到不足35美元后,又上升到超过49美元。到1964年11月,巴菲特的合伙公司拥有超过430万美元的美国运通公司股票。它还在另外两家公司押了大赌注:得克萨斯海湾制造公司460万美元,纯石油公司350万美元,这两家都是“烟蒂”。这三项投资已经占了整个投资组合的一半多。而到1965年,仅对美国运通公司的投资就占了1/3。
合伙公司1962年成立的时候,只有720万美元的资金。巴菲特一点儿也不害怕集中加仓,他一直不停地买进美国运通公司的股票,到1966年已经在该股票上花了1300万美元。他觉得合伙人应该了解一个新的“基本准则”——“我们远远没有像大多数投资机构那样,进行多样化投资。也许我们会将高达40%的资产净值投资于单一股票,而这是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即我们的事实和推理具有极大可能的正确性,并且任何大幅改变投资潜在价值的可能性很小”。
以他的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的世界观来看,巴菲特的冒险之旅走得更远。格雷厄姆支持的讲究实际的定量分析方法是速度裁判员的世界,是那些仅做纯数据工作、弯腰捡“烟蒂”的驼背者的世界。巴菲特每天早上过来工作,浏览《穆迪手册》或者标准普尔公司的周评,以满手的数字为基础寻找便宜的股票,然后打电话给特雷迪–布朗–纳普公司的汤姆·纳普下单买入,休市了就回家,晚上睡个好觉。正如巴菲特谈起这些他喜欢的方法时所说的,“更多的有把握的钱是由明显的定量决定赚来的”。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数据统计出的低价股的数字会一下收缩至零,而且因为那些“烟蒂”一般都是些小公司,如果拿一大笔钱来投资,这种方法就不奏效了。
虽然还在用那种方法继续工作,但在美国运通公司一事上,巴菲特已经拥有了后来他称之为“高度可能性的洞察力”,这打乱了本杰明·格雷厄姆的核心思想。和其他公司不一样,美国运通公司的价值并不是来自现金、设备、房地产或者其他可以计算的资产,如果有必要清算,它所拥有的不过是对客户的信誉。巴菲特把合伙人的钱——艾丽斯的遗产,汤普森博士的积蓄,安妮·戈特沙尔特和凯瑟琳·埃伯菲尔德的钱,安琪夫妇一辈子的积蓄,以及埃斯蒂·格雷厄姆的钱——全部押在这个信誉赌注上。这是当查理·芒格说起这桩“伟大的生意”时,一直不停提到的竞争优势。而这正是菲利普·费希尔提到的更弱智的分类方法,它用的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对。
巴菲特在后来给合伙人的信中写道,购买“正确的公司”(有合适的前景、天生的行业条件、管理等)意味着“价格会一路走好……这也是能让收银机真正唱歌的原因。但是,这并不经常发生,就和洞察力一样。当然,定量分析不需要洞察力——数字会如一根棒球棒一样狠狠地击中你的头。因此,大钱往往是那些能够做出正确的定性决策的投资人赚到的”。
对定性分析方法的新的强调是在1965年底,巴菲特向合伙人宣布取得巨大成果时获得了回报。在年度报告中,他比较了这累累硕果和早先舆论发布的他会以一年10%的优势击败道琼斯指数的预期——谈到这炫目的业绩时,巴菲特表示,“很自然,没有作者喜欢被这样的错误公开羞辱,它不太可能会被重复”。尽管说了这些讽刺的话,但他已经开始了一个避免合伙人高预期的传统。随着杰出战绩的记录越来越长,巴菲特的信开始只着重关注衡量成功与失败。他频繁使用“有罪”“难堪”“失望”或者“过失”这样的字眼,包括用来形容他所谓的错误——他一直执着于不让任何人失望。当阅读者开始识别出这种模式时,一些人认为他在操纵他们,而另外一些人责怪他假装谦虚。几乎没有人能真正了解,在这种不安全的奔跑中他的感觉有多深。
在霍华德去世的第二年,沃伦开始考虑用某种方式来纪念他,比如捐助一所大学,但是他似乎一直没有找到那个完美的手段。之前,他和苏珊已经成立了巴菲特基金会,对教育事业进行了小规模的捐助。但这不是他心里面想为父亲做的。沃伦并不想成为一个慈善家,是苏珊喜欢分配资金,并且也是她在掌管基金会。相反,巴菲特毫不松懈地紧张工作。在美国运通公司这件事上打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全垒打后,1965年4月,巴菲特从奥马哈国民银行的信贷部挖来了约翰·哈丁,让他专门负责公司的行政管理。哈丁接手工作时,巴菲特如此警告他:“我不知道是否有必要永远做下去,但如果我不干了,你也将会失业。”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一点儿要不干的迹象。哈丁曾希望学会投资,不过这份野心很快就破灭了。“我曾有独立处理投资事宜的想法,但在看到沃伦是多么优秀时,这种想法就消失了。”他说。取而代之的是,哈丁直接将大部分钱投入了合伙公司。
除了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美国运通公司的股票像铲东西一样铲进合伙公司,沃伦正在寻找需要他加以协调的更大的交易。大的“烟蒂”和“定性的”分类裁判交易,与在家里通过浏览浴袍里的《穆迪手册》找到的完全不同。他的下一个目标,另一个“烟蒂”,远离奥马哈。
巴菲特网络里的每一个格雷厄姆信徒都在寻找新的主意,丹尼尔·科文带来了位于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一家纺织品制造公司,这家公司正以低于资产价值的折扣待售。巴菲特的想法是买下这家公司,清算后分成一块一块出售,最后关闭。这家公司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这时,沃伦已经从失去父亲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满脑子都是这个新念头。
巴菲特开始围着这家公司打转,并且观察它。而且,他开始从容地收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这一次,不论好坏,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具有马萨诸塞州个性的人管理的公司。
西伯里·斯坦顿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很不情愿地关闭了十几个工厂,一个接着一个。剩余的工厂则沿着新英格兰日渐没落的城镇的河边蔓延,就像一座座长期无人供奉的红砖寺院,空空如也。
这已经是第二个斯坦顿掌管公司了,他被一种宿命感笼罩。站在新贝德福德满是岩石的海岸边,就像克努特国王一样,命令具有毁坏能力的潮汐赶快撤退。和克努特不一样的是,他事实上想过潮汐会听命于他。美国哥特式的新英格兰版本在生活中上演,西伯里以他高大的身材冷冷地往下凝视着来访者。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能设法找到他,他会这么干。他隐蔽在一个偏僻的、远离织布机喧嚣、位于顶层阁楼的办公室里,到那儿需要走过一条又窄又长的楼梯,门口还有他秘书的秘书把守。
新贝德福德是这家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曾经像新英格兰王冠上的钻石那样闪闪发光。曾几何时,那些从它的港湾出发去捕杀抹香鲸的渔船使它成为北美洲最富裕的城市。到1854年,每年捕鲸的收入等于1200万美元,这让新贝德福德成为在南北战争之前按照人均收入计算最富裕的城市。斯坦顿的祖父,一个捕鲸船的船长,也是当时掌管这个世界上最恃强凌弱的生意之都的几个家族之一的头领。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抹香鲸越来越稀少,捕鲸船为了寻找弓头鲸不得不一直向北冒险进发,最终抵达北冰洋。1871年的秋天,新贝德福德的很多家庭并没能等回他们的儿子和丈夫。由于当年冬天来得出奇的早,22条船不幸陷在北冰洋的冰里,再也没有回来。于是,新贝德福德再也不复从前,曾经的支柱——捕鲸生意也没能复兴。随着鲸鱼的供应萎缩,对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在减少。1859年,石油从宾夕法尼亚州的土地里汩汩涌出。之后,煤油代替日益稀少的鲸鱼油,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随着维多利亚式生活中经常使用的物品,如妇女穿的紧身衣、蓬蓬裙、精致的阳伞以及马鞭等,从家里的架子上逐渐消失,用于这些物品的有弹性、像梳子一样的鲸鱼须便没有了市场。
1888年,家里做茶叶生意的霍雷肖·哈撒韦和他的会计约瑟夫·诺尔斯组建了一家由多人参与的合伙公司,准备跟着他们眼中的下一个生意潮流干。他们建了两个纺织品厂,艾卡什奈制造公司和哈撒韦制造公司。其中一个合伙人就是臭名昭著的“华尔街女巫”——海蒂·格林,她是家族船运生意的女继承人,在新贝德福德长大。为了办理贷款和投资,她曾驾驶渡船从霍博肯租住的公寓一直到了纽约。她昂首阔步走在曼哈顿下城,裹着旧式的黑色羊驼长袍,披肩在脖子上绕了又绕,还戴着一顶老掉牙的帽子,整个看起来就像是只苍老的蝙蝠。她的打扮如此古怪,并且吝啬得出名,因此甚至有谣言说她用报纸当内衣穿。1916年逝世之前,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
有这样的投资者支持,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了一个又一个,负责将那些从南方来的船只上卸到新贝德福德码头的一摞摞棉包进行梳理、卷轴拉丝、纺织、染色。国会议员威廉·麦金利,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主席,不时会来到这个地区给新的工厂剪彩,他还赞助通过了一个可以在对外贸易中保护纺织工厂的关税条文,因为那时在其他地方,制造纺织品已经相对便宜了。因此,即使在一开始,北方的纺织厂也需要政治的帮助才得以生存。20世纪早期,一项新技术——空调——使工厂得到了革新。空调可以精确控制空气湿度以及其他微粒物质,这样再也没有证据说明,将棉花从劳动力便宜的南方运到寒冷的新英格兰海岸是一件很经济的事情了。诺尔斯的继任者,詹姆斯·斯坦顿眼看着一半竞争者的工厂转移到了南方。留下来的工厂里的工人们不堪被反复地降低工资,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罢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给他们的老板狠狠一击。他的儿子回忆说,詹姆斯·斯坦顿“不太情愿再去花股东的钱购买新设备,因为生意非常糟糕,前景也不确定”。于是,詹姆斯用分红的方式抽出了资本。
到他的儿子、哈佛毕业生——西伯里·斯坦顿1934年接管公司时,这个破旧的哈撒韦工厂每天还能嘎吱嘎吱地织出几匹布,西伯里开始被一种自认为是拯救纺织工厂的英雄的想法占据。他说:“一家拥有最先进的机械、管理高明的纺织公司在新英格兰肯定会有一席之地。”他和他的兄弟奥蒂斯·斯坦顿构思了一个为期5年的现代化计划。他们投资了1000万美元用于安装空调、电梯和头顶上的传送带,改善了照明,还在公司脆弱的红砖大楼里配备了具有未来感的更衣室。工厂从生产棉布转为生产人造丝——穷人的丝绸,在战争期间还生产人造丝降落伞布,这些使他们的生意出现了短暂的兴隆。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廉价的国外劳动力始终能把价格压低到客户们愿意接受的水平。为了竞争,西伯里不得不在他的新工厂里挤压工人们的报酬。但是年复一年,浪潮拍打着他的海岸——更便宜的外国布料,更好的自由竞争,以及南方更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日益威胁着他的工厂。
1954年,卡萝尔飓风14英尺高的风暴巨浪涌入哈撒韦位于海湾街的总部。虽然公司独特的钟塔安然度过了这场风暴,可海水带来的垃圾、各种碎片淹没了大楼里的纺织机和纱布。在这种情况下,反应很明显,哈撒韦应该加入南迁的队伍,而不是重建工厂。可取而代之的是,西伯里将哈撒韦和另外一家工厂——伯克希尔精细纺织公司合并,试图筑起抵抗浪潮的堤岸。
伯克希尔精细纺织公司的产品包罗万象,从最挺的斜纹布到最纯的薄纱、优质的窗帘凸花条纹布、精美的横螺纹衬衫衣料等。伯克希尔的主人马尔科姆·蔡斯坚定地拒绝为现代化投资一个子儿。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莱迪就读哈佛商学院时,曾于1954年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论文,却得到了这么一个令人气馁的结论,失望之余,他卖掉了伯克希尔的股票。
蔡斯很自然地反对西伯里·斯坦顿对现代化的需求,但是新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被斯坦顿的使命感掌控。他简化了公司的生产线,专注于生产人造丝,产量达到全美男装西装衬里的一半。因为斯坦顿掌管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一年要使用将近250亿码的织物,斯坦顿继续“无情的”现代化进程,又砸入了数百万美元。
这一次,他的兄弟奥蒂斯开始怀疑继续留在新贝德福德的可行性,可西伯里认为纺织厂南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拒绝放弃复兴工厂的梦想。
1962年,当丹尼尔·科文就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事与巴菲特接触时,巴菲特已经知道了,就像他知道美国的任何一个规模合适的生意一样。注入公司的资金意味着伯克希尔——根据会计师的核算——价值2200万美元,或者是每股19.46美元。可是,在连续9年的亏损以后,任何人都能以仅仅7.5美元的价格买入股票。巴菲特开始买入了。
西伯里也一直在买伯克希尔的股票,用其他还没有投入工厂的现金每两年进行一次要约收购。巴菲特认为西伯里会继续这种操作,这样他就可以合理安排自己交易的时间,只要股票变便宜了就买入,而价格一旦上升,就又把股票卖回公司。
他和科文着手买入股票。但如果有人知道巴菲特在买哪只股票,就很有可能会推动股价上涨。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巴菲特通过特雷迪–布朗公司的霍华德·布朗购买股票。这家公司是巴菲特最喜欢的经纪商,因为那儿的每个人,尤其是布朗,守口如瓶。这对于巴菲特坚持保密性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特雷迪–布朗公司给巴菲特合伙公司的账户编的代码是BWX。
当巴菲特来到坐落于华尔街52号的这间小小办公室——巧合的是,这和本杰明·格雷厄姆曾经工作的地方同属一幢艺术装饰大楼——时感觉就像进入了一家地板上铺着黑白相间的瓷砖的老式理发店。靠左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坐着公司秘书和办公室经理,右边是交易室,再过去是一个租用的小隔间,水冷却器和衣帽架几乎占了一半的空间——作用类似于某种壁橱——沃尔特·施洛斯就坐在那张磨损的办公桌前经营着合伙公司。通过一成不变地使用格雷厄姆的方法,自离开格雷厄姆–纽曼公司以来,他每年的投资回报超过20%。他用股票交易佣金代替现金支付应该给特雷迪–布朗公司的租金。不过他的交易很少,所以在房租上他占了大便宜。他将其他开销缩减到不能再缩了:订阅《价值线投资调查》,一些纸和笔,地铁代币,就再没有其他的了。
交易室的中心放了一张20英尺长的木头桌子,这还是这家公司在它通往垃圾场的路上捡回来的。桌子表面满是几代学生用铅笔刀刻出来的记号。如果想要在纸上写数字,必须在纸下面垫一张书写板;否则,“托德爱玛丽”这样的字眼就会被嵌入文字里。
在这张被孩子们弄得伤痕累累的桌子的一边,是霍华德·布朗的领地。他和他的合伙人面对着公司的交易员——和所有的交易员一样——他坐在那儿,忐忑不安、焦虑地等待着可以让他交易的电话铃声。紧挨着布朗的桌子旁边的一块空地被用来当作“来访者的桌子”,最便宜的木制文件橱柜沿着墙壁摆放。
纽约没有哪个地方能像特雷迪–布朗“来访者的桌子”一样,让巴菲特觉得宾至如归了。这家公司还涉足套利交易、预测以及“数桩”(正在被收购或者分解的公司)——各种各样,只要他喜欢就行。它还交易如牙买加(皇后)水务公司的为期15年的股票期权——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权利,一旦有预测纽约将接管这家水务公司,股价就会上涨;等预测暂时平静了,股价又会下跌。特雷迪–布朗每次在它们下跌时买入而在上涨时抛售,反复一次又一次。
这家公司还擅长搪塞那些没名气的、被低估的企业管理层,努力挤压出隐藏的价值,和桑伯恩地图公司案例中的做法如出一辙。“我们总是身处诉讼。”一个合伙人表示。它的一切都沾染着过去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气息,和美国运通公司这样的巨大交易没有一点儿相似之处,不过巴菲特喜欢这儿的气氛。汤姆·纳普研究股票,而如果不是在精心策划交易,他会整天密谋一些恶作剧。他征用了一个巨大的储存柜,里面装满了他和巴菲特因失误买下的面值为4美分的蓝鹰邮票和缅因州海岸线的地形图。这堆地形图还在不断地加厚,因为纳普把从股票上赚的钱全部倾注在买缅因州海岸线地形图上去了。那堆蓝色的“老鹰”在慢慢减少,被用于邮寄给巴菲特的一堆粉单上了,每周一次,每次40张邮票,周周如此。
其实,粉单上有关那些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报价,在打印时就已经过时了。巴菲特把这些粉单仅仅当作电话市集的起点,在数不清的经纪人电话里,也许会有一个要用到这个报单来达成交易。通过他的经纪人利用这个系统工作,他可是个行家里手,缺少公开发布的价格帮助减少了竞争。而如果有人愿意给每一个市场参与者打电话,并且无情地压榨他们,那么和那些缺少精力或者懦弱的人相比,他就拥有很大的优势。
布朗会给巴菲特打电话,让他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了5美元一股的某股票的卖盘报价。
“嗯,4.75美元买入。”巴菲特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如钓鱼甩竿一样,这样做是为了测出这个卖家到底有多饥饿。
询问了顾客是否愿意接受这个更低的价格后,布朗将会告知巴菲特这样的回复:“对不起,低于5美元,对方不接受。”
“不予考虑。”巴菲特将会回答。
几天以后,布朗又会再次致电巴菲特:“4.75美元卖出价,已经搞定,那我们就以4.75美元买入。”
“对不起,”巴菲特这回将立刻回答,“4.5美元买入。”
布朗又要回致卖方,而对方肯定会表示,“怎么回事?4.75美元怎么了?”
“我们仅仅是传递信息,4.5美元买入。”
电话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直到一周以后,布朗又来了,“搞定,4.5美元买入”。
“对不起,”巴菲特将会回答,同时又压了0.125美元,“4.375美元买入。”
就这样,他以巴菲特特有的方式不断压价。他很少,几乎不会因为非常想得到一只股票而提高报价。
巴菲特第一次下单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是在1962年12月12日,2000股,每股7.5美元,另付经纪人佣金20美元。他告诉特雷迪–布朗要一直买。
科文从董事会成员斯坦利·鲁宾那儿获得关于伯克希尔的信息,他是公司顶级的销售人员,同时正好是另一位董事会成员奥蒂斯·斯坦顿的朋友。奥蒂斯·斯坦顿现在觉得他的兄弟遥不可及。躲在秘书们把守的象牙塔里,随着他崇高的愿景和现实之间的碰撞越来越剧烈,西伯里喝的酒也越来越多。现在,奥蒂斯和西伯里极其不和。他认为西伯里应该接受罢工,而不是满足工人对更高工资的需求。他也不赞成他的兄弟就继承人做出的选择,西伯里的儿子杰克,是一个非常令人愉悦的年轻人,可是不适合这个工作——根据奥蒂斯的判断。而奥蒂斯对于西伯里的继任者有自己的想法——肯·蔡斯,现任公司的副总裁。
似乎收购的威胁即将到来,西伯里·斯坦顿立刻对巴菲特的购买做出反应,进行了几次要约收购。而这正是巴菲特所希望的,因为他的购买是建立在最终西伯里会收购股票的预期之上的。他要伯克希尔的股票不是为了保留,而是为了出售。虽然如此,但每一项交易里既会有买家,也会有卖家。到目前为止,西伯里·斯坦顿已经抵挡住便宜的外国布料的挤压和卡萝尔飓风的袭击。除了西伯里会变成巴菲特那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巴菲特会变成西伯里那样。
最终,沃伦决定自己驱车前往新贝德福德去看一看。这是唯一一次,他不是顺便走访。一般由非常忠于西伯里的塔波尔小姐来决定,哪些来访者可以通过一道道玻璃门,沿着狭窄的楼梯,来到位于顶楼的西伯里的办公室。当她严肃地带领沃伦走进西伯里那经过豪华装修、有舞场那么大、镶嵌了木头的藏身之处时,沃伦看见西伯里那张桌子附近根本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很显然,这个男人通常让人们站在他的面前,而他就坐在那张桌子后面,指挥他们干这干那。
两个男人在角落里一张令人不舒服的长方形会议桌旁坐下。巴菲特询问斯坦顿,下一次要约收购打算怎么做。斯坦顿透过架在鼻子上的金丝边眼镜看着他。
他相当热诚。接着他说:“我们也许会在这些天进行一次要约收购,你打算以什么价格出售呢,巴菲特先生?”或者类似这样的话。那时股票价格为9美元或者10美元。
我说如果他们要约收购,我会以11.5美元出售。他又说:“好,那你能保证如果我们收购,你会卖给我们吗?”
我回答:“如果很快,而不是20年以后,我会的。”
我愣住了。我感觉到不可能再买到股票了,因为我太了解他将会干些什么了。于是我回家了,没过多久,我就收到了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下属的老殖民信托公司的来信,信中的要约收购价格为11.375美元。这比之前达成一致的价钱要少12.5美分。
巴菲特火冒三丈。“这真的把我惹火了。要知道,这个家伙正在企图骗走1/8个点,而事实上那时他已经和我握手表示成交了。”
巴菲特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而斯坦顿却企图欺骗他。巴菲特派科文去新贝德福德规劝斯坦顿不要背信弃义。可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斯坦顿否认他和巴菲特达成过什么交易。他告诉科文那是他的公司,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真是个错误。因为这次欺骗,西伯里·斯坦顿将自作自受。巴菲特决定——不再出售股票——相反,现在他要买这家公司。
他发誓他将得到伯克希尔,他会把它整个买过来。他要拥有它的库存、纺织机、纺锤。这是一家垂败的、没有希望的企业,实在不值得这样做。可是它很便宜,并且他很想得到它。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斯坦顿拥有它,而巴菲特和其他的股东更值得拥有它。在巴菲特的决定中,他忽略了在丹普斯特得到的教训——只保留了一个。而这一个恰恰是他应该忽略的。
巴菲特派出侦察员去寻找更多集中持有的股票。科文手中有足够的股票进入伯克希尔的董事会。但是,其他人也开始注意到了。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的老朋友杰克·亚历山大和同班同学巴迪·福克斯成立了一家合伙投资公司。“某一天,我们发现沃伦正在买伯克希尔–哈撒韦,”他说,“于是我们也开始买。”在一次从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办公室前往纽约的旅途中,他们告诉巴菲特,他们也在跟着他买伯克希尔,“他感到十分不安,他说,‘看看,这回你们搭错地方了,但那是不正确的,砍仓吧’”。
福克斯和亚历山大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就做错了?巴菲特让他们搞明白了,他正在寻求伯克希尔的控制权。但即使这样,对于这群格雷厄姆的门徒来说,搭顺风车也是一个受欢迎的消遣。实际上,巴菲特收购了他们的股票。他说,我比你们更需要它。他们同意以当时的市场价格将股票卖给他,因为很显然这对他关系重大。而且,看来他还有其他的秘密方式接近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家公司对我们无关紧要,可很显然对巴菲特非常重要。”亚历山大说。
和福克斯以及亚历山大一样,还有一些人也成为巴菲特的观察者,像追踪大脚怪的足迹一样,跟踪着巴菲特的投资举动。这造成了对这只股票的竞争。巴菲特让这些格雷厄姆的追随者明白,他们最好不要染指伯克希尔。唯一的例外是亨利·勃兰特,作为对他服务的报答——他让勃兰特以低于8美元的价格买进这只股票。他开始看起来有点儿狂妄自大,这令一些人觉得很不愉快。可是,他一贯表现出的脚踏实地又让他们着迷,甚至他的吝啬也变成了光环的一部分。在很多年里,他可能都是那唯一的一个,虽然通常在纽约做生意,却不仅有免费寄宿的本事(在长岛,和弗雷德·库尔肯的母亲安妮·戈特沙尔特住在一起),而且得到了免费落脚的办公地点(在纽约,由特雷迪–布朗提供)。
但是,苏珊有时会陪同一起过来,在她的命令下,巴菲特会从他已故的大学朋友的母亲那儿的住处升级到在广场酒店开一间房。不仅是因为那儿很方便他做生意,而且在苏珊看来,那里离那些百货商店很近,如波道夫·古德曼、亨利·本德尔等。那时,一些谣言开始在巴菲特的朋友中传开了——这类谣言总是围着他不放,比如,他宁可让自己刚出生的女儿睡在梳妆台的抽屉里也不买张小床。说他在广场酒店找到了一间最便宜的房间,卧室很小而且没窗,和哥伦比亚大学那间旧的勤杂工房间一样,而且只要他单独一个人来纽约,他会谈到极低的价格入住。不管这些谣言的真实性,每次他登记入住酒店时,毫无疑问都会感到一阵遗憾,因为他再也不能不纳税就待在纽约了。
去波道夫购物是巴菲特已经改变的纽约常规之旅的又一个部分。白天苏珊主要是吃午饭和购物,晚上两人一起共进晚餐,接着去百老汇或者夜总会看表演。看到她能自得其乐,巴菲特很高兴,而且她已经开始习惯到高档一点儿的商店买东西。不过,虽然她现在有权放松钱包,可是他们之间还是会争论她应该花多少钱。而她调整消费的方式,有时仅仅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苏珊通常是受益者,她的衣橱里满是从波道夫买来的衣服。有一次,苏珊从纽约带了一件貂皮夹克回来。因为他们遇见了沃伦的一个朋友,他把他们带到了一个毛皮商那儿。“我觉得我应该买点儿什么,”她说,“他们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于是,她为了感谢毛皮商的热情而买了那件夹克。
现在,所有使投资伯克希尔免成错误之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除非巴菲特能够搞清楚怎样才能让它经营得好到足以让苏珊永远能穿貂皮夹克。他又去了一次新贝德福德,这次是去看看继承人杰克·斯坦顿。这个人将会从西伯里·斯坦顿手上接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需要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但是这位斯坦顿先生声称自己很忙,派了肯·蔡斯陪同巴菲特在工厂里走了走(和马尔科姆·蔡斯没有什么联系。伯克希尔精细纺织公司和哈撒韦合并后,马尔科姆·蔡斯担任董事长)。
杰克·斯坦顿根本不知道他的叔叔建议让蔡斯代替他,来接过西伯里的棒。
肯·蔡斯是一位专业的化学工程师,47岁,安静、自制,而且真诚,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未来掌管这家公司的竞争者。巴菲特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而蔡斯仔细解释,他总共花了两天的时间,告诉巴菲特有关纺织生意上的事。他的直率给巴菲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斯很明确地表示,他认为斯坦顿家族将钱砸入这样一个日薄西山的行业实在很愚蠢。当行程结束,巴菲特告诉蔡斯,他会和他“保持联系”。
大约一个月以后,斯坦利·鲁宾按照巴菲特的要求,去劝说蔡斯不要接受另一家纺织工厂的工作。同时,巴菲特正积极争取更多的股票,包括蔡斯家族里不同成员所特有的股票。
巴菲特最后的目标是奥蒂斯·斯坦顿,后者很希望他的兄弟退休。奥蒂斯对西伯里的儿子杰克很没有信心,而且他也怀疑西伯里是否真的愿意交出掌管公司的权力。
奥蒂斯和他的妻子玛丽同意在新贝德福德的沃姆苏塔俱乐部和巴菲特见面。他们在这座象征新贝德福德曾经的辉煌,具有优雅意大利风格的大楼里吃午饭,席间奥蒂斯确认了他愿意出售股票,条件是巴菲特要跟西伯里出一样的报价。巴菲特答应了。接着,玛丽询问出于家族感情,他们是否可以从即将出售的2000股中留下几股,就几股而已。
巴菲特拒绝了。要么全部,要么就一股也不要。
奥蒂斯·斯坦顿的2000股将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权提高到了49%——这足以保证他能有效控制公司。带着掌握一切的骄傲,4月的一个下午,巴菲特在纽约和肯·蔡斯会面,他们散步走到第五大道的广场和中央公园南端,巴菲特请客吃冰棍。没吃两口他就切入正题:“肯,我想让你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总裁,你怎么考虑?”既然他现在控制了这家公司,他说,就可以在下一次董事会上更换管理层。尽管鲁宾劝过蔡斯不要接受另一份工作时给过他暗示,可他现在还是被巴菲特的选择吓住了,肯·蔡斯答应在董事会开会前保持沉默。
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经被改变,杰克·斯坦顿和妻子从新贝德福德赶到广场饭店和巴菲特及苏珊会面,他们一起吃了早饭。凯蒂·斯坦顿为她的丈夫说好话,她是一个比丈夫更主动的女人。在谈到一个吸引巴菲特夫妇的话题时,她抛出了自己的想法,这才是关键:巴菲特当然不会推翻新英格兰这家世袭工厂留传下的家族管理传统,而让肯·蔡斯这样的工厂小人物来主持大局,要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一直在打理这门生意。她和杰克已经融入了沃姆苏塔俱乐部。更重要的是,和苏珊一样,凯蒂也是初级联盟的成员。
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过,她认为杰克因为他的父亲就应该有权接管公司,这让我印象很深。她的请求中一部分内容是说肯·蔡斯真的和杰克、她、我、苏珊不是同一阶层的人。
可怜的凯蒂,她的听众恰恰是一个蔑视世袭的人,并且对奥马哈的权贵嗤之以鼻。
现在对杰克来说已经太迟了,同样对西伯里而言也太迟了,他曾经独裁统治着这家公司,而在董事会一个朋友也没有。甚至他自己的董事长马尔科姆·蔡斯也不喜欢他。因此,在巴菲特的支持者于1965年4月14日为提名巴菲特加入董事会而举行的特别会议上,他凭借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支持很快被选为执行董事。
几个星期后,巴菲特飞往新贝德福德,迎接他的是《新贝德福德标准日报》的头条新闻——“‘外部利益’接管公司”。这个编造的故事激怒了巴菲特。他从丹普斯特得到的教训就是,永远、永远不要让自己被贴上清盘人的标签——这会招致全城人的憎恨。巴菲特向媒体发誓,他会让公司的运营一切照旧。他否认收购会导致工厂关闭,并且在公开场合发表了承诺。
1965年5月10日,董事会会议在新贝德福德的总部召开。会上提出给即将离任的负责销售的副总裁一笔丰厚的退休金,批准了上一次会议通过的详细内容,并且同意给职工增加5%的工资。接着,整个会议变得怪异起来。
70岁的西伯里,近乎全秃的头上遍布着老年斑,宣布他已经计划于12月退休,而让杰克来接替他的位置。不过,他又说,他不可能“在一个他无法拥有完全权威的机构里”继续担任总裁。只有像他这样傲慢的性格,才会让他接下来——尽管反叛者已经接管了这艘船——又说了一通,表彰了一下自己的功绩。接着他提出了辞呈,董事会接受了。杰克·斯坦顿跟着又添加了一小段尾声。他说,如果他在12月接任总裁,他很确定,这将意味着“继续成功和有利润的运营”。董事会成员耐心地听着,然后同样接受了他的辞职。
到那时,杰克·斯坦顿才放下他手中的笔,停止记录会议内容,而那两段发言已经被记录在内了。然后,两位斯坦顿昂首阔步地走出了房间。这时,董事会所有的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然后轻松地叹了口气。
接下来的会议进程很快,董事会选举巴菲特担任主席,确认肯·蔡斯将会主管——巴菲特一时愚蠢——费尽心思争取来的这家命中注定的公司。几天以后,巴菲特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如此解释他对纺织生意的看法:“我们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这是一个商业决定,我们尝试接触一门生意。对投资而言,价格是很大的因素,它会决定最后的想法。我们以一个好价钱买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
后来他重新修正了这个观点。
就这样我买入了自己的“烟蒂”,而且努力抽着。你沿着街道走,也许也会碰到一个“烟蒂”,它湿漉漉的让人很恶心,你避开了。可这是不要钱的……也许只剩一口。伯克希尔–哈撒韦也没什么了,只剩下湿漉漉的“烟蒂”在嘴里。那就是1965年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我的很多钱被套在这个“烟蒂”里了。 注释标题 Adapted in part from the documentary Vintage Buffett: Warren Buffett Shares His Wealth (June 2004) and in part from interviews.
如果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伯克希尔–哈撒韦,可能我的情况会更好。 从华尔街到硅谷(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