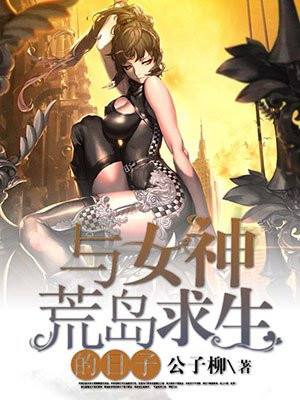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传声筒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初读《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对第一章的写作技巧印象异常深刻,就在《香港时报·文与艺》上介绍了一下。当时写了两千多字,由于篇幅所限,无法把全章译刊,只抽取其中五段对话,大略讲述了时间浓缩的手法。许多年来,总觉得没能够好好地把那章节说个清楚明白,所选五段对白,也不连贯,看不出原著的紧密复杂,当下打算一有空,就把全章译出来,再讲一讲。近读五月号《十月》,发现小说已有中译,并发表了第一章全译,高兴莫名,就采用孙家孟先生的译文,还一个心愿。孙先生的译文,后来连同其他各章出了书,不过稍有删节。这里仍用《十月》较完整的译本。
1 本事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是秘鲁小说家马里奥·巴加斯·略萨一九七三年的作品,全书十章,采用了多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既有罗列的公文文件和各类事件的汇报(第二、四、六章),又有广播电台的节目和地方报章的报道(第七、九章);其中四章完全由对话体构成,场景繁复,人物众多,作者采多角度、多镜头的技巧,全面推进,有如立体主义的绘画作品,把许多个面同时呈现,是结构现实的代表作。本文抽取全书的第一章,试作分析。以下先把故事略作介绍。
潘达雷昂在陆军服务,尽忠职守,工作表现优异,由中尉升为上尉。陆军总部的将领找他密谈,交给他一项艰苦的机密任务。原来,天气炎热,军纪松弛,由于这样那样的理由,边境地区不断发生士兵污辱妇女事件,总部因此要他扮作商人到那里秘密组织军中流动妓院“劳军队”。潘达雷昂带了母亲和妻子前往,瞒着家人,积极工作,成绩斐然,良家妇女安全了,可是社会舆论却谴责伤风败德;而广播台乘机敲诈,不果,一怒之下揭露“劳军队”的活动,使潘妻大怒离去。这时,名妓“巴西女郎”遭歹徒杀害,潘达雷昂很激愤,穿上军装送葬,暴露军人身份。将军们急忙善后,一面解散劳军队,一面把潘达雷昂召回发配北部高寒地区,成为丑闻的代罪羔羊,劳军女郎则被将军及神甫据为情妇。
小说的第一章,叙述潘达雷昂升职,被陆军总部将领密召,授以新任务。潘达雷昂硬着头皮带同母亲妻子前往履新。全章只以对话呈现动作情节的进展,为了方便讨论,现把全部对话二百零五句编上号数,其中场景、人物、地点,也先在下文简列出来。
小说的第一章结构,主要可分为七处场景,分述如下:
(一)潘达雷昂在首都利马家中。
主要人物:潘达雷昂(昵称潘达、潘弟达)、母亲雷奥诺尔太太、妻子波奇塔(昵称波恰)。
(二)利马陆军总部。
主要人物:洛佩斯·洛佩斯上校、维多利亚将军、柯亚索斯将军(外号老虎)。
(三)边城第五军区司令部。
主要人物:斯卡维诺将军、军中神甫贝尔特兰、电台播音员辛奇
(四)边城酒店。
主要人物:潘达雷昂、波奇塔
(五)潘达雷昂在边城的住家。
主要人物:潘达雷昂、雷奥诺尔太太、波奇塔。
(六)边城酒吧。
主要人物:潘达雷昂、巴卡柯尔索中尉。
(七)边城妓院“茅茅”和“秋秋蓓”。
主要人物:潘达雷昂、浪子波费里奥、秋秋蓓太太。
除了上述的场景外,另有一名佛兰西斯科[弗兰西斯科]兄弟,属于“方舟兄弟会”的宗教组织,在边区流徙传道,该会相信世界末日将要来临,只有把人钉在十字架上,学习耶稣为人类赎罪的榜样,才能推迟末日的到来。他们把无辜百姓随意钉死,治安大乱。
整章小说中还有许多军人、市镇的长官,以及平民百姓,他们都说了话。他们多数是投诉士兵侵犯妇女。有的还是当事人,有的则是受害者的丈夫和亲属。
2 空间的浓缩
故事展开。
一开始的时候,陆军中尉潘达雷昂在利马的住家中,清晨被妻子叫醒,梳洗一番,要去见长官,不知道会接受什么新的任务,到什么地方去工作。母亲和妻子对他服侍得无微不至,吃过早餐,他就上军部去了。这一个场景,是小说中[1]至[10]的对话。
对话[11],写“方舟兄弟会”的圣佛兰西斯科兄弟在边区传道的插语。
潘达雷昂抵达军部,经过秘书小姐的通传,见到了上司洛佩斯·洛佩斯上校。原来室内还有两位将军在等他,要交托给他一个重要的机密任务。将军们告诉潘达雷昂,他们经过细心调查,在整整八十个军官中,选中他这忠于职守的人。
将军们和潘达雷昂说话的时候,不时要接听电话,其中一个电话是边区第五军司令斯卡维诺将军打来的,场景就推接到边区的司令办公室去。对话[28]、[32]都是斯卡维诺将军提起潘达雷昂的工作,因为这个人将派到他那里去。
当将军们把新任务的内容和原因告诉潘达雷昂时,小说就把兵士们侵犯妇女的事,借各乡镇长官和平民纷纷向军部投诉抗议来呈现,对话[36]是一名市长说自己的弟妹被糟蹋了,对话[39]是另一位市长的投诉,对话[38]则是边区军中神甫的抗议声。接下去,出现了妇女的哭泣、军方的安慰、亲属的埋怨,还加上对话[47],一名电台广播员辛奇的大声疾呼,从空中播送。
这一段投诉的场景从对话[36]到[52]原则上结束,接着,小说用溶接的方法,溶入潘达雷昂家人知道了新调派,全家要搬到边城依基托斯去的一场。
电影中的溶接,是把两个不同的场景,用淡入淡出的剪辑方法连接起来。比如,上一场是城市,下一场是乡村,如果镜头一转,由城市突然变为乡村,是普通的直接割接;溶接则是缓慢的交叠:上一场的城市由清晰变为暗淡,而下一场的乡村由暗淡变为清晰;上一场渐渐淡得没有影子,是淡出,下一场由暗淡接上,渐渐清晰,是淡入。溶接时,两场的景物会交叠同时出现,观众可以同时见到城市的高楼大厦,也可以看见乡村的小桥流水。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第一章对话[53],是溶接的淡入开始,写上尉家人对新任务的反应,渐渐淡出的是军部的任务委派。因为是溶接,所以两个场景会同时出现。不过,电影和小说当然不同,小说有小说文字序列上的局限,只能先后交接出现。
对话[54],又插了一个传道的镜头。对话[67]则是透过电话通话,边区小镇奥贡内斯向边区第五军部依基托斯作报道。不过是一个电话,就把两个地方的现状连在一起。
利马陆军军需处的场景,由对话[12]开始,到对话[82],就正式结束了,全部淡出;而淡入的一场,渐渐清晰、明亮起来。如今潘达雷昂一家三口,由首都利马搭乘飞机到边区重镇依基托斯去。对话[83]是家人乘搭飞机,然后他们抵达依基托斯,先住在酒店里。这一个场景,到对话[105]结束;中间插入对话[100]和[102],叙述当地司令部将军和军中神甫的对话,对潘达雷昂将展开的工作表示不满。
抵达依基托斯市后的潘达雷昂,到第五军区司令部向斯卡维诺将军报到,并没有受到热烈的欢迎,而是一片指责。潘达雷昂只好为自己辩护,说这件事完全不是他的主意,他不过是受命而来工作的,他自己对“劳军队”的事务全无兴趣,甚至请求将军把他调走。将军发了一顿牢骚,明知一切不可挽回,只好告诉潘达雷昂该怎么执行:不许他回军部露面,不许穿军装,不能泄漏军人身份,不能和军人生活在一起,家人不能和军眷往来,居所也要安置在偏僻的地方,工作要秘密进行。为了保密,只可和特派员巴卡柯尔索中尉每周见面一次,向司令部汇报工作状况。由对话[106]至[140],是这一场景的过程。斯卡维诺将军和军中神甫贝尔特兰道貌岸然,摆出卫道者的姿态;后来,“劳军队”被迫解散,妓女们却被他们占为情妇。
在上面的场景中,作者仍然抽空加插了圣佛兰西斯科兄弟的传道[118]。对话[140]与[141],是一次干爽利落的直接割接,斯卡维诺将军刚说完指派一名中尉做联络员,联络员就立刻出现说话了。这时,场景也由军区司令部割接上一间酒吧,巴卡柯尔索中尉和潘达雷昂一面喝啤酒,一面讨论工作将如何推展。潘达雷昂本来是个烟酒不进,不上红灯区的模范军人,所以,联络员教导他该找当地的三教九流人物、到烟花地带去,扮成商人的模样。这一场由对话[141]到[164],写两个人在酒吧的会面,不过,这场景作者采用了交替剪接的手法,把另外一个场景叠放在一起,成为一组平行蒙太奇。
电影上的平行蒙太奇,是把银幕的叙事次序分割开,让两个场景交替呈现,可以产生紧凑比对的效果。比如说,一个女子被匪徒绑架,困在屋子里;另一边,侠士来救她了,电影镜头就会这头叙述匪徒如何对女子不利,另一头描写侠士怎样骑马赶来。
小说运用的一组平行蒙太奇,这边写两个人在酒吧喝啤酒,另一边则写潘达雷昂的家人在边区找到了居所,布置屋子。同时,从她们的话语中,也表现了潘达雷昂已开始执行任务,一直严守秘密,使她们感到他的行为奇怪,不免咕哝起来。这一场由两个场景组成的平行蒙太奇结构,到[164]告终,对话[165]又出现了佛兰西斯科兄弟传道的声音。在整部小说中,“方舟兄弟会”的传道是一条重要的支线,到了最后一章,这条支线就和其他各线合流;不过,在第一章里,它只是疏疏落落地不时冒一下子,仿佛涓涓滴滴、隐隐蔽蔽的岩洞流水。
为了执行任务,正人君子潘达雷昂硬着头皮到红灯区,扮成商人的模样,他先到“茅茅”来,对话[166]。他见到了这一区的重要人物浪子波费里奥,从他身上掌握了不少资料。通过浪子的带领,潘达雷昂来到另一所妓院,结识了秋秋蓓太太,又了解了不少夜蝴蝶的情况。“劳军队”的任务,总算有了一点头绪。[166]到[194]的这一场景,仍然加插一次佛兰西斯科的传道[184]。
小说第一章的末节,是潘达雷昂从红灯区出来,回到家中,喝得烂醉,对话[195]。妻子和母亲对他的行为大感惊异,母亲细心给他敷冷毛巾,喝健胃水和热咖啡,妻子则认为他在外面鬼混,气得哭了起来。全章在一片忙碌之中结束,对话一共二百零五句。
说是“对话”,其实,小说有不少的句子只是独白,只是一个人在那里讲话,并不与别人交流。例如佛兰西斯科,只是他一个人在说教;电台广播员辛奇的播音,则是单程的声音;至于电话,也不一定有直接的答复。原则上,多数的说话都是对话,要注意的却是:巴加斯·略萨在这里用的对话,和传统的小说对话并不相同。一般的小说出现对话,如果甲乙两人说话,就是甲乙甲乙甲乙的形式,在这一章小说中的对话,因为场景交替,人物众多,即使甲乙两人对话,他们的话会被其他场景各人的说话隔开,成为甲丙乙、甲丁乙,甚至甲丙乙丁的形式。举例来说,[68]是老虎对打电话来的少尉那边的回复,[69]是雷奥诺尔太太对儿子说话,[70]是洛佩斯·洛佩斯上校对下属潘达雷昂的话,而[71],则是波奇塔对丈夫说话。一共四段对话,说话的有四个人,对象反而只有两个,次序上是甲乙丙丁四人,但这四个人说的话彼此之间全无关联。同样地,甲说了一句话,可能要过了一阵,我们才找到另一个人的答复,比如[152]、[154]、[156]、[158],潘达雷昂说了四次话,到[160]才得到中尉的答话。
在平行蒙太奇组合的一段中,[145]至[164],潘达雷昂家人的说话,都是对潘达雷昂说的,像[149]、[151]、[153]、[155]、[157]、[159]、[161]、[163]各句。妇人说话的时候,潘达雷昂显然是在场的,而且一定答了话,不过,作者把他的答话省去了。因为答了,也不重要。故此,只呈现妇女们一句又一句的问话,显示她们的不安和噜苏。在这场中,潘达雷昂也说了不少话,看起来,次序没错,[149]是波奇塔说话,[150]是潘达雷昂说话,[151]是雷奥诺尔太太说话,[152]又是潘达雷昂说话,不是对话吗?事实上四句话语之间并无关联,潘达雷昂的话,都是在酒吧中和同僚说的。
人物出现得最多的一场,是[36]至[52],是偏僻小镇各地的投诉和抗议,人物既有市长、兵士、神甫,木匠、电台播音员,还有一群妇女。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说了一次话。除了偶然的一两段对话,其他的话,看来都成为独白。[41]和[42]仿佛是对话,不过,前一句是陶乐德娅哭哭啼啼回答彼德·卡萨沃基上校的安慰话,后一句却是玛克西莫·达维拉上校对赫苏斯小姐的说话。只不过两句对白,牵涉的是两处不同的场景,人物却有四个。虽然这样,文意可又巧妙地相连。
全章小说中的剪接主要是用直接割接,但也用过溶接和平行蒙太奇的交替剪接。此外,还出现了连类剪接;连类,是把相同的事物并列在一起,或者以一件事物作为媒介,把两者串连起来。《诗经》中常常出现连类对举的手法,比如: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用参差荇菜起兴,然后反复回增,引申各章节。至于这章小说运用连类剪接手法的也有多处,举例来说,对话[10]是潘达雷昂在家里,清晨吃过早餐上军部去,母亲送他出门口,对他说:去吧孩子,我祝福你。接下来,对话[11]却是佛兰西斯科兄弟传道说:以上帝、圣灵和死于十字架上的圣子的名义。[10]和[11]本来距离遥远,表面上也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作者用了“祝福”——两个场面都出现的事情,有机地把上下场连接在一起。对话[105]和[106]也是连类剪接,[105]是潘达雷昂抵达依基托斯市,住在酒店里,和妻子调情,说自己飘飘然,不知自己是谁;接下来,第[106]句,是依基托斯市第五军区司令斯卡维诺将军对潘达雷昂报到时说的话:你是谁,我知道得清清楚楚。“谁”是联珠,这次反而有对抗的意味。连类剪接可以产生对比、讽刺、一气呵成的效果;当然,如果滥用了,就显得刻意匠气。
把许多不同的场面,用各种剪接手法连接,并列在一个平面上,全面推展故事,是一种新的结构方法。这是巴加斯·略萨对传统小说艺术的突破。如果依照传统的写作,作者得一处一处地写,整个篇章将被分为数十个小章节,而且必得“分头描写”:故事大概仍以潘达雷昂这个人物为中心,依次来回家中和军部,又搭乘飞机到依基托斯报到,闷闷不乐,和同僚到酒吧见面,到红灯区去工作,醉酒回家,等等。这是一条直线,至于小镇各处的抗议和投诉、军部与边区司令部之间的联络,就得分别穿插,会相当疏散。如今,作者仿佛立体主义绘画的画家们,把一个人的正面、侧面都叠画在一个平面上,使我们看见同一张脸的几个面,可以有三只眼睛,三只耳朵,以及一个既属于正面又属于侧面的鼻子。运用新的构成方法,作者把许多场景并列,成为综合的整体,既不必分头逐一描写,也可以把极细微的场景轻易捕捉,让当事人亲自登场,正面讲述,浑成一个统一的空间。像电台播音员的广播,不过一句口白,却让如此重要的人物也亮亮相。至于佛兰西斯科兄弟的传道,本是小说中重要的环节,作者无需另花许多笔墨叙述,在这一章,显得不经心地只出现了四次,这是非常经济的笔法,也是空间浓缩的最佳示范。
半世纪以前,约瑟夫·佛兰克[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的著名论文《现代小说里的空间形式》讨论福楼拜时,指出福楼拜呈现三种共时情节的技巧是:把对话并置,通过来回切断时间,取消了顺序。佛兰克称之为“形式空间化”。这是现代小说的源头。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里个别的手法,到了乔伊斯,则成为了《尤里西斯》整个小说的审美结构,读者必须反复“重读”才能理解这小说;读者要把小说里各个或明或隐的片段重建,而这些片段可能前前后后分布各章。读者在这种重建的过程里,其实也参与了小说的创作。巴加斯·略萨是福楼拜迷,并且写了研究的专书(《永恒的狂欢—福楼拜和<包法利夫人>》,1975)。他的《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显然跟福楼拜很有渊源,有承继的地方,也有创新的地方,这是小说家与小说家之间,越过国界、种族和时间空间的对话。他并置了更多的人物和情节,读者听到比《包法利夫人》农产展览会里更多的声音,往来应答,有一言堂,有小组讨论,有的亲昵,有的粗俗,有的劝世……但作者致力的,反而是情节动作的共时发展,声音之外,空间在不停地变换,而时间之流在暗地里游去。
3 时间的浓缩
把不同的场景聚合并列,是巴加斯·略萨空间浓缩的手法,面貌清晰,层次分明。至于他运用的时间浓缩手法,可能不易得到一般读者的注意,甚至被忽略了。时间的浓缩,主要出现在潘达雷昂一家人的生活细节表现上,尤其是他们乘搭飞机,以及在依基托斯布置新居的两场上。对话[83]到[89],寥寥七句对白,写潘达雷昂一家人从利马到依基托斯去。人物说了话,话题和上下文的特种任务有关,是小说的主线,不过,在这一段叙述中,对话都变成次要的焦点,重要的反而是人物的动作。且看看这些人做了些什么。[83],波奇塔把机票放在钱包里,一面打听机场的入口处。这时,一家人显然买了机票去搭飞机了。[84],雷奥诺尔太太望着云层、飞机的螺旋桨和下面的树木。这时,潘达雷昂一家人显然已经坐在飞机里,在天空中了。[85],潘达扣上安全带,并且说,马上到了。这时,飞机已经抵达目的地,旅客要扣上安全带等候降落。[86],波奇塔戴上太阳镜,脱下大衣。这时,一家人已经抵达依基托斯市,天气炎热。[87],潘达打开皮夹,付给司机几张钞票,并且说:对,师傅,门牌五四九号,利马旅馆。这时,一家人从机场直接到酒店去住了,利马旅馆只是名字,地点却是依基托斯。[88],波奇塔把旅行袋摔在椅子上,脱掉皮鞋。显然,一家人已经办好住宿手续,在酒店内休息了。
从[83]到[88],一共六句对话,作者却借三个人闲话家常,快捷利落地交代他们从利马到达依市,文字非常经济,机场、天空、机场、计程车、酒店,就完成了整个出门远行的旅程,毫不浪费篇幅。这种写法,一面以对话进行小说的主线,一面以行动过渡时间,是双线推进法,颇像一个人弹琴,右手弹乐曲,左手奏和弦,互相配合。不过,这一段只呈现了时间浓缩的一点面目,时间浓缩表现得更透彻的,还是婆媳二人布置新居的一场。
对话[145]至[161],是由两个场景交织起来的,其一是潘达雷昂和同僚在酒吧中讨论如何进行工作,另一场则是潘达雷昂的母亲和妻子在家中布置新居。时间如何浓缩呢?看看两名女士的家务就知道了。[145],雷奥诺尔太太看了看斑驳的墙壁、肮脏的地板和布满蜘蛛网的天花板。这时,一家人搬到依市,面对一间极不像样的屋子,又脏又破烂。[151],雷奥诺尔太太举起掸子、扫帚、铝桶,又是掸,又是扫,又是擦。当然,搬进了那么糟的一所屋子,只好动手打扫了,首先把屋子洗擦一番。[153],波奇塔擦着玻璃,洗扫地板。洗擦干净之后,开始粉刷墙壁。工作都按部就班。[155],波奇塔在髹门,刷衣柜,挂画。屋子的墙壁粉刷过了,就可以把门漆好,也可以挂画。[157],雷奥诺尔太太整理衣柜,缝窗帘,掸灯罩,插开关。屋子显然髹漆好了,可以缝制窗帘张挂了。[159],波奇塔整理床铺,铺上台布,髹漆家具,把杯子、盘、餐具摆进食柜里。如今,整座屋子打理好了,可以居住了。我们看到:这家人并没有买新的家具,而是动手做。一来,这军人并非富有,二来,也不便招摇。猪圈似的地方终于变成了可以生活的家。
仍是六句对话,作者就把一家人布置屋子的过程娓娓陈述,手法上依然两线进行,对白是对潘达雷昂的工作感到奇怪,行动是做家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如何做家务。比如[153],做妻子的完成了三件工作:擦玻璃、洗刷地板、粉刷墙壁。都不简单,给屋子擦玻璃可能要花几个小时,洗刷地板也不是几分钟可以做完的事,至于粉刷墙壁,可能要整整一天,而且,还得等墙壁干透了才能挂画。依照真实的时间,擦玻璃、洗地板和粉刷墙壁,起码要花一整天的时间,可是,做这三件家务时,波奇塔在小说时间中只说了一句话:连邻居都不能让他们知道你是上尉?说一句话,几秒钟就够了。一个人能够在说一句话的时间内,做三件粗重而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家务么?但小说可以。巴加斯·略萨用他的独创手法,把时间浓缩,使一个人在说一句话时完成了许多工作。这正是作者创新的地方。埃里克·拉布金(Eric Rabkin)曾比较小说形式的时间和真实的时间。他指出小说主要运用三种不同的报告形式:叙事、对话、描写。叙事在阅读的时间里,往往短于真实的时间,试想想,原本要花一整天整顿房子的时间,书本上几句话就完成了。对话在阅读的时间通常跟真实时间相近,例如“没什么,妈妈;没什么,波奇塔”。至于描写,或者因人也因事而有所分别,但总长于真实时间,比如,一个人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一瞥,大致上已把握了这人的模样、服饰、姿态,可用文字描写,得一一道来,要用整段的文字才行。这小说并没有那种浮泛、空洞、一连串形容词的描写,而是把描写潜藏在具体的情节动作、说话里。这方面,下文再分析。
从这一个场景看,妇人的说话和进行的工作,是小说同时推进的两条线,主线是对白,她们都担心潘达雷昂接受了什么可怕的特别任务。她们的家务是副线,描写他们搬到了依基托斯整理居室的情形。把两条线一起写,就不必“花开一枝,话分两头”了。这样子双轨行进的处理法,本来可能该用十万字去写,结果只需五万竟可把细节囊括,也可看出作者把时、空浓缩,同步并置的手法。
双线推进小说故事发展的写法,可以采主线副线相同的比重,可以采主线强副线弱的比重,也可以把重心放在副线。像两名妇人在新居做家务,显然是副线较强。这情形颇像电影中常用的镜头,焦点不同,效果各异。比如说,镜头的焦点可以调到前景上,那么,背景就朦胧了;相反,把焦点调到背景上,那么,前景就朦胧起来。两名妇人做家务时,作者的叙述焦点显然集中在工作上,所以,一连串的行动清晰,她们的对白因此比较朦胧。
同是一组平行蒙太奇剪接,小说中的交替剪接效果明显比不上电影,这是文字的局限。在小说中,场景的并列,即使排在同一页纸上,阅读的时候仍要分先后次序;但电影呢,如今的银幕上可以同时出现几个不同的场景。这方面,电影比小说占优势。那么,小说可有比电影占优势的技巧吗?
对话[153],波奇塔可以只说一句话,然后做了抹玻璃窗、擦地板、给墙髹漆三件工作,工作逐一完成。如果把这场景搬上银幕,画面展开,波奇塔出场,说:甚至邻居也不可知道你是上尉?话很快说完了,电影镜头如何描写她完成了三件繁重的工作?拍摄她抹窗子、擦地板还是髹墙壁?如果三件工作都要在一句对白中全部呈现,并且表示完成,拍出来的画面,怕要变成一组快镜,活像那些变速的默片,只见一个人飞快地跳来跳去,非常滑稽。巴加斯·略萨的时间浓缩手法,的确使电影眼睛除了变速外,目为之瞠吧。何况,文字赋予读者更多想象的空间,反复沉吟的余裕。这正是文字的好处。
类似的时间浓缩手法,每次潘达雷昂一家人在一起时就出现了。比如开头,对话[2]是潘达雷昂被妻子叫醒,还打着呵欠,对话[4]已经表示他起了床,洗脸擦肥皂刮胡子了,对话[6]时,他已经穿戴整齐,对着镜子打领带,对话[9]是吃早餐、喝咖啡,到了对话[12],他已经抵达军部。简简单单地说过五次话,却完成了一个人早上起来该做的所有工作。同样地,最后一场是潘达雷昂从红灯区回家,喝醉了酒。每说一句话,雷奥诺尔太太都做了许多事,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拿水递毛巾、给儿子喝健胃水和咖啡。
小说与电影的叙述手法,各有所长,彼此影响。如果把《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搬上银幕,相信会是颇壮观的景象,银幕上可以同时出现两个不同的场景,甚至三个、四个、五个、六个,还可随时扩展或还原,真是变化无穷。比如银幕上本来只有潘达雷昂一家三口早上在家里吃早餐,到了母亲祝福儿子上班,银幕可以分裂为两个场面,一边是母亲祝福儿子,一边则出现了佛兰西斯科兄弟的传道,接着,家庭场景消失,出现了军部的一幕,分裂的画面又可以合而为一,直到对话[36]开始,银幕上再次可以裂成许多不同的画面,画面A是市长揉着帽子大叫,画面B是军中神甫大声疾呼,画面C是另一名市长在跳脚,画面D是陶乐德娅在哭,画面E是木匠在投诉,画面F是电台广播员在播音……许多画面同时出现,他们的声音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配合画面说出来,既可吵成一片,也可以单独逐一讲话,然后,电影继续进行,或溶接,或交替剪接,或多镜头剪接,真叫人目不暇给。当然,遇到那几场搭乘飞机和布置新居,就得费心处理了。问题在画面长时间割裂,各种影像、声音一齐来,稍纵即逝,我们也许需要八只眼睛,十二只耳朵。
4 描写、结构写实
小说篇章只以对话来推展故事,怎样描述景物呢?传统的小说可以把人物的面貌、服饰、姿态仔细地陈述。巴加斯·略萨既然用对话的手法,就把描写景物减至最低。但不等于说他把景物完全舍弃了,景物反而技巧地、有力地反映出来。他依旧用最简练的文字,描写首都利马和边城依基托斯。对话[5],借波奇塔的眼来看利马:灰色的天空、房顶、汽车和行人。这是低调子的描述,利马,就像任何一个城市一样。小说的重心是依基托斯,利马不用多花笔墨。那么,依基托斯又如何呢?[115]里,潘达雷昂从将军的肩上看出去,看到浑浊的河水、一只满载香蕉的小船、蔚蓝色的天空和火红的太阳。[124]里,贝尔特兰神甫也转过脸去朝着窗子,踮着脚望着粼粼闪光的河水、茅屋和生长着树木的平原。[139]里,潘达雷昂望着远处一个光屁股的小孩在爬树,一只红羽鹭鸶在一瘸一拐地走动。天际,一片灌木丛在喷出火焰。不过是几笔,依基托斯的面貌已经出来了,河、树、禽鸟、水果、阳光、热带、炎夏,一片色彩缤纷的原始市镇。而利马是灰色的。
依基托斯是炎热的地方,所以,斯卡维诺将军要不断吹风扇,[108],他把秃头凑近电风扇;[110],他打开手帕,擦了擦前额、两鬓和脖子上的汗;[114],他抓起电扇对着自己的面孔、头顶;[125],将军又坐了下来,吹着电风扇;[129],将军把手掌、手背放在嗡嗡作响的看不清的扇片前来回翻动着。而贝尔特兰神甫,风扇被将军占用了,只好不停地挥扇子。至于利马的将军们,则悠闲舒服地坐在沙发上抽烟。作者如此三番四次写风扇、抹汗,既呈现依基托斯是一个炎热的边城,是否也在暗示:“劳军队”这件事,是一座火山?
边区的依基托斯是这么的一个原始城镇,作者在潘达雷昂和同僚在酒吧中喝啤酒时,也反映了一笔:人们把猴子、鹦鹉和鸟儿做成标本;喝酒的时候,巴卡柯尔索中尉夹给潘达雷昂一片煎蛇肉。这种把描写融化在叙述里的手法,正是福楼拜式的。在巴尔扎克时期,描写是独立结构,和情节分开。
聚合了众多的场景全面推进,产生的效果,以空间、时间的浓缩最明显。同时,这一章写得成功的,还有密度与节奏。由于场景多、人物众,整章小说仿佛一盏转不停的走马灯,角色不断流水出场,一个紧接一个,毫无空隙。场景多、人物众,也显得这章小说热闹、忙碌、喧哗、充满动感。这些,正配合了作品的风格,因为小说一直用讽刺的手法来叙述,反映秘鲁军方的腐朽。如果小说用冷静缓慢的调子来表现,反而显不出潘达雷昂这名荒谬英雄的处境。我们的荒谬英雄就在各种喧闹里从事一种说不得的任务。这种说不得,包括在军队里没有名分,家人都不能接受,同时也不容于个人的道德、操守,真是内外交困。在个人与军规之间,只有他,一个正人君子,成为吃黄连的哑巴。
密度高,节奏明快,是这章小说的特色。在电影上,爱森斯坦和雷诺阿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多用短镜割接来组织画面之间的秩序,后者以单镜头娓娓叙述,各成典范。巴加斯·略萨本质上长于单镜头式的叙事,例如他其他的作品:《城市与狗》、《青楼》[《绿房子》]、《教堂咖啡室中的对谈》[《酒吧长谈》]、《胡利亚姨母与剧作家》以及《世界末日之战》都充满单镜头的调度,所以,《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短镜剪接法反而是例外。但,小说写得好不好与是否例外是两件事,得看运用的技巧是否适当切合要写的东西。这次的短镜剪接无疑切合不过了,我们就读出一片炎热、忙碌、焦虑、疑惑、喧闹、滑稽、腐败和混乱的场面。巴加斯·略萨的作品,结构上总是各有特色,而又切合要呈现的现实内容,难怪论者称他为“结构写实”的典范。这是他和其他大部分拉丁美洲作家的分别,他们擅长魔幻写实,而巴加斯·略萨的作品,并不魔幻。
5 翻译
最后,顺便提提小说的译文,作品原本的名字是《潘达雷昂与劳军女郎》,中译加上了上尉两字。成为《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葛洛瓦高斯[科洛瓦科斯(Gregory Kolovakos)]和基利斯特[克里斯特(Ronald Christ)]二人的英译则用《潘托哈上尉与特种任务》。内文方面,英译比较详尽,也较典雅;中译有些地方粗俗些(也许这样更体现了作者的原意),由于道德标准尺度有别,不得不省略了某些句子,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整体而言,中、英两个译本,各有优点,略有微瑕。译事艰难,如果觉得中译尚有不足之处,也许是没能把波费里奥译得更传神,因为这个人是华裔,只会讲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不准。英译用拼错的字来显示,比如他说:“我也在那里,简直人山人海……”([183])英译是:I was thele too and thele was lotta people。又说:Fantastic speakel, that blothel. You not understand him vely good.至于中译,却仿佛他是一个外语流利的人物。这里,作者并没有歧视华人的意思,相反,后来的章节显示,低下层的人物反而成为上尉的朋友;上层的,自命得道的,不过惺惺作态,他们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
读过萧乾译菲尔丁的《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里面有一封情书,是那名当代纨绔公子的手笔,别字连篇,译得很传神,留下深刻的印象:
最神圣而至可敬木的人儿:
你的眼京既然比太羊还亮,能在我心中引起火苗,我相信它们一定可以洞见我的心。如果说你不知道我的爱情,那是荒堂。不,小姐,我正重否认,走遍全球世界也找不到有人像你那样迷住我的眼京。没有你,就是公殿也成沙漠,可要是有你的话,旷野也会比天堂还可爱。西望你相信我发的誓,指要能和你同在一起,天地下处处都是天堂。我相信你对我爱情的强列,不加怀宜。我不能把这爱情藏起,正如你——或者太羊不能把美容藏起一样。请相信,自从上次看见你的方容,我一直没睡成叫。西望你大开红恩,准我下午来拜见,容杏之至。谨向我最神圣的人儿致最大的敬意。
最热列敬木你的崇拜者和奴才
江奈生·魏尔德顿首
《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中译里有一二处,或仍可斟酌。现选主要的几点来说说。比如[155],中译是:波奇塔在髹门,刷衣柜。这两件工作照字面来看,给人的印象是髹漆门扇和把衣柜扫刷干净,显然和真正的意思稍有出入。原文encera puertas是给门扇上蜡;而empapela armarios则是为一个柜糊纸。其中并非没有分别,打蜡的时间可能较油漆短,不过,糊纸的工作却要比扫刷所需的时间长。
此外,第[4]句,丈夫对妻子说要一条毛巾抹脸。中译是:把毛巾递给我。原文有por favor,英译也用了please。本来,少了一个“请”字,似乎不大重要,其实,这一个“请”字,显示了拉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夫妻也可以是平等的,丈夫没有大男人主义,很尊敬妻子,尊重女性。
第[118]句,是佛兰西斯科兄弟在传教,西班牙文中的su,既可指他的,亦可指她的,被译成了不同的意思。中译全译作她的:她的肉体,她的血,她的眼泪,她的汗水。在这里,“她”泛指母亲。英译则译为“他的”,而且是大楷的写法His。这么一来,指的就是耶稣了。后者或更贴切。因为是传道的声音。
第[144]句的翻译,挺有趣,中尉夹给上尉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中译说是一片煎蛇肉,英译说是炸马铃薯片(potato chips)。而原文的chonta,我只知是棕榈树。可把我弄糊涂了,看来要去请教朋友。为什么那么重视这食物?我觉得它反映不同地方的饮食文化,在香港,吃一碗蛇羹,极富地方色彩,可是喝一盘罗宋汤,却是另一回事。
第[170]句,中译把妓女译为夜蝴蝶,既忠于原文,而且传神。
第[178]句,波费里奥唱着母亲编给他的歌,中译是:“本人天生是穷厮,老鸨小偷干到死。”其实,原文是母亲的预言:“华人天生是穷厮。”这里有华人的辛酸史迹,从上一代吟唱下来,并非单指波费里奥。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初稿,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修订 传声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