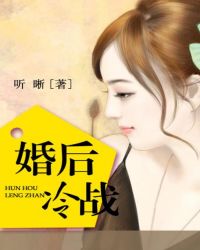有一种记忆叫刻骨铭心——读李致《牛棚散记》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有一种记忆叫刻骨铭心——读李致《牛棚散记》
余启瑜
1969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
巴金《随想录》
2007年春,我第一次得到李致题字送我的新书《终於盼到这一天》。该书所记录他在“文革”期间被监管经历的“牛棚散记”,就收录其中。其实,书中还有《我所知道的胡耀邦》和《小萍的笑容》两篇文章,虽然没有纳入“牛棚散记”标题內,但同样与“牛棚”生活有关。2015年,由四川省散学会选遍出版的名家自选集,李致又在他的《李致文存:我的人生》中,再次将这组文章完整地选编入书。事隔八年,重读“牛棚散记”,仍然感到“文革”往事不堪回首,历史悲剧发人深省!李致作品一向以注重事实,文词简练为特点,“牛棚散记”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组文章。
李致从事写作几十年,著作丰厚,“牛棚散记”以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和《小萍的笑容》在他的作品中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这十来篇文章在作者心目中的感受却是非同一般。他不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叙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身心倍受煎熬和极其单调的日常生活细节中,以不同的內容和角度,像剥茧抽丝一样,为读者再现了那个荒唐年月里的荒唐事件,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在巨大的政治风浪中对真理的渴求、对正义的呐喊、以及对信仰的坚守之后,终于迎来春回大地、阳光普照的心理历程,《终於盼到这一天》和《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就是李致在“文革”中的心灵实录,是他重获新生之后面向苍天喷涌而出的一种释放,是面对亲人,从內心深处呼出的一声长叹!
但凡经历过那个荒诞岁月的人,都知道“牛棚”是集中看管、关押“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专属居所。李致似乎还是算幸运的,因为他所进入的“牛棚”,就在他所属机关的南院,离家不过一箭之遥,而且,妻子、儿女尚在咫尺,甚至,年幼的儿子还可以定期给他送些东西过去。不过,但凡是进了“牛棚”,一切待遇就与家的距离无关了。
“运动来势很猛”的时候,很多“大人物”都是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关进“牛棚”,瞬间沦为阶下囚。这个时期,“革命群众”纷纷忙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致这个“小当权派就暂时被搁置下来”,这使他赢得了一个尚可冷静思考的空间。当他感到“风云突变”,“三天內,(单位牛棚里)人员不断增多”的时候,这个信号使他准确地判断出,自己被“关进去的可能性大”。有了这个结论,他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希望妻子也要有同样的思想准备,并且,还向妻子慎重承诺:“你千万不要担心,我会承受住这个考验。第一,绝不会自杀,就是人家诬我自杀,你也不要相信;第二,不是我的问题,不管给我多大的压力或诱惑,决不承认;第三,更不会去诬陷别人,不卖友求荣。”这看似短短的76个字,普普通通的几句话,却句句擲地有声!其內容关乎亲情,关孚信仰、关孚尊严、关孚道徳!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李致对于进入“牛棚”就可以说是心怀坦荡,有备无患了。
就在李致向妻子作了交代,并隐藏着内心的不安,与孩子一起压抑着开怀的笑、闹声,玩了一场告别式游戏之后,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即在开了针对他的批斗会后,就被送进了南院的“牛棚”了。
世间11个月,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身陷“牛棚”监禁生活的李致来说,却是度日如年,不仅不许自由出入,关在一间屋里的“牛鬼”也不能交谈,以他的切身体会,那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精神折磨”。然而,此时,他除了接受眼前的现实而外,别无选择。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时期,无论背负什么“罪名”而身陷囹圄的人,都会产生最基本的疑问:“文革”将会怎样进行下去?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牛棚”会住多久?……诸多问题缠绕,却是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头脑一片混沌,前景一片茫然,李致也不例外。好在他是有备而来,而且心里装着“妻子的安慰”:“不管最后是什么结论,我一辈子和你在一起”。轻轻的一句话,同样是一诺值千金!还有什么能比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运动中,命运、前途未卜的情况下,与你不弃不离,生死相依可贵呢?可以说,妻子的理解和对子女、家庭事务的承担,不仅解除了李致的后顾之忧,给了他生活的力量,也成为他在“牛棚”安营扎寨最强大的精神支柱!
“文革”中,人道已丧矢、人权被剥夺、尊严受到公开的践踏,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游街和批斗。无论罪状有多么可笑,一旦被“认定”,被批斗就在劫难逃。李致在《我大声高呼口号》一文中记叙了他在批斗会上的真实情景:“我坐的是‘喷气式’,头被按得很低。尽管我一直在想我爱人再三叮嘱的‘要正确对待革命群众’,心里仍然压不住满腔怒火。……我一生(包括在旧社会十九年)没有受过这种人身侮辱。更重要的是,我认为“造反派”这些做法并不附合毛主席的指示。……然而,他们呼的全是最‘革命’的口号。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直起身子大声高呼: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口号,是在“文革”中被运用和发挥到极至的一种表达形式。在一场以绝对压倒优势针对一个人的集会上,口号会被主持者演绎得淋沥尽至,被斗者就是一个被任意践踏的对象。然而,出乎“胜利者”们的意外,李致竟然没有像其它被斗者一样,在批斗会上选择沉默和忍辱负重,反而是进行公然对抗!正是他的这一声高呼,使与会者无不惊愕万分,真是胆大妄为!这无疑激怒了“革命群众”!待众人反应过来,李致遭到的自然是加倍的拳打脚踢。但此时的他,竟是庆幸自己“未被打翻在地,”而且“丝毫不感到痛,只感到痛快。”甚至“高兴自己没有屈服。”而是用大声高呼革命口号以示对诬陷和暴力的不屈和抗议!李致的这一声高呼,让自己挺直了脊梁,呼出了士气!痛,并痛快着!
荒诞的年月,必有荒诞之事。李致笔下的“谁是母蚊子”应该是比较奇葩的一个。
他在文中说,造反派忙于“内战”的时候,南院“牛棚”的各色人等被放逐到西山农场劳动,这无疑使久被监管的“牛鬼”们大喜过望。但是,虽然“暂时丢掉了汇报、检查等各种烦恼”,然而,“郊区蚊子多,一到黄昏,听到蚊子的翁翁叫声就使人不寒而栗。二十几条壮汉集中在一间屋子,给蚊子提供了‘打牙祭’的最好时机。没有蚊烟,用扇子抵御,防不胜防”。于是,大家一起对蚊子进行声讨。李致发表了一通看法,他说:“其实,公蚊子并不咬人,只喝露水。母蚊子要产卵,需要营养,才吸人血。”殊不知,这番议论蚊子的话,竟然成为告密者的一枚子弹,导致一位自称是“老干部”的女“造反派”勃然大怒,她居然凶神恶煞地质问李致“谁是母蚊子”,一头雾水的李致恍然大悟,“忍不住在心里笑了”---原来“她把自己当作‘母蚊子’”了。此时,书本知识使局面锋回路转,李致回答:“这是知识问题。你如果不信,可以翻翻少儿出版社出的《十万个为什么?》”。然而,恼羞成怒的“母蚊子”并不善罢干休,竟强词夺理地要李致“老实交待,认真写份检查”,继而变本加历,待机报复。
一次“三秋”劳动前后,所有“牛鬼”都放假一天回家。这一天,对他来说太珍贵了!不仅可以看望妻子、儿女,还可了解母亲的情况,还有太多的话要说……,他激动地等待着那个幸福时刻的到来,丝毫没有感觉到,“母蚊子”对他变本加历的报复已悄然拉开了序幕。李致眼看着上自耀邦同志,下至各种‘阶级敌人’都放回去了,他从容地跟在队伍后面,而此时,“母蚊子”却恶意限令李致不准回家!李致无可奈何,只是忧心着,妻儿们看见“牛鬼”们全都回家了,唯独自己被留下,一定会担心自己而无辜地承受压力,因此,他难受极了。但是,在情绪极其低落的状态下,李致突然意识到,家是回不去了,可自己岂能“配合”“母蚊子”来折磨自己?于是,他调整好思路,想出对策。第二天用平静、从容的姿态洗衣服、在对着自家公用厨房的地方凉哂,他相信,到公用厨房去洗菜、做饭的妻子、女儿,一定能看到自己,一定会懂得,他没事!同时,也让在一旁偷窥的“母蚊子”看到,我好着呢!
那时,就像有一个魔鬼,把猜疑和敌意注射到了这位女“造反派”(包括那位告密者)的血液里,让她(他)的自私、怯弱、妒嫉、虚荣恶性膨胀,心理扭曲,而把人的善良、忠诚、无私、纯洁丧失殆尽,岂料,翻过这页历史,“母蚊子”事件却变成一则“文革”笑抦……
余秋雨先生曾说:“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份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
的知识份子多半就是如此。因此,他们在精神陷入极度空泛无助、人身行动失去自由的时候,就必然会为自己寻找一定的支撑来作为精神自救,读书,自然成为首选。但当时,被允许阅读、并用以改造思想、深挖根源的唯一参照读本就是《毛泽东选集》。李致在“牛棚”的十一个月里,给自己下了一味“猛药”---通读了《毛选》(一到四卷)四遍。力图从书中吸取力量,寻找希望,尽管他并不能从中预测“曙光”能在何时出现,还是觉得,“有希望总比绝望好!”后来,多亏他想到“以检查自己的文艺思想为理由,要求学习《鲁迅全集》”,这个要求居然得到“专政小组”的许可,从此,才结束了只读一种书的日子。埋头在鲁迅的书里,心中一直紧绷着的那根弦,总算是松驰了些许,一颗焦虑、疲惫的心也有了一个安放之地。他在《寻找精神支柱》这篇文章里,作了这样的叙述:“我‘天天读’鲁迅的书,真是莫大的幸福。我发自內心感谢‘专政小组’的人,并感到别有用心的人毕竟是个别的”。其实,在当时,就算你把《鲁迅全集》背得滚瓜烂熟,无论把自己的文艺思想批判得如何深刻,都是永远无法达到“专政小组”的要求和目的。灾难和阅读,只是净化了灾难者的灵魂。而值得一提的是,李致在这篇文章里,没有用笔墨去叙述那个把中华文明、经典巨著作为“四旧”而残酷摧毁的现状,却仅用一句:“我发自內心感谢‘专政小组’的人”准许他读鲁迅的著作,这不仅是对‘专政小组’给予了最温和的嘲讽,同时也折射出那个年代的真实背景。
“牛棚散记”中《小屋的灯光》我已读过多遍,感到这是李致“牛棚散记”中用情最深,也是给人印象极为深刻的一篇。在这篇文章里,一盏极为寻常的灯,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通报平安的使命,那是一盏心灯!只要阅读这篇文章,都会出于对“文革”的特殊记忆和贯性思维,而十分自然地想起“文革”中一首非常流行,且最具代表性的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可以说,这首歌在当时,几乎就是迷茫、苦困的代言词,被运用得极其广泛。身处“牛棚”的李致,应该是附合这种情怀的吧?可他却偏偏仰望的是他家小屋那盏灯!他怎么没有寻找北斗星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阅读李致的作品逐渐增多,与他的交往越来越密切之后,便越发感到,李致行文一贯直抒胸意,文字真诚、朴实、从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倘若他要是把“小屋的灯光”写成了“仰望北斗”,那就纯粹是粉饰,是矫情了!而且,也决不是李致应有的风格!身陷“牛棚”之中,能够望见自家小屋的灯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因为“文革”中,随时都有无数家庭被割断亲情,失去信任、夫妻反目、儿女背叛的悲剧在上演。显然,北斗星离他实在是太遥远、太虚无飘渺了,他没有煽情的心绪,而能够在一盏灯所点燃的希望中,鼓足活下去的勇气,远比遥望北斗要管用得多!此时,一个深深相爱并相互信任、理解的妻子,一双可爱的儿女、一个远在故乡的年迈老母,就是他的全部,他的牵挂!而这一切都维系在小屋里的那盏灯上。灯亮着,说明妻儿安在,他心里就“得到某种安宁,感到一些温暖。”就怀着希望,充滿信心,小屋的灯光一旦熄灭,恐慌便接蹱而至,妻子没在家?她会去哪里?会出什么事?因此,心里“毛焦火辣,什么事也做不成”,不仅茶饭无味,还彻夜难眠。报纸,《毛选》、乃至《鲁迅全集》统统读不进去,甚至用《新华字典》来“打卦”,猜测家里出了什么事?这些描写,不仅是最为真实的记述,同时,也还原了“牛棚”生活最私密的真象。最终,略施小计与妻子取得联系,并约定:“……一回家,马上把小屋的灯打开,免得我担心。”此时,读者与作者一起松了一口气!
立秋后,天气转凉,“牛棚”搬到有暖气的北屋平房。这一来,身子到是暖和了,而心却凉了——北屋看不见小屋的灯光,那个悄无声息、唯一心领神会的沟通方式就此中断,新一轮的不安卷土重来。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李致在洗澡间偶遇儿子,三句问话,少不更事的儿子三声回答,终于使他释然!
“小屋的灯光”,以一盏灯,投影了一个时代;以一盏灯,浓缩了一段亲情!
在李致的《终于盼到这一天》和〈我的人生〉中,除“牛棚散记”外,还有两篇文章是不可忽略的——《小萍的笑容》和《我所知道的胡耀邦》。这两篇文章并没有收入“牛棚散记”,却介乎于“牛棚”內外,从另一个则面和角度记叙和抒发了作者內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
李致一向喜欢孩子,加之又是儿童工作者,所以和同楼的孩子相处得很好,也很得孩子们喜爱,尤其是同楼的小萍姐弟。但是,“文革”初期,大字报只许贴在机关大楼内,而揭发《李致有个大阴谋》的大字被贴进食堂,因此,在大院,李致常被几个稚童追逐着、像唱童谣似的合唱:“李致,有个,大阴谋!”这些孩子以前并不认识李致。毫无疑问,此时李致心中是五味杂陈的。然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六一”儿童节到来的时候,他竟与他的小邻居小萍不期而遇。如果没有“文革”的发生,他本可以抱起她来,祝她节日快乐,但是,此刻,他却痛心地感到,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之间那种亲近、随和、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却是一道无形的屏障。就在李致不知所措的时候,小萍却极其自然和友好地给了他一个微笑,而且,这个笑容,跟过去没有任何区别。瞬间,李致分明感到一缕春风拂面,一米阳光穿胸而过,这久违的、纯真的笑容,不仅带给了他“无比的温暖”,而且让他感到“人间的良知和真情是无法摧毁的”!
以后,无论李致走到哪里,无论时间多么漫长,经历有多么痛苦,他却始终没有忘记小萍的笑容。在粉碎“四人帮”后,李致出差到北京时,曾特意去看望小萍一家,只可惜小萍姐弟出去玩了,没见着而万分遗憾。
“牛棚”生活11个月的苦难,以及一个温暖的瞬间,同样都是刻骨铭心,同样成为永不磨灭的记忆,前者为了不忘历史;后者,为了不忘感恩,那怕是对一个孩子!
能够和一代伟人胡耀邦进入“牛棚”、并同住一屋,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但是,处在那个残酷的年代,也未见得是好事。在政治、前途失去方向,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在丧失人道、人权的政治高压之下,一切职务不仅显得微不足道,而且,职务越高,也必将成为“专政”的最大对象。朝夕相处中,稍有不慎,不仅沦为“同党”,甚至招来杀身之祸。每一天都有充滿血腥的悲剧在上演,在这场空前绝后的政治大舞台上,身陷“牛棚”的人又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登场,的确是一个艰难的决择,也必然使一切有良知的人倍受煎熬。李致在《我所知道的胡耀邦》一文中,就是回顾和描述他与胡耀邦在“文革”前后,以及“牛棚”內外的一段复杂经历,那就是一种煎熬:李致一直崇敬从耀邦同志,但迫于压力,于是,在大批判高潮中,给耀邦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但最终,却为了这张大字报而悔恨不已!
煎熬就是折磨!煎熬没有皮肉之苦,却是心灵之痛!
李致进入“牛棚”之前,目睹“耀邦同志被从窗口揪出来,头被按得很低的。我不忍心看,匆忙走回家,坐在饭桌前,用手蒙住眼睛,眼泪一大串一大串地从指缝中流下来”。
可是后来,竟在“牛棚”与耀邦同志同居一室,朝夕相处。但是,当有人不滿耀邦同志早起处理痔疮影响睡眠,破口大骂时,却不敢说一句劝慰的话;同居一室,同为“牛鬼”,竟不敢借一张《北京日报》给耀邦同志看;被分配与耀邦同志单独在一个无法容纳两人一起劳动的空间,靠得那样近,也感到有亲切感,却仍然没勇气与耀邦同志有丝毫交流……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李致已到四川人民出版任职。对于四川出版工作上遇到的困难,却仍然是曾经患难与共的耀邦同志给予了精明的拨点和支持。或许,正是耀邦同志博大的胸怀,更加深了李致对自己的反思和悔恨,因此,他在本文中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回望过去,对自己进行了大胆、深刻的剖析,把自己真实地坦露在读者的面前,他说:“对耀邦同志胡乱上纲的大字报,既是我‘思想混乱’的表现,也是我人品污点的暴露。我没有顶住当时的压力,想借此划清界线,保自己。”读到此处,令人唏嘘不已,钦佩之情油然而生!“文革”中,写过大字报的人应该有亿万之众,在“文革”已成为历史的今天,居然有人能为仅仅写了一张大字报而忏悔,这是不多见的、也决不是虚伪的!
……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的荒唐狂乱,当人们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
“文革”距今已过去50年了。但是,在“牛棚散记”中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感到心潮难平、百感交结……,冯骥才先生曾著文说:“20世纪历史将以最沉重的笔墨,记载人类的两大悲剧:法西斯暴行和文革浩劫。凡是这两大劫难的亲历者,都在努力忘却它,又无法忘却它。文学家与史学家有各自不同的记载方式:史学家偏重于灾难的史实,文学家偏重于受难者的心灵”。我想,李致的《终于盼到这一天》和《李致文存:我的人生》就是他的心灵实录!在此,我仍然愿意借用冯骥才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贻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谨以此文纪念“文革”50周年!
2016年6月20日17:10完稿于老叶子书屋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