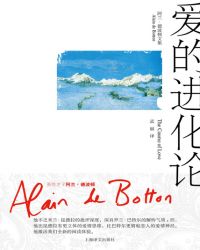第13章 爱的课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爱的进化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结婚四年后,一直在憧憬有朝一日为人父母的他们,决定不再人为阻止这种可能性。七个月后,在浴室的水槽边,他们等到了消息,验棒垫有棉片的观察窗内显现出一条淡淡的蓝线——颜色还未饱满到足以预告一个新成员的到来,它似乎离当下还有九十五年的距离;它将用一个目前令人难以置信的名号,称呼眼前这两个身着内衣的人:“我父母”。
在备战的那漫长的几个月内,他们想弄明白他们该做些什么。他们熟知自己生活的种种困难,把这视作一个机会,从细节出发,让一切从开始便走上正轨。一份星期日增刊上建议,多吃土豆皮、葡萄干、鲱鱼和核桃油,柯尔斯滕对此积极遵从,以对抗她对于发生在体内、无法掌控的一切的恐惧。不论是在开会中,还是公交车上,赴宴时还是洗衣服,她都在挂念与自己肚脐眼几毫米远的地方,有心脏瓣膜在形成,有神经元在拼接,有DNA决定下巴的形状、眼睛的颜色,个性的细微之处会有来自祖辈的遗传。她总是早早上床,便也不足为奇了。在她的人生中,她还从来没有如此关心过任何事物。
拉比经常把手放在她肚子上,做成保护的姿势。肚里正在发生的,可要比他俩聪明许多。他们知道如何做预算、预测交通流量、设计平面图,肚里的却懂得如何为自己建造一个会不停运作一个世纪之久的脑袋和心脏。
分娩前的几周,他们羡慕这外来的人儿即将迎来自己瓜熟蒂落的最后时刻。他们想象着在以后的生活中,也许在经过长途飞行后的某家国外的酒店房间里,它会像胎儿那样蜷缩起来,寻找着久违的母体羊水内的原始和平,以不受空调噪音的干扰,消除时差的影响。
历经七个小时的苦难之后,她终于到来了;他们叫她埃丝特,是取自她妈妈的一位曾祖母,第二个名字叫卡特琳,是拉比妈妈的名字。他们的眼睛没法从她身上挪开。她方方面面都那么完美,是他们看过的最漂亮的人儿;她大大的眼睛瞪着他们,似乎充满了无限智慧——仿佛她用尽前世吸收着世界的每一点智慧。她开阔的前额、精雕的手指和两只仿佛与眼睑一样柔软的小脚,将在日后无眠的漫漫长夜,以哭闹不止考验着父母的理智时,能起到镇静神经的决定性作用。
他们将她带入其中的星球,立刻便开始令他们烦恼。医院的墙是病恹恹的绿色,护士笨拙地抱着她,医生用压舌板猛戳着她例行检查;从隔壁的房间可以听到她的尖叫声和砰砰声;她一会儿太冷一会儿太热——在最初几个小时的疲惫与混乱中,她似乎一直在无休止地哭闹,哭闹声刺破了她两个绝望的侍从的心,他们无典可据以翻译她愤怒的命令。巨大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各种声音絮絮叨叨着她无法理解的内容;头顶的灯散发出猛烈的白光,她纸一般脆薄的眼睑还过于脆弱,以致无法承受;要吸住乳头,就仿佛要在肆虐的海洋风暴中抓住生命的浮标一般;说得委婉些,她是有些不舒服。在剧烈的挣扎之后,她最终在她的旧家外面睡着了,虽然肝肠寸断,但也无解,好在熟悉的呼吸声一起一伏,让她感到宽慰。
他们从未如此热切、确定地关心过任何人。她的到来,改变了他们对爱的理解。他们认识到,对于一些利害攸关的事物,他们过去了解得实在太少。
成熟,意味着承认浪漫的爱情可能只是狭隘的、也许是相当刻薄的情感生活的一个方面,它主要集中在寻找爱,而不是给予爱;是被爱而不是爱。
对年长于孩子许多倍的成人而言,孩子最终可能会意想不到地成为他们的老师;以一种全新的爱的方式,他们提供给成人——通过彻底的依赖、利己主义和脆弱性——一种高深的教育;这种爱绝不会嫉妒地要求回报,或怒气冲冲地表示悔恨;它真正的目标完全在于,另一个人的利益可以凌驾于自身利益之上。
她出生当日的清晨,护士安排另外一个新生儿家庭出院了,除了给他们两张关于疝气和免疫接种的宣传单页,没有其他任何指导或建议。普通家用电器的说明书都要比新生儿的指导更详细;世界保持着一个令人感伤的信念:对于人生的感受,一代人能理智地告知另一代人的,并无很多。
通过孩子,我们认识到,爱是一种以最纯净的形式呈现的服务。这个词已是饱含负面的含义。一种个人主义的、自我满足的文化不能轻易地把满足感与他人的需求等同起来。我们习惯以爱回报他人的付出,回报他们娱乐、吸引或安慰我们的能力。然而婴儿却一无所能。稍微大一些的孩子有时候会极为受挫地评价说,婴儿们毫无价值。其实这正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教会我们不求回报地给予,只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帮助——而我们处于施助者的位置。我们被引入的这种爱,不是基于对强者的仰慕,而是对弱者的同情,这是每一个物种共有的脆弱,它曾为我们所有,并且最终将再次为我们所有。人们总是很容易过分强调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无助的生物在此提醒我们,没有人能最终是纯粹的“自我奋斗”,我们活在债务累累的人际关系中。我们意识到,生活取决于——毫不夸张地说——爱的能力。
我们也领悟到,服务他人并不丢脸——实际恰恰相反,因为它让我们摆脱于一种令人疲惫的责任感:不断迎合自己扭曲、贪得无厌的本性。我们认识到,生活不该只为自己而活,更值得我们为之而活的,是获得一个新生命后的那份安心与殊荣。
他们擦着她的小屁屁,一次又一次——不明白自己为何以前从未清晰地理解,这确实是一个人必须为一个人所做的。他们在午夜替她温着奶瓶;她若能一气睡上超过一个小时,他们便如释重负;他们担心她打嗝的时间,并为此争吵。所有这一切,日后她都会忘记,他们也不能或不愿意告知于她。未来某天,当她内心有足够的幸福感,渴望为他人如此付出时,她的这种认识会令他们间接体验到感激之情。
她的一无所能令人提心吊胆。事事皆需学习:如何用手指绕握杯子,如何吞咽香蕉,如何在围毯上移动手抓住一把钥匙。一切都学来不易。一早上的任务也许就是搭好积木再推倒它,用叉子敲桌子,朝水坑里扔石头,把关于印度寺庙建筑结构的书从书架上抽出来,或尝尝妈妈手指的味道。一切都那么不可思议。
柯尔斯滕和拉比都未体验过这种爱和无聊夹杂的感受。他们习惯将自己的友情奠基在共同的情致之上。但令人困惑的是,埃丝特却既让他们最感无聊,也令他们最是深爱。爱与心理兼容性很少会如此疏离——然而这压根无关紧要。也许人们过于强调了与他人的“共同点”:拉比和柯尔斯滕全新地认识到,人际关系的生成,几乎不存在任何要求。依据真爱之书,任何急需援助者,皆可与我们为友。
文学作品很少有描述娱乐室和婴儿室的内容——也许是出于充分的理由。在旧小说中,奶妈们会迅速把婴儿抱走,以便秩序得以重新恢复。在纽巴图-泰伦斯小区的这间客厅里,从外在的意义而言,接连数月,不会有多少大事发生。时间似乎空洞一片,但实际上,一切生活的内容和意义都蕴含在其中。当埃丝特最终从早期的漫长黑夜中觉醒,获得连贯的意识后,她会彻底遗忘所有的细节。但它们留给她的恒久财富则是身处这个世界时最初的舒适度和信任感。埃丝特的童年将根基于较多的感官记忆,而具体事件储存则较少:被人紧搂在怀;某个特定时段内斜斜的阳光;饼干的味道和类别;地毯的纹理;夜间长时间行车时,父母那遥远而难以理解的抚慰之声,以及一种她有权利生活、有理由期待的潜在的感受。
孩子还教授了成人关于爱的其他方面:真正的爱应该以最大的慷慨之心,不断尝试着随时解读在难以对付和令人讨厌的行为之下,有着怎样的真相。
父母必须猜测哭闹、踢打、悲伤或愤怒的真实目的所在。而令这解读行为脱颖而出的——同时也令它与一般成年人的关系截然不同——是它的宽容。父母倾向于推断孩子本质上是好的——虽然可能会令他们操心或痛苦。一旦戳刺他们、让他们不舒服的钉子被准确地辨认出来,他们就会恢复到原初的纯真。当孩子哭闹时,我们不会指责他们调皮或自扮可怜,我们会想知道他们为何事惊扰;当他们咬人时,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害怕或一时心烦。我们对于各种不良影响异常敏感:饥饿会损伤复杂的消化道,而睡眠不足会令人心情不佳。
若能将这种本能哪怕些许用于处理成人的关系——同样,如果我们能透过暴躁与凶残,辨认出总掩身背后的恐惧、困惑和疲惫,这着实是善者仁心。这便是以爱的目光凝视人类的真正含义。
埃丝特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和外祖母一起度过的。在去因弗内斯的火车上,她大半程都在哭闹。等抵达外祖母带阳台的家时,她爹妈已经面色苍白、疲惫不堪。埃丝特体内有不适,可她却无法知道是什么疼、哪儿疼。她的仆从们凭感觉说她太热了。一条毯子被拿开去,一会儿又给她包回来。新主意不断冒出来:可能她渴了;也许太阳晒得她不舒服;或者电视噪音太大;要么他们用的肥皂不对;又或者床单令她过敏。显然,没有任何人会推断她只是任性或乖僻,孩子可是再好不过的。
尽管仆从们忙着又是喂牛奶,又是给她按摩背,扑爽身粉,抚摸她,给她换上不痒的衣领,一会儿扶她坐着,一会儿又躺下,还洗个澡,抱着她上下楼梯来回走,却找不到根本原因。最后,让人忧心的是,可怜的小家伙都吐了。将香蕉糙米膏吐到她崭新的亚麻裙上,那可是她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外祖母还在上面绣了“埃丝特”。然后她又立刻睡着了。周遭人们过多的关切,让她彻底被误解了,而这,绝非仅有的一次。
作为父母,对于爱,我们会有另一种领悟:对于依赖我们的人,我们对其施以控制力的多少,会相应地影响到这些任由我们处置的人儿,我们不得不谨慎待之。我们了解到一种并非有意为之、始料未及的伤害力:因为对方的古怪或不可预知、焦虑或瞬间的刺激,而令我们备受惊吓。我们必须自我训练,该应他人之需而非自己第一反应行事。野蛮人须用肉掌轻握水晶高脚杯,否则它将如秋日的枯叶一般被揉碎。
周末的清晨,柯尔斯滕尚在补觉时,拉比照看着埃丝特,他热衷扮演各种动物。起初拉比并未意识到自己的模样有多可怕。他也从未想过自己是一副巨人面孔、眼睛古怪而富有威胁性、声音充满攻击性。四脚伏地的假狮子惊恐地发现,他的小伙伴在尖叫着求助,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任凭他百般保证老爹已经赶回、可恶的老狮子已经逃走,她还是无视他,只有更温柔、更细心的妈咪(被紧急喊醒,因此对拉比毫不领情)出手才能奏效。
他意识到,在引导她领略这丰富的世界时,自己必须谨小慎微。鬼怪不能被提及,这词汇有着激发恐惧的魔力;恐龙也不适合开玩笑,特别是天黑之后;在首次提到警察、解释不同政党以及天主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关系时,他必须注意自己的描述方式……他意识到自己从未见过有人——目睹她勇敢地仰面翻身趴着,亲历她书写第一个单词的场景——像她一样毫无防备;他庄严的职责在于,绝不能提醒她自身的弱点,或利用这些弱点对付她。
虽然天性愤世嫉俗,可如今他却全然只将世界的正面展示给她。因此,政治家们都鞠躬尽瘁,科学家们正奋力攻克疾病;现在是关掉收音机的好时刻。在开车经过一些更破败的街区时,他感觉仿佛是歉疚的官员在带着外国政要参观,那些涂鸦很快会被清除;戴头罩的人们是因为高兴才大喊大叫,这个时节的树很漂亮……陪着这位小乘客,令他为自己的成年同胞们感到羞愧。
至于他自己的本性,也得被净化和简化。在家他就是“爸爸”,不为工作或财务状况焦虑,热爱冰淇淋,是个傻大个儿,最爱拉着他的小姑娘转圈圈,然后让她骑在脖子上。他太爱埃丝特,以至于不敢在她面前丝毫流露自己的焦虑。爱她,就意味着奋力获得勇气,全然摆脱常态的自己。
故而,在埃丝特幼年时,世界呈现着一派稳固安定,日后她会必然感受到这稳固安定的不复存在;而这,实则全仰仗她的双亲对世界不懈而审慎的编辑。惟有尚未领悟生活变换无穷、世事无常的人儿,才幻想其固若金汤、地久天长。譬如,于她而言,纽巴图-泰伦斯的房屋天然便是“家”,具备这词该有的一切永恒关联,它丝毫不只是一座基于预算而遴选的极其普通的屋子。在埃丝特存在于世这件事上,也充满了极度的偶然性。如果柯尔斯滕与拉比人生的打开方式稍有不同,那么如今已然凝结在他们女儿身上的一系列不可磨灭的身体特征和个性特点,便会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如果当初其中一人取消晚餐,或已名花有主,又或太害羞而不敢讨要电话号码,彼此的基因便永不可能结合,她便也永无可能降生于世。
埃丝特的房间铺有一张米色的羊毛地毯;她可以在上面连坐几个小时,用纸剪着各种形状的动物,或在晴朗的午后,透过房间窗户看着外面的天空;这地毯因为她最初的爬行练习,会留给她久远的感受;她会终身记住它独特的气味和质地。然而,对她父母而言,它并非注定是这个家庭坚不可摧的图腾:实际上,它是在埃丝特出生前几周才预订的,是从商业街(就在公交站旁边)的一个不太可靠的本地销售员那里匆忙购买的,之后没多久他就停业了。这地球的新生命之所以令人安心,部分源于他们尚不能理解大千万物精细的本性。
备受呵护的孩子,树立着富有挑战的先例。舐犊之爱就其本质而言,会掩藏起付出这份爱背后的努力。它不让爱的接受者体验到施予者的复杂性与悲伤——以及为了这份爱,父母牺牲了自己多少的兴趣、社交和事业。它以无限的慷慨,一度将这小人儿置于宇宙的中心——给他或她以力量,以便有一天他们可以接受现实世界的真实模样和令人无措的忧伤。
这是爱丁堡一个典型的夜晚,当拉比和柯尔斯滕终于安顿好埃丝特,给她围上熨得笔挺的口水巾、穿上舒适的婴儿服、卧室的婴儿监视器一片寂静后,这两位极度耐心有爱的护理人撤退到他们的角落,看看电视,翻翻过期的周日期刊。如果孩子奇迹般地能观察领悟到这些,一定震惊于他们这行为模式的快速转换。拉比和柯尔斯滕一连数小时给予孩子的那些温柔、纵容的言语,被挖苦、报复和吹毛求疵所取代。爱的辛劳已令他们筋疲力尽。他们再无什么可以给予彼此。他们体内那个疲乏的孩子正恼怒于自己已是支离破碎、被忽略多时。
如果成年的我们,初次建立人脉关系时,潜心找寻一类人,他们能给予我们幼年时便已领略的包罗万象的无私之爱,这不足为奇;如果我们最终倍感受挫,并极度苦恼于此爱之难求,人们并非了解或在意我们的需求,以致不能适度施以援手,这同样不会出人意料。我们可能因自身需求不为他人本能地感知而恼怒,并予以责怪,可能不时从一段关系移至另一段,也可能谴责某一次性爱肤浅菲薄。直到某天,我们终结自己这有悖现实的追寻,终得成熟达观,并意识到解脱于这种企盼的惟一路径,也许便是不再索求完美之爱,并接受它并非无处不在,继而不再戒心重重地算计回报几率,而开始给予爱。 爱的进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