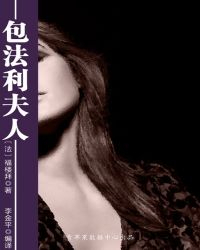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包法利夫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修女们原先对她的感召力很看好,如今非常惊讶地发现鲁奥小姐似乎完全摆脱了她们的关怀。说实在的,她们为她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教她日课经、静修、作九日祈祷,给她讲道,谆谆教诲,要她崇敬圣贤和殉道者,善言规劝,应该淡泊物欲,寻求灵魂的升华,她却像扯紧缰绳的奔马,猛一停蹄,马嚼子掉了下来。这个人的思想太现实化了。她爱教堂是因为教堂里的鲜花,她爱音乐是因为抒情的歌词,她爱文学是因为里面有情欲的刺激,在信仰的旨意前,她作出反抗,同样,她对修女院的戒律也越来越反感,因为这种戒律制约了她的肉体上的要求。所以,当她父亲来接她出院的时候,大家并不依恋她。院长嬷嬷甚至认为在最后的那段时间里,她已不把修女院当回事了。
爱玛回到家里后,起初还喜欢对仆人发号施令,接着就厌倦了农村生活,怀念起修女院来。当夏尔第一次去贝尔托的时候,她正自觉得非常失望,因为一成不变的生活没有任何乐趣。
然而,因某种新的处境引起的不安,或者是这个男人的出现给予的刺激就足以使她相信自己终于拥有了这种神奇的感情。在这之前,爱情一直像一朵玫瑰绽放在绚丽的诗意盎然的花园中。可是现在,她实在无法把这种平静的生活与她曾梦寐以求的幸福联系在一起。
七
有时,她还想,现在这段时光应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呢,这就是所谓的蜜月呀。为了好好品尝这柔情蜜意,无疑应该到那些名胜的地方去,刚行夫妇之实的人们能在那里领略到更甜美的浪漫。在驿车里,蓝色的丝帘遮掩下,慢慢地爬着陡峭的坡道,听着马车夫的歌声伴随着羊群叮咚的铃铛声和沉闷的瀑布喧响回荡在山间。傍晚,在海湾里面临汹涌的波涛呼吸柠檬树的芳香,然后,夜幕降临,在别墅平台上,他们二人手指交叉握在一起,望着满天繁星,为未来制订计划。她觉得世上应有专能生产幸福的地方,就像只能在某些地方生长好奇花异草。她渴望能在瑞士的山区木屋凭栏或者把自己的愁绪锁进苏格兰的村舍别墅;渴望能有这样一个丈夫,他身穿黑丝绒大燕尾礼服,脚蹬软皮皮靴,头戴一顶尖尖的帽子,手上戴着长筒手套。
也许她想找个倾吐心曲。可是,像变幻莫测的云,飞旋无形的风那样不可捉摸的苦恼,叫她怎么诉说?因此她是有苦说不出。
然而,如查夏尔愿意倾听她的衷肠,如果他想到了该听听她心里的想法,如果他的目光,即使只有过那么一次,接触了她的心灵,她觉得,许多话就会脱口而出。如同墙边的那行果树,手一放上去,果子就会雨点般的掉下来。虽然他们空间上越来越贴近了,心灵上的距离却越来越大。
夏尔的谈吐平淡呆板,没有独特的风格和见解。他常说,在卢昂的时候,他从没想到过,去看看巴黎名角的演出。他不会游泳,不会击剑,不会打枪。有一天,她在小说里读到一个马术用语,请教他,他解释不清楚。
一个男子汉,本来应该世面广阔,精通多种技艺,能引导你领会爱情的力量,细细品味生活的乐趣,深入种种奥秘,一问三不知行吗?可这一位竟实在帮不了你什么,因为他一概不和,什么都不想知道。他以为她很幸福,岂知她之所以怨他,正是因为这种如铁石般的平静,心安理得的愚钝,甚至还因为她给予他的幸福。
有时她作画,夏尔就站在旁边望着她俯身在画板上,这对他是莫大的乐趣,他眨着眼睛,仿佛能把她的作品看得更清楚些,或者在大拇指上把面包心搓成一个个小圆球供她擦画。当她弹钢琴时,她的指头弹得越快,他也越佩服。她稳稳地叩打每一个琴键,从高音到低音,一个接一个地把整个键盘叩打一遍,这架旧乐器的钢弦本来就已七歪八扭,以经受她这一番折腾,窗子要是开着的话,声音一直可以传到村外。执达员的文书,手拿着公文,光着脑袋,趿着便鞋走在大路上,常常闻声停步,侧耳啼听。
而且,爱玛善于治家。她给病人发去索要出诊费的账单,信上的措辞却非常婉转,看上去竟不像是来催账的。星期天有邻居来家里吃饭,她总有办法端上一桌像模像样的菜,例如在葡萄叶上高高地堆起意大利李子,把几罐子果酱倒在一个碟子上,她还说该去买些漱口盅,让大家漱了口再吃水果甜食。这么一来,人们对包法利更是刮目相看了。
夏尔也觉得自己越来越了不起,因为他有这样的贤内助。他把爱玛的两小幅铅笔画,配上宽阔的画框,穿上长长的绿绳子,挂在客厅里,高悬在糊墙纸上,自豪地让人欣赏。弥撒完后,大家总能看到他趿着漂亮的绒绣拖鞋,站在门口。
他晚上10点钟回家,有时12点。一回家就要吃的,这时女佣已经睡了,总是由爱玛伺候他。她帮他脱掉礼服,吃饭的时候好自在一些。他把他遇上的人,去过的村子,开过的药方娓娓道来,感到很得意,他吃掉剩下的洋葱烩牛肉,刮去奶酪上长了霉的奶皮,啃掉一个苹果,喝掉大肚瓶里的酒,就上床仰卧着,然后,鼾声大作。
他向来都惯于戴布睡帽睡觉,现在用包头布,耳朵上总系不住。所以早上醒来头发乱蓬蓬地搭在脸上,加上枕头带子系的结晚上松开了,弄得头发上沾了一层白绒。他总是穿着那双结实的皮靴,靴面上有两条很粗的皱褶,往上斜挑到脚踝,而鞋面的其余部分却依然绷得很直。他总说:“这在乡下算不错了。”
他母亲提倡他这种节俭的做法。她像从前一样,家里出了芝麻点小事就跑来看儿子,然而老太太似乎早就料定跟儿媳妇难相处。她觉得媳妇办事大手大脚,很不符合他们的经济状况,用木柴、食糖、蜡烛非得像大户人家似的,灶下烧的炭火够做25个菜呢!她整理大衣柜里的衣服,肉店送肉来的时候她叮嘱媳妇看着点儿,别上人家的当。爱玛谨领教导,老太太更是诲人不倦;就听到她们口口声声的“我的女儿”和“我的母亲”,两个人的嘴角都在抽搐,和和美美的话语都是用气得发抖的声音说出来的。
第一个儿媳妇在的时候,婆婆觉得儿子还是偏向自己的;而现在,夏尔爱爱玛,讨了老婆忘了娘,这是对本该属她所有的情感的剥夺。她默默地观望着儿子的幸福,心里难受。她重提往事让儿子别忘了老人含辛茹苦为他作出的牺牲,与爱玛的虚应故事相比较,说明他倾心相爱是不公平的。
夏尔无言以对。他孝敬老母,却又心疼娇妻。他觉得左右为难。老太太走后,他胆怯地试着投石问路,把母亲批评一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时说过的原话照搬给爱玛听。爱玛只消一句话就把他打发到病人那儿去了。
不过,爱玛从她所相信的理论出发,还是愿意表现出自己是爱他的。月下花前,她低吟着以前背下来的激情飞扬的诗句,用咏叹的声调唱着哀曲。可唱完后,她认为自己一如既往地缺乏激情,而夏尔对她依旧无动于衷,没有更加爱她。
就这样,当她撞击他的心灵,却打不出一点火星,加之她也无法理解自己感受不到的感情,也无法相信任何不是以惯常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后,她毋庸置疑夏尔的爱情已止步于此了。爱的表露已成为一种习惯,定时地吻她一下,同其他习惯没什么两样,皆在预料之中。
包法利先生治好过一个猎场看守的肺炎,这个人送给夫人一条意大利猎兔犬;爱玛带着小狗出去散心,单独待一会儿,换换环境。
她一直走到巴纳维尔的那座山毛榉林子,走到田野那边的一堵墙,墙角上的废屋边。在深深的界沟里,杂草丛中,长着又细又高、叶边如刃的芦苇。
她先环顾了一番,看看与上次来时有什么不同,看到毛地黄和野萝卜还长在老地方,那些大石头四周仍是一丛丛的野荨麻,沿着废屋的三扇窗子还是那一片片的地衣,而百叶窗一直关着,腐朽的木屑散落到锈蚀的铁栏上。起初她的思绪任意地飘荡,恰似她那条猎兔犬,在田野里转着圈,跟在黄色的蝴蝶后面叫唤,叼着一朵麦田边的丽春花追赶鼩鼱。接着,她的想法渐渐地明确起来,她坐在草地上,用伞尖轻轻地拨拉着,扪心自问:
“天啊,我为什么要结婚呀?”她在想,倘若在另一种巧合下,她是否会遇上另一个男人呢?于是,她开始想入非非,想像那些可能发生而并不存在的事情,想像另一种生活,想像那个陌生的丈夫。他,当然与众不同,应是才貌双全,出类拔萃,富有魅力的,就像她修女院的老同学们所嫁的那种男人。她们现在在干什么呢?在城里,有马路的喧嚣声,剧院的嘈杂和舞会的灯光,她们过着随心所欲、尽情享乐的日子。可她呢?她的生活却是凄冷的,厌倦。这只毒蜘蛛,在黑暗中默默地结着网,牢牢地缚住她的心。她忆起当初发奖的日子,她登上主席台去领她的小花冠。她梳着辫子,穿着白袍和普鲁涅拉斜纹薄呢镂空鞋,那么文静可爱的模样,她回座位上去的时候,男宾们都弯下腰来祝贺她。马车挤满了一院子,人们在门口向她道别,音乐老师夹着提琴匣经过时还跟她打了招呼。这一切变得多么遥远!遥远的过去啊!
她叫唤小猎兔狗佳利,把它夹在两腿间,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脑袋,对它说:
“来吧,亲亲女主人,你才是无忧无虑呢!”身体细长的小狗慢慢张开嘴巴打个呵欠,爱玛发现它也是一脸愁容,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大声和它说话,其实是自我安慰。
有时,从海上刮来刮来阵阵狂风,一下子刮遍科州,给科州整个高原、直至最远的田野带来清新的咸味。灯心草倒伏在地,呼呼作响,山毛榉叶子嗖嗖地迅速抖动,而树梢摇曳不止,继续它们无休的怨诉。爱玛用披巾裹紧肩头,站起身来。
林荫道上,树叶折射下来的绿光照在低矮的苔藓上,她踩着苔藓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夕阳落山,枝丫间的天空红彤彤的,高矮粗细相当的树干笔挺地矗立着,宛若棕色的廊柱,映衬在金色的背景上。爱玛怕了,她叫唤佳利,急急转身,走大路返回托斯特,倒在软椅上,整个晚上,她都沉默着。
然而,九月下旬,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她受到伏毕萨安德维利埃侯爵家的邀请。
侯爵在王朝复辟时期当过国务大臣,目前正伺机重返政界,一直在为竞选众议员作准备。冬天,他把许多木柴分发给大家,省议会一开会,他就要激昂慷慨地陈述一番,要求为本地区修建几条公路。大热天时,他长过一个口疮,是夏尔用柳叶刀把它割掉后奇迹般地痊愈了。他派往托斯特去送医疗费的差使晚上回去说,医生小园里的樱桃长得极好。而伏毕萨的樱桃树却总长不好,侯爵先生找包法利要些枝条做扦插。他认为自己应该亲自上门致谢,于是就看到爱玛,觉得她身姿袅娜,而行起礼来也不俗。他认为邀请这对年轻夫妇到城堡里来算不上是过分的屈尊俯就,也没什么不合适。
就这样,一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钟,包法利夫妇就坐着他们的双轮马车前往伏毕萨,他们把一个大箱子捆在车座后面,一只帽匣放在挡板上,另外还有一只纸盒,放在包法利的两只脚之间。
天黑时他们到达那里,花园里开始点起灯笼,给来往的马车照明。
八
意大利式的城堡是最近建成的,两翼向前突出,三道石阶向三面展开,通向一块极大的草坪,草坪上有几棵参天大树,树与树之间隔一定距离,几头奶牛在树丛间吃草;而细沙路两侧,是用灌木编起的路篱,杜鹃花、山梅花和绣球花的花簇叶丛垂落到细沙路曲折的弧线上。小河在桥下流淌着,雾霭中依稀可见一些茅屋,散落在牧场上,周围是两座小丘,平缓的坡面上覆盖着树木,树丛后面有两排平行的房屋,那是从旧城堡中保留下来的车库和马厩。
夏尔的马车在中间那道石阶前刚停下,就有几名仆人跑出来,侯爵迎上前,挽着医生夫人走进门厅。
门厅很高,地上铺着大理石方砖,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那里回荡。迎面一道笔直的楼梯,左边朝向园子的回廊通往台球厅,一到厅门口就能听到象牙球连续相撞的声音。爱玛穿过台球厅前往客厅,她看到有几个神情严肃的男人围着球台,他们的领结打得高高的,个个佩带勋章,神情默默地推动球杆。深色的细木护壁板上挂着几个巨大的镀金镜框,每幅画像的下沿都用黑色的粗体字标出姓名。爱玛看到有:“让一安托万·德·安德维利埃,德·伊夫邦维尔,伏毕萨伯爵兼弗雷斯奈男爵,1587年10月20日牺牲于库特拉战役。”在另一幅的下沿是:“让一安托万一亨利一居伊,德·安德维利埃,德·拉·伏毕萨,法国海军司令,圣米歇尔骑士团骑士,1692年5月29日于胡格一圣瓦战役负伤,1693年1月23日于伏毕萨辞世。”其他的就看得模糊了,因为灯光被聚集在球台绿色的毡子上,使房里黑影浮动。灯光把挂着的画幅照成褐色,照在画幅上油彩断裂的地方,现出细细的纹路,在这些镶着金边的发黑的巨幅画像上,有些部位显得比较明亮:苍白的前额,两只凝神的眼睛,披落到红礼服肩头上扑粉的假发,或者在滚圆的小腿肚上方吊袜带的纽扣。
侯爵打开客厅门,一位贵妇人(正是侯爵夫人本人)站起身来,前来迎接爱玛,让她坐在身边的椭圆形双人沙发上。她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好像熟人一般。侯爵夫人大约四十岁,肩头很美,鹰钩鼻,说话的音调拖得长长的,那晚在她栗色的头发上只搭着一条镂空花边头巾,垂落背后呈三角形。一个年轻的金发女郎坐在她身边的一张高靠背椅子上。男士们在礼服翻领的饰孔上插一朵小花,围着壁炉和夫人们聊天。 包法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