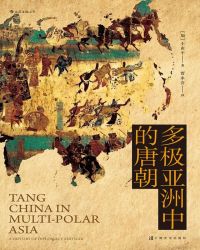骁勇善战的突厥人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鵽是一种羽毛淡黄的鸟,尾分叉,爪似鼠但无后趾,如鸽子一般大小。它们成群结队而飞,发出尖锐的鸣叫,严冬时南徙避寒,春暖后则返回北方沙漠栖息地。 注释标题 慧琳:《一切经音义》,1737年本,卷73,5页下;卷99,3页上。关于鵽,见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台北:大化书局,1982年,卷10,2649页;许慎:《说文解字》,《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卷4上,8页下;丁度:《集韵》,693、694页;郝懿行:《尔雅郭注义疏》,卷5下,18页上—下。据郝懿行,鵽也被称为“沙鸡”。对鵽的相关讨论,见蔡鸿生:《突厥方物志》,《中外交流史事考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158—159页。 鵽虽其貌不扬,却引起了素来严谨、认真的唐朝史官的注意。《旧唐书·五行志》通常只记录和阐释蕴含政治先兆的自然现象,却有关于鵽的记载。 注释标题 关于《旧唐书·五行志》的编撰和内容,见Denis C. Twitchett,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Cambridge,1992),pp. 223—224。 史官称鵽为“突厥雀”,认为鵽鸟南飞是预示着突厥即将来犯的凶兆。史料记载:“调露元年(676),突厥温傅等未叛时,有鸣鵽群飞入塞,相继蔽野,边人相惊曰:‘突厥雀南飞,突厥犯塞之兆也。’”随后,史官又记下了鵽鸟可怖的死相:“至二年(677)正月,还复北飞,至灵夏已北,悉坠地而死,视之,皆无头。” 注释标题 《旧唐书》,卷37,1368页。《宋史·五行志》也有关于鵽的记载,见脱脱编撰:《宋史》,卷64,1409页;《新唐书》,卷215上,6043页。关于“突厥雀”,见李昉:《太平广记》,卷139,1009页。在十七世纪的中国,也有一个类似的有关沙鸡的故事,见Timothy Brook,Vermeer’s Hat(New York,2007),p. 121,p. 137。
其实,鵽并不是什么邪恶之物,唐人甚至以其为美味佳肴。 注释标题 慧琳:《一切经音义》,1737年本,卷73,5页下。 无辜的鵽鸟和好战的突厥之间有如此令人不快的联系纯属不幸的巧合——鵽鸟大概在黄河结冰时南迁,而突厥恰好也在此时在黄河北岸的寺庙祭酹求福,厉兵秣马,准备渡河攻唐。 注释标题 《通典》,卷198,1074页。对突厥起源这一复杂问题的相关考察,见Peter B. Golden,“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Turk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Turkic Peoples”,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ed. Victor H. Mair(Honolulu,2006),pp. 138—143;Yamada Nobuo,“The Original Turkish Homeland”,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9(1985),pp. 243—246;Peter A. Boodberg,“Three Notes on the T’u-chüeh Turks”,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ed. Alvin P. Cohen(Berkeley,1979),pp. 350—360。
●●●
骁勇善战的突厥人
如果说鵽鸟南飞是突厥进攻在即的预兆,品种优良的战马则是突厥人骁勇善战的标志。初唐君臣皆是骑马好手,经常对突厥马赞叹不已,他们对突厥马绘声绘色的描述,使我们得以一窥这些非凡之物。史料记载:“突厥马技艺绝伦,筋骨合度,其能致远,田猎之用无比。”太宗同样钟爱突厥马。647年,骨利干(部落名)遣使朝贡,献良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被挑选出来献给太宗。太宗对这些马极为惊叹,称之为“十骥”,并为每匹马赐名。他在欣喜之余,更以笔墨详细描述了这些“特异常伦”的马匹的风姿,称它们骨骼强壮,眼圆如镜,头方如砖,腿长如鹿,颈细如凤,腹小而平,鼻孔粗大,即便在全速奔驰时仍然呼吸自如。正是这样的骏马使突厥能闪击敌人,并在对方组织反击之前就早早撤离。
突厥的另一项优势是“工于铁作”,他们制造的铁兵器久负盛名。突厥人用黠戛斯(今吉尔吉斯斯坦)进献的铁打造刀剑、匕首、长矛、箭镞、盔甲和鞍具部件。黠戛斯是突厥的附属部落,控制着富含金、锡、铁等矿藏的辽阔地域,在有些地方,矿脉非常接近地表,乃至暴雨冲刷之后就露出地面。黠戛斯人对大自然的这种特殊恩惠感激不尽,称之为“天雨铁”,并把铁作为贡献给宗主国的重要物品。在突厥制造的各种箭头中,“鸣镝”为突厥首领专用。这种响箭的设计别具一格,箭头有三个三角形平面,附有带孔的骨制圆珠。箭射出后,空气从珠孔中穿过,发出尖锐的声音,以此引导麾下的突厥骑兵攻击他们的首领意图打击的目标。因此,鸣镝是突厥首领在战场或狩猎场上发号施令的工具。
突厥是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独特,狩猎既是其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军事活动。突厥人通过狩猎磨炼了各种军事技能,如调遣移动队伍、协同攻击、骑术、射术等。不仅如此,他们经常佯装狩猎,实则发动军事进攻。他们如此娴熟地将狩猎活动转变成军事进攻,往往使习于定居生活的唐朝军民猝不及防。七世纪二十年代末,唐朝僧人玄奘在前往印度途中经过中亚地区的素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附近)时,目睹了一次这样的狩猎活动。玄奘尽管博学多识,却没能察觉其背后的军事意义。他和随行僧人似乎只注意到了突厥可汗古怪的发型,华丽的绸缎长袍,长长的头饰,以及大批身着皮毛、毡衣的骑兵,所以仅仅一带而过地记载道:“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
玄奘目睹的其实正是突厥军队的基本阵型。这种阵型形同一支三叉戟,突厥可汗亲率中军,突厥各部首领及其麾下骑兵分别为左右翼,另有一支先头部队。作战时,先头部队发起第一波进攻,左右两翼逐渐向中路靠拢,最后与中路会师完成作战。突厥首领在运用这一战术时非常灵活。在全面快速的进攻中,如果首领断定战况对本方不利,就会当机立断,马上率部撤离。高祖曾对此评价道:“(在军事行动中,突厥人)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胜止求财,败无惭色。”
突厥这种独特的战术源于其游牧生活方式,以及可汗组织的联合军事行动所具有的见机而作、便宜行事的特点。突厥人不像唐人那样惯于定居,他们的流动性非常高,既不执着于拥有自己固定的领土和边界,对他人的类似意愿也不屑一顾。突厥各部驰骋于草原之上,为了生存而争夺水源和牧场。他们的本性就是在移动中寻求优势,攫取利益。他们之所以会联合起来突袭唐朝的边境城镇,也是受这种本性的驱使。这种由突厥可汗组织的袭击,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各部落对唐朝器物的需求。从本质上说,它是突厥统治者要求周边部落首领协同作战,以“中央”政治领袖的身份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手段。然而,对唐朝的侵扰实际上是把双刃剑。一场失败的突袭将导致参与部落折兵损将,空手而归,突袭的组织者也会反受其害。它会削弱可汗的权力基础,威胁其领导地位,甚至会引发突厥其他部落首领对汗位的野心,招致激烈而血腥的争斗。初唐统治者很快意识到:突厥攻击唐朝意不在开疆扩土,而在敛财劫物;突厥政体缺乏有效的机制确保附属部落首领的政治忠诚,难以对他们实行集中控制;此外,为阻止突厥迫在眉睫的进攻或潜在的威胁,军事行动并不总是可行或最佳的方式,解决此类问题往往有事半功倍的办法——政治操纵。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初唐统治者甚至在建立自己的王朝之前,就发展出了一套对付强敌突厥的柔性策略。他们会仔细评估自身与突厥的相对实力,当突厥实力更强时,他们或是向对方献上大量金银财宝,或是在突厥各可汗之间制造不和,加深本来就已经存在的矛盾;而当内乱或自然灾害大大削弱了突厥的力量时,唐朝就趁机出兵一举摧毁了突厥汗国。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