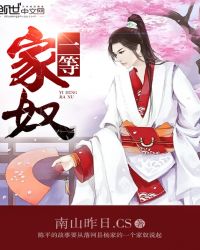三 水夜妖娆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妃子血(全二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破晓前,舱门被打开,徐靖未步入,见我二人情景,面色更加难看。被子被扯掉,我与花重分别被徐靖未和小鲁公公拉起。我一声不吭,花重则问:“王爷找到可攀的岩壁了?”
徐靖未拉我到床前,粗鲁地扯出左荃珠身下的被单,撕成长条。在小鲁公公的协助下,我被绑在徐靖未身后,如此贴近他,又令我反胃。他反手抚我后背,沉声问:“本王就这么令你讨厌?”
我不答,瞅着花重自如地爬上小鲁公公后背。他倒不用绑,我却被捆了。
船继续往黄围渡口行驶,徐靖未带着我及一行十一人,跃身攀上陡峭的山壁。我不得不抓着他的后背心,挡住胸口的碰撞。徐靖未鼻哼一声,有条不紊地指抓山岩,一步步带我往上。他攀上丈余后,我恍然发现,他选的竟是蛮申江水域最陡峭的山壁,再看一旁花重,这人不知什么时候闭上双目,在小鲁公公身上休息了。仔细看,我又发现小鲁公公不仅身手好,而且他在攀爬换手时,总有一只手距离花重身子很近,难怪花重如此大胆,原来他早知小鲁是不会叫他掉下去的。
“你还有闲情东张西望?莫非想看昌帝会不会突然出现,好把你救下?”徐靖未冷冷问,随着他的问语,他身子猛然往上一蹿,急停后,我因势,头撞他肩上。
“身上一点肉都没,全是骨头……”他叹了声,又继续往上。我双手揪住他衣裳,几乎把衣裳抓破。
“你究竟哪里好,本王现在很后悔。”他稳健有力地抓住山壁,灵活地又上一步。我忽然觉得他并非一个色令智昏的男人,至少他现在后悔了。
过了片刻后,我道:“我也不知道。”
他笑道:“如果现在我把你丢下去,结果会如何?”
我平声道:“你可以试一下。”
他不笑了,沉声问:“南屏山下,你为何不拒绝与我同行?”
我沉默。山风吹起我的鬓发,第一缕阳光斜射,秋日的山景很优美。
徐靖未攀上山顶,解开我身上绑带,打横抱起我,施展身法,纵身向前。小鲁背着仿佛沉睡的花重,紧随而上。
我心下焦急。左荃珠死前暴露了船行方位,西日昌应该知晓,但徐靖未沿途又改了山道,带我到了南越峻岭,越往南越内里走,我被救回的概率越小。
我摸了摸胸口,笛子和簪子都在。笛子我倒是能吹,只是我并非惯常使笛的叶少游,且只有一丝游离的气劲,想要催眠准武圣谈何容易?簪子是花重给我护身的,但小小的一枚簪子,大约只能杀花重和我自己。
半个时辰过去后,我稍觉意外,徐靖未没有走直线山路回南越内里,他一直率众迂回前行,显见山林里不安全。
小鲁公公虽然修为不浅,但个头矮小体力不足,花重换到了另一人肩上。一直沉睡的花重睁开了眼,对我诡异一笑。我心下顿时有了底,只是看看徐靖未,丝毫没有放手换人的打算,他抱得紧着。
察觉到我的反应,徐靖未低头望我,我立刻别转脸去,他便在我腿上加了份握力,我微微一颤,他又松了力。
“你这个女人……”徐靖未低沉道,“别想了,我知道花先生给了你笛子,但你没机会吹笛子引大杲人来!”
我不发一声,低头等着。
徐靖未一行人中,走在队伍最前端的青衣侍卫,应该是位高手。他停下身法,所有人都停下来了。
“我到前面去看一下,请王爷在此等候。”
徐靖未一点头,青衣侍卫飞身而去。我看在眼里,惊在心底,此人的身法不在林季真之下。
我被徐靖未放下,在他怀中不觉着什么,落地后一阵眩晕。
“你怎么了?”徐靖未扶住我的后背。
我吸了口气,往前一步离开他的手,而后道:“没吃早饭而已。”
徐靖未当即问众人:“谁身上带有干粮?”
我连忙道:“不用了,也吃不下。”
徐靖未凝视我道:“你还真难伺候。”
我脚步发软,走向花重,却被徐靖未拉住,“与他说了一晚上话还不够吗?”
我叹了声道:“那让我坐下吧!”
徐靖未松开我,我坐到了地上。徐靖未笔直地站在我面前,低声道:“这会儿倒有几分江湖儿女的味道。”
我不搭腔,就连乞丐我都当过,哪里会在乎地上干净或脏,哪里会在乎所谓风度。
青衣侍卫很快回来了,带回淡淡的血腥味。
“王爷,前面埋伏着不少大杲人,但他们动静太大,我发现了驻守西部的陈留王的手下,不过那人已经死了。”
“哦,陈留王?”徐靖未思索片刻后道,“不去理他,我们走自己的路。”
我被徐靖未拉起,这时候,一侍卫对小鲁公公道:“还是让我来背花先生吧,公公省点体力。”
小鲁公公道声好,拉着我的徐靖未却喊了声:“王二!”
正说话的侍卫一惊,青衣侍卫已无声站到了他后背,一把匕首捅了进去。
“花先生,不要当本王什么都不知道。”徐靖未冷冷道。
我望花重,他面上依然平静,即便王二拔出了匕首,那侍卫倒在他脚下,他的表情也丝毫未变。
“走!”徐靖未下令。
我在他怀中投眼小鲁公公背上的花重,徐靖未扳过我的脸,“别看了,他现在自身难保,南越第一谋士又如何?”
我盯着徐靖未的眼,仿佛第一次认识他。
徐靖未却不看我,而换了平声道:“回南越后,我一样会宠你。”
我收回目光,心下道:那不可能。
王二带众人行走的多是偏僻小道,甚至穿行于无道的杂草之间。我暗自思索,花重那边显然不可靠了,就算他有人安插在靖王一行人中,能获救的也只有他自己。
“王爷,准备迎战。”王二忽然开口,但他的脚步不停,身法不乱。一众人亮出了武器,只有徐靖未和小鲁带着人未动。
我抓着徐靖未的衣襟,扭身望去,青黄的山野间,风乱草惊。王二率先掠步,那一手草上飞的轻身功夫兼备灵动和敏捷。一点黑芒从王二身旁突现,跟着是一团血雾喷散,一位隐藏草丛的武者被王二击毙。这人一死,附近区域隐伏的黑衣武者不再按捺,纷纷跃出与靖王的手下短兵相接。
我看了几眼后,别转脸去,不忍再顾,这些人的下场只有一个死字。王二就像一把尖刀,所向披靡杀开了一条血路。并非这些武者修为不高,而是他们的对手是王二。王二的动作干净利落,比起当日林季真也不遑多让。
黑衣人溃败,四散逃亡,约二十几位黑衣武者留尸山野。徐靖未带我从容穿过,他冷笑一声,得意的话还未出口,就改了面色。
“花重呢?”
王二飞转回身,在一地尸体中挑出了小鲁公公。
徐靖未咬牙道:“该死!”
花重与小鲁公公缀在队伍末梢,王二在前打头,徐靖未带着我夹在当中,当双方人激战,花重趁机跑了。
徐靖未铁青着脸,抓我的力量不自觉大了一分。他是明白人,这些黑衣武者的目标其实不是我,是花重,或者说这是第一步,先把花重救出来。
我摇晃了下身子,徐靖未这次却抓得更紧,“都是你这个女人!”
我轻哼一声,“我好生待在皇宫里,你非要抓我出来,与我何干?”
徐靖未郁结,手中力道松了,我也松了口气。他又继续上路,行进加速。
失去了花重对徐靖未的打击极大,一个冷酷的念头逐渐浮上我心头,换了我是西日昌,在花重与我之间,肯定先选择前者,若不得已,一定要抛弃花重,宁可先杀了他。
我轻轻摇了下头,徐靖未冷冷地道:“如果刚才那些人是昌帝安排的,那你已经被舍弃了。”
我叹道:“你若有机会当面问他,就会知道答案。”
我想西日昌一定会给他讲一个故事。故事可能信手拈来,无非类似妻儿老母同时掉入水中,先救哪一个。西日昌很会玩这套,恩情、道义放两旁,他只选择顺势而为。若刚才那些黑衣人是他安排的,那无疑做得很正确,先捞回容易营救的花重,再图后事。
可我还是感叹,西日昌、花重以及徐靖未都是冷酷之人。那些黑衣人包括被王二所杀的侍卫,在他们眼里,都是行事的必然工具。相比他们三人,我虽也手染血腥,却远远不如。
又路经两处埋伏,埋伏者武力更高强,很精彩的死斗,但我失了兴趣观看。徐靖未周身散发着杀气和血腥味,他的气味困着我,令我神智恍惚,眩晕和困顿一波波袭来。
“醒醒!”徐靖未摇晃着我,我勉力撑开双眼,仿似他的手下也减员了。
王二上前一摸我脉搏,沉声道:“她病了。”
“她不是一直病着吗?”
王二道:“昨晚还是着凉了……”
徐靖未二话不说,脱下外衣包住了我。
王二道:“这当头千万不能让她死了,需要尽快找医师医治她!”
徐靖未重又抱起我道:“往陈留王驻地去!”
我迷糊地被他搂在怀中,还是很讨厌他的气味,但不反胃了,可能是肚子空空,也没什么可反的。
王二提醒道:“陈留王与太子亲近,王爷需提防。”
徐靖未搂紧我,苦涩地道:“西门,你怎么就这么命苦?”
我胡乱地说了句:“放我回去吧!”
徐靖未忽然改了语气道:“女人,别给我装死!”
他抱着我疾速前行。正午的阳光直射,我觉着很热,我知道我在发烧。不知头脑清醒还是糊涂,我从怀中颤巍巍取出簪子,贴在面颊上。徐靖未没有阻止。等他不注意了,我用簪子刺破了自己的手,我需要一点痛,驱逐沉困的睡意。即便没有武力,我也不想再成为昏睡者,什么都不知道。
徐靖未没有往陈留王的驻地去,陈留王却率着手下赶到了。双方人在山脚会师。陈留王的人都一色蓝裳,蓝裳们涌上前来,为首的一人朗声道:“王兄,我来迟了!”
徐靖未道:“不迟,来得正好!”
陈留王道:“我南越脚下,岂容大杲武夫猖獗?王兄,我已派了五千精兵围堵了这片群山,你放心吧!”
徐靖未止步道:“如此甚好,有劳罡风开道,护我回王都。”
陈留王徐罡风亲自牵马走来,蓝裳军士们原地不动。徐靖未这才走向他,将我先横放马上。
“这个女子就是西门?”
我看不清陈留王的面容,只小心握着簪子,不叫人发现我手上伤痕。
“是啊。”徐靖未答。另有几位蓝裳军士牵马而来,王二等人也纷纷上马。
徐靖未与徐罡风寒暄完毕,翻身上马,说时迟那时快,徐罡风翻腕亮出匕首,一刀扎向徐靖未后心。徐靖未也好生了得,急转矮身,躲过了要害,匕首刺入了他肩胛。
“陈留王!”徐靖未落地后怒吼。王二一巴掌拍飞身旁阻他的蓝裳军士,飞身蹿来。我的马受惊,竟在此时撒腿狂奔。我只听见徐罡风阴冷的声音,“靖王得意太多年了……”
我紧紧抓住马镫,身子佝偻在马鞍上。靖王和陈留王缠斗在一起,只有三名蓝裳军士追我,他们并非高手,高手都留在南越二王身旁。我在马上颠簸,惊诧地发现了马狂奔的原因,我手握的簪子无意中刺到了马腹。从无意到刻意,我再次戳了下马,狂奔去吧,我的命运在我自己手中。
马嘶鸣一声,跑得更快。蓝裳军士在马后怒喊,他们很吵,令我心烦。我再次刺了下自己的手,颠簸之中,力道猛了,鲜血流淌。疼痛感抵消了部分眩晕,但驱除不了浑身的烧热,汗流浃背地死死抓住能抓的一切,我勉强支撑在马上。与马奔跑速度相呼应的是头脑的飞速运转,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到此时可判断是一场政治阴谋。从最初花重所定的趁大杲西征,以我为饵扰乱大杲后方的计谋,到徐靖未提前的仓促行事,现在已转变成南越王室内部的纷争。
不知是花重还是西日昌一手导致了情况的变化,也难确定最后谁将得利,我只知我自己,这根导火索被过早点燃,烧到了南越。
被点燃、被焚烧的还有我的躯体,我觉着自己越来越烫,即便用簪子戳破肌肤,也难抵消极度的不适感。作孽的是我还要继续虐待身下的马,这也等同继续虐待我自己。它跑得越快,颠我就越厉害。蓝裳军士倒是离我越来越远,但不把他们全甩了,我停不下来。模糊的视野前方,山路已经变得开阔。
更烫了,恨不能撕破身上所有衣裳,人仿佛在滚油里煎熬,我觉着我浑身冒出泡来,泡再一个个膨胀,胀破。我终于忍不住呻吟,但出口的却是尖厉的啸声。我被自己骇住了,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落难中,我叫出口的声音却分明充满着决绝的气劲。头脑跟着明白过来,我的身体处于异常情况。难怪我能在马上支持那么久,气力却没有枯竭,难怪我在颠簸之中,却总能抓牢不掉下去,原先还以为自己的身法能凑合,现在才明白是我的修为回来了。
身子依然滚烫难受,但神智为之振奋。我运起体内的气劲,骨骼立时哗啦作响,仿佛被打破又重新拼凑,强大的内息同时带来毁灭感和重生感。我只得感叹:真是病态的身躯,病态的气劲。我的感叹还未消失,整个人身子突然猛地一抽,竟从马上腾飞,凌风而起,山风吹拂火烫的肌肤,煎熬和清爽并存,很痛苦也很畅快,很脆弱也很强大。我扭转身,来路已不见蓝裳军士,藏匿起气劲,我猱身掠上山野上一株乔木。
现在我有了选择,是只顾自己逃亡,尽快回到西日昌身旁,还是沿路返回,一探南越二王究竟。我的头脑没有发热,是发烫的,而我本来就是个胆子很野的女人,不趁修为恢复的时候做点什么,那是懦夫。
带着不适的汹涌重返的气劲,我悄然踏上了返程。我一边嘲讽着自己,有点力气就不安分,一边竭力释放感知,分辨山野里的动静。我的视线并不清楚,但视力的低弱,反而增强了感官的敏锐。我很快察觉了三名气馁的蓝裳军士,他们口中说着无法回去交差的话。我从三人身旁隐秘而过,他们的修为只有清元后期,而我已经无法确定,非正常情况下自己的武力。
我觉着自己真的成了头野兽,穿行潜进于杂草山树之间,时而像豹子,时而像鹰,而我的头脑狂热中带着野兽的执著。我想要知道靖王与陈留王火并的下场,更想知道究竟谁才是猎物,谁才是猎人。
前方传来了阵阵脚步声,我恰好前行到高低落差的山脚,挪身翻腕,我一手扣在一处山岩下,埋身于矮坡。这个位置很隐蔽,我藏好身形后不久,就听到了言语声。
“王兄真算怜香惜玉了。”徐罡风笑道,跟着我惊讶地听到徐靖未的声音,“我只是不想她死在这儿,死得那么早!”
徐罡风顿了顿,道:“这出苦肉戏但愿能骗过昌帝。昌帝托人送信于我,倒是打一手好算盘。”
我按住心头大惊,更小心隐匿气劲,当他们经过我上头,我克制住周身难受,屏息。
徐靖未叹了声,“连我都被你欺瞒过去了,这一刀你倒下得了手!”
徐罡风笑道:“若王兄躲不过这一刀,就不是我南越第一将军了!”
徐靖未不语,徐罡风问:“王兄现在打算去英雄救美……”一众人渐行渐远,我不敢放出气劲探听,我听到的已经够多。
他们走远后,我又待了片刻,然后才往山崖走。这时候我还去追南越人,就是傻瓜。得知二王的密谈后,我该知会西日昌去。徐靖未做了两手准备,我跑掉和我没能跑掉,他都准备了阴谋。
压抑着体内的难受,我走到徐靖未带我翻上的山壁前,风吹不散周身的灼热,百丈下的蛮申江则在诱惑我往下跳。
我展开衣袖,忽然感到身后疾速而来的高手气息。毫不迟疑,我纵身而跃。
“西门!不要!”徐靖未急呼。想来他与陈留王在寻我路上,碰到了那三名蓝裳军士。
我在空中微笑,迟了,靖王,那一刀你白受了。
衣裳张开,凌厉的风呼啸左右,我越坠越快,周身的煎熬仿似凝固,半空中,我错觉,我真的自由了。
没有争权夺利,没有仇恨阴谋,矛盾也凝聚在这一刻。没有了这些纷扰,也就离开了西日昌。
我扑通落入江水,冰凉立刻侵入肌肤,深入骨髓。浑身皮肤仿佛被万针刺千刀剐,灼热不复,疼痛取代一切感觉。我往江底沉去,江水推我东去。沉到半途,我咬牙划起,逆流往西。
我不知气劲何时会消失,它来得奇怪,不合常理,一旦消失,我就将葬身江底。我必须得尽快寻一个安身场所,但不是在这片水域的两岸。被秋凉的江水浸泡后,我的身体状况会更差。
我不信我会死在这里。幼年我没死在老贼手里,唐洲我曾想放弃,南屏我放开生死,怎么可能死在这里?我体内的气劲出奇的争气,游走周身百脉,支持我往西潜游。冰凉和灼热似相互抵消,我憋气往西。
我逐渐抛开那些争斗那些烦杂,再不纠结。我只是一个寻常人,我既不想要天下,也不想呼风唤雨。我恨,因我痛失家人,我怨,因我无力报仇。恨也好,怨也罢,我还是一个女人。有人一次次一日日,扣开我的心门,有人一回回一遍遍温暖我的身心,即便明知这人是个祸害,即便明知这人起心不良,但他却打动了我。
在我迷离的临危之际,是他在我耳畔絮絮不停地呼唤,在我失去修为形同废人的时候,是他一如既往地陪伴着我。如果他只是个寻常男人也就罢了,但他不是。皇宫里美女如云,他舍弃了三千粉黛,夜夜睡在一个不能用的我身边。
我从唐洲回到宫廷,但凡招惹我的后宫女子,都被他一一打发了,从孙文姝开始,一直到田乙乙。他分明清楚田乙乙不过是南越人的试探石,他还是为我剔除了。
我在蛮申江水底,突然发现我是多么思念他。曾以为自己堕落,陷于欲望的深渊,如今我却在另一种深渊里,思念黑暗又光亮的天地,那里开满绝美又血色的情花。
花开花落,花飞花逝,一曲无言,“永日无言”,跌宕起伏于身骨,无法遏制的颤抖一音音拔高。头脑似要崩溃,江底突然变色。
幽幽浑浑的江底,流动的江水穿身而过,这里不是情花满谷的天地,却染上了一层晕红。
气劲跟随暴涨的思绪激荡起来,我的身体再次滚烫,热血沸腾于四肢百脉,火辣辣的液体流出七窍。我心下明白,我流血了。我的身体早已透支,此刻更是超了负荷。竭力冷静镇定下来,忍耐着体内剧烈的翻涌,我继续西进。
思绪逐渐沉淀下来,我也想明白了自己身上的变化。我的血脉肌骨历经老贼二次重创,而变得脆弱易伤,无法支持气劲的正常运行,但我所修的乃世间绝学天一诀,被西日昌硬救回来所用的也是天一诀,多年的修行和外力的补救使我具备了改造气脉的条件。之所以之前一直察觉不到身上的气劲,是因为身体需要休眠需要蓄力,可被徐靖未一搅和,加之我自身的情绪变化,导致在身体提前异变。
或许这正合了我的武道,没有寻常路径没有徐图缓进,只有急变突化。
我小心地控制情绪,尽力适应身体的变化。热血爆出七窍后,似又达到一个平衡度,周游叫嚣在体内,仿佛无数把钝刀刮骨削肉,闷痛之极,却还能勉强忍受。
不知在江底潜行了多少时候,当我浮上水面,换了浊气,却骇然地发现江面上正漂浮几十具死尸。看这些尸体的衣着装扮,不少是徐靖未那条船上的南越人。
极目远望,午后的充足日光下,南越船在前方却灰影惨淡。我悄然靠近,越近越觉船上异常,搏杀还未终止。
我潜水底贴近船舷,搭手船身,才露出头来,身旁就扑通一声,又一具尸体。
“对敌人手下留情,就是找死。”一人冷冷道。
“还是王大人厉害!”一人奉承道,“若非王大人及时赶来,我们这些人就都得交代在这里了!”
我轻手轻脚爬上船,但身上的水滴落船板,被那王大人察觉。
“谁在那里?”
我摸出簪子,却不是绾湿发,而是拨得更乱。船舱被王大人以气劲破壁,我身子一晃,他的气劲固然强,但还未达到伤我的地步。
我看清了舱内人,他们也看到了我,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小猪!终于找到你了!”
我一愣,我都披头散发,狼狈不堪了,苏堂竹竟还能认得!
南越人见苏堂竹有了援手,不容我接近他,已抢先动手,围攻于他。我心下大怒,先前王大人那句话显然是嘲讽苏堂竹出手不够犀利,这会子我来了,他们却柿子挑软的捏,先除心善手软的。
“趴下!”我喝道,苏堂竹不会办利落的事,我来。
逼人的气劲瞬间散发,王大人跟着大喊一声:“不好!”压着他声,我双指夹着簪子,手印气场覆盖下来。苏堂竹拉着左右趴倒,几个机灵的南越人也趴下了。螺旋气场充满船舱,王大人飞身退出船舱,等他站稳脚跟,眼前已是一片惨景。
血肉横飞,断肢片片,舱内到处都滚落着血块。以天一诀的气场,林季真尚不能挡,何况这些人?
王大人惊骇地招呼剩余的南越人溃逃,我没有追击。我体内的状况他们不知道,若知道,南越人岂会逃跑!我不能连续施展气劲,只怕用多了,我就真的毁了。
“小猪……”苏堂竹和他的人都伏在地上,面色苍白地望我。
“我又杀人了。”我轻叹一声,因气劲鼓飞的衣袖回落。
观望那位王大人离去的身法,我断定他的修为与王二接近,幸而他被我手印强横凶残的杀戮方式惊退。他若留下,我与苏堂竹等人就完了。
苏堂竹与身旁的侍卫相扶而起,我竭力克制体内剧痛,转面望他,问:“陛下呢?你怎么来了?”
苏堂竹三言两语道明了情况,此刻西日昌下令上官飞鸿率军边境,与南越水军在蛮申江水域中段展开激战。西日昌料准徐靖未弃船,命苏堂竹收船历练,不想南越人没有抛弃这船,遣了那位王姓高人来救。苏堂竹心肠本就柔弱,太医又做得太久,不会杀人只会救人。王大人未到,苏堂竹带领的侍卫大败船上的南越人,而王大人一来,局势就逆转。若非我阴差阳错地抵达,苏堂竹险矣。
侍卫们简单地清理了船舱,将尸体扫落江水,江水顿时染红。我去另一舱看了看左荃珠,她安详地沉睡,面容虽惨白,却说不出的优美。
“她到底是谁?”我问。
苏堂竹沉声道:“她就是左荃珠,真正的左荃珠。当日师兄找到了她,把那个南越李代桃僵的杀了。”
我觉得胸口更难受了。冒名顶替的却是自己,这讽刺太大!
“小猪,你怎么啦?”我的情况终究瞒不过医师。苏堂竹抓住我的手腕,我颤了下,没有甩开他。
苏堂竹一搭我脉搏,立时面色大变,高喊道:“全速前进,尽快抵达黄围渡口。”
“陛下那里情况如何?”
苏堂竹眸色一沉,厉声道:“师兄那儿你不用操心,你先给我躺下!”
我挣脱他的手,沉声道:“靖王和陈留王并没有内讧,他知道吗?”
苏堂竹不理我,再次抓住我的手腕,拖我到另一船舱,按我躺下。
“我死不了!”
苏堂竹幽怨地道:“早知道你的情况,我死也不要你出手……”
我躺下后就觉得疲累,习惯性地又摸簪子,被苏堂竹夺去。他收了我的簪子后破口大骂道:“混蛋!笨蛋!傻瓜……”
我只是担心一睡着,就会睡很久。
苏堂竹忽然骂不下去,他垂下头去,无奈地坐于我身旁。
“师兄不会有事,他从不轻易信人。”苏堂竹低低地道,“你也不用担心我,你这样子,我就算再心慈手软,也不会不顾忌你。师兄说得对,我再这样下去,只会累人害己。”
我应了声,沉困的睡意阵阵袭来。
等我醒来,已是入夜,苏堂竹早在旁等候,递上温热的米粥。大杲太医的手艺比南越厨子精湛得多,光看成色,闻着香味,我就胃口大开。但我伸出手,却见一双手已被包扎,从指尖到手腕,包得纹丝不露
“我来吧!”
苏堂竹一手扶起我,一手拿勺喂我。我觉着不自在,越来越不自在。我暗运体内气劲,血脉似温和下来,被我一运又迅速流动起来。
“不能乱来!”苏堂竹正色道,“我趁你睡着,施过几针。你这状况,绝不能再动武力,不然轻者废了修为,重者性命不保。”
我点头,苏堂竹仔细地喂我用粥,我又发觉不自在的还有头面。头发被梳理了,西日昌的簪子插在了发间,脸面干爽,显然也被清洗了,甚至身上的衣裳都被换了。此刻这船上除我以外没有女子,必然是苏堂竹亲手换的。我纵然是个再豁达的女子,被他如此对待,也很尴尬。想起当年苏堂竹为我解落霞丸之毒,难言的情愫幽然而生。
苏堂竹放下空碗,对我细声道:“小猪,我也只能在师兄不在的时候,这样叫叫你。你听我一句,等这次回了盛京后,你旁的什么都不要管,一心养伤,伤好之后也不要再弹琵琶。师兄经过此事,已全面铲除了南越在大杲的隐患,会把你护得更紧。以后的事,包括西秦国师,你都不要管了。”
我没有应声。
苏堂竹又开始唠叨,苦口婆心的言语,只为劝我放下武者的身份,抛开仇恨的包袱。我知他为我好,也就默然听了。
平凡人过寻常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平淡的幸福,浓郁的无法持久。太苦了承受不住,令人疯狂,太甜了就腻,腻了就成桎梏。有点苦有点甜,更多的是平淡,才能维系日复一日的朝起暮归。
我也想过寻常的日子,但时不待我。和一位君王过寻常的百姓夫妻生活,简直是痴心妄想。
我下地,整整身上的衣裳,打断了他的话,“小竹,前方有状况。”
苏堂竹一怔,他的修为比我差了两阶,没有感知到前方水域的动静,但他却百分百信任我,当即他下令,所有侍卫警戒。
“你知道左姑娘死前说了什么吗?”我平静地道,“她说世间最美的地方是大杲。”
苏堂竹嘴唇翕动,却说不上话来。我径自走出船舱,他连忙跟出。
“为了守护心中的最美,她付出了一切。陛下虽然有诸多不是,可我相信,由他统治的国度将维持长久的和平和富饶。”我忽然笑了下,“你不战,总有人要战,你不杀,总有人在杀。温和的止杀,只是姑息,这是我为陛下找的借口。但每一次朝代更迭,都是一样的,都要死很多人,都要血流成河。顺应时机,好的取代差的,更好的取代好的,腐朽的被推翻,不合百姓民生的都会消亡。”
我走到甲板上,夜风中我切实地感到了自己。我不再被风穿身,仿似假人,而是真实存在,我活着,为一个男人,和他的理想并存。尽管这个理想注定血腥,充满残酷的杀戮,但我已彻底释怀。
“如果有一日我瞎了一只眼,剩余的一只不剜除将殃及性命,我的选择就是做一个瞎子继续活下去。”
苏堂竹道:“不要再说这样的话,我明白的。”
冷冷的夜风吹送,这会苏堂竹也感知了前方有船只迎面而来。我又上前一步,立于船尖上。苏堂竹马上拉住我的衣袖,提高声道:“你不准去!”
跟着,船上几乎所有侍卫都跪了下来,打头的一个道:“大人,你不可再涉险。”
我愣了愣,随即明了,在我沉睡的时候,苏堂竹必然和他们道了我的身份。片刻后,我沉吟道:“看看。”
苏堂竹改换抱住我腿,我微微一笑,道:“你还想被陛下揍吗?我只想看看,站得高看得远,我不过去。”
苏堂竹松了手,瞬间,我整个人荡了出去。
“小猪!”
我头也不回往前,口上道:“其实,我也是骗子。”
苏堂竹追来,身法却没我快。他既追来,我也没有甩开他,我们保持距离一前一后在江面上穿行了百余丈。江水急流的波涛中,出现了船只,不是一艘而是一支船队。每一艘船的船杆上悬挂的旗帜在夜色中显目,玄色底纹,一轮红日之中,一道白色悬穿。红日白泪,这是西日皇族的族徽。
我一怔,身子低落,连忙拔身而起,双足已湿。身后苏堂竹喜道:“师兄亲自来接我们了!” 妃子血(全二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