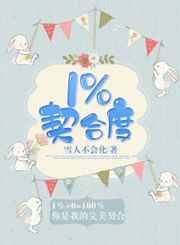房间里开着几盏巨大的白色吊灯,把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通透,而小少爷蜷缩其中,渺如沧粟。
外面的挂墙玻璃其实是一块巨大的影像墙,里面安满了密密麻麻的针孔摄像头。
连着的另一边,穿着一丝不苟白大褂的医护人员和科研博士们看着珍贵高级的Omega,相互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赶紧停止注射抑制剂吧,我怕他的腺体经受不住会坏掉!”
另一方赶紧驳回:“绝不可以!他的新生腺体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不注射抑制剂只会流窜的更加厉害,彻底扼杀掉他稀罕的西番莲信息素。”
“那也要给他喝口水吃口饭吧,他已经三天滴水未进,滴米未沾”,一个年轻的女Beta看了看屏幕里脸色几近透明的漂亮Omega,“就怕撑不到手术那天,人就没了……”
大家一时间默契的闭嘴,终于,人群里有人道:“腺体肿胀太厉害,简单的咀嚼功能怕会导致它猝然破裂,挂营养针吧。”
于是,第二天,全身上下消了毒包裹的只剩两只眼睛的护士踏进了病房。
彼时,施木然正抬起沉重的眼皮去努力的看着大门外,可惜灯光太刺眼,他只能先看到一片苍白,接着就是过度光照的麻点和眩晕。
他张开嘴,每一个音节自喉咙口喑哑断续的发出:“是,是……谁?”
来人被他破碎的声音惊了一跳:“护士,过来给你输营养液。”
面无血丝的施木然眸子暗淡了下去:“哦。”
然而营养液并不能每天都输,因为考虑他身体的排泄机能在下降,旁人和他都不能随意进出无菌仓,只要人不死的情况下,他们就吊着他的一口气。
护士去给他输营养液时,施木然都会有短暂的清醒,声音飘渺的似乎要立刻断气:“是,是谁?”
每一次护士都耐心的回答:“是我。”
可是慢慢的,医生又开始往他体内注射新的激素药物,以克制他的新生腺体。在药物的作用下,他的意识也变得更加混沌。
护士再过来的时候,他的声音更加虚弱:“商……柏?”
护士惊讶,商柏是谁?
她回答:“陆少爷,我不是。”
接着,他看到床上瘦小的Omega蜷缩成一小团,肩膀剧烈的颤抖起来,丝毫不顾后颈上撕裂的钝疼和半个月没进主食的孱弱身体,痛苦的呜咽了起来:“商柏……”
“呜呜呜……我要回家。”
“我要……商柏……”
他的声音太悲恸,如同钝刀划在玻璃上,沉重撕裂,终于,小护士不忍再说实话。
后来,施木然再问她时,她就骗他:“嗯,是我。”
可惜那时的施木然再也没有半丝的力气去探讨来人究竟是谁。
半个月后,医师们开始给他打能激发出发热期的药剂,施木然从来没有经历过发热期,初期时并没有太多感受。
可是三天后,药物在体内发酵,开始正式发挥作用。
施木然的后颈像被火烧了一样灼痛,整个人就像被暴晒在沙滩里缺水的死鱼,等待潮汐时回归海洋。
他呼吸微弱,脸色白如枯槁,仿佛一碰即碎的完美瓷器,抱紧双臂,缩成一小团,耳朵里听不到任何声音,喉咙生涩的灌了铅块一样,吐不出任何干巴的字眼。
他抽搐着,面色疲惫着,俨然半截身子都要入土。
而他的父亲陆其宗也终于在术前的第三天透过玻璃窗户过来看他。
施木然伸出细的青筋爆出的手,喉咙里发出嘶哑不成腔调的呜咽。
“我……”要出去。
“我……”要回家。
“我……”要……商柏……
可是没有人能听懂他的诉求,只听到他嗓子眼里轰轰隆隆,喉管断裂一般的声音。
又或者就算有人听懂了,也不会搭理他。
手术依然进行着。
陆其宗转身对身边人道:“给他加三倍的药量,手术三天后正常开始。”
身边的医师脸色一变,小心翼翼回答:“可是,议长大人,这样他――”
陆其宗回头,脸上是不容冒犯的肃穆神色:“会死,还是会残?”
“都……都有可能。”
陆其宗继续不带任何感情的冷冽吩咐:“那就加,只要人不死。”
不死,只要不死,会伤会残都不当紧。
而接下来的三天就是施木然一辈子的噩梦。
医生换了十几厘米长的粗大针管,在他陷入睡眠之时,刺进了他的经管。
施木然从睡梦中猛然惊醒,喉咙口发出沉闷的低吼,医生按住他的脑袋:“别乱动,陆少爷,还没注射好。”
施木然心里陡然生寒,浑身血液倒流,巨大的恐惧和疼痛让他出于本能开始反抗。
也可能是撕心裂肺的痛苦唤醒了他身体的潜能,他居然还有力气从床上滚下。
骨头砸在地板上时,似乎完全碎裂开来,他也不顾,凭着强烈的求生欲望一厘厘,一毫毫,狼狈不堪,拼劲全力的爬向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