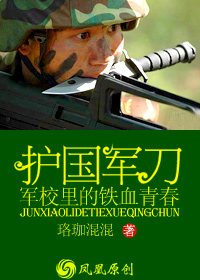[第14章从头再来,燕子在一个冬天飞走了]
第1节并列机枪分解结合
昨天所有的荣誉,
已变成遥远的回忆。
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
今夜重又走入风雨。
我不能随波浮沉,
为了我致爱的亲人。
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只为那些期待眼神。
心若在梦就在,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
看成败人生豪迈,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摘自《从头再来》
送走了刘恒,我们来不及思考,甚至连抒发下伤感情怀的时间都没有,因为造孽的日子,再一次降临!
而既然选择留下,那就证明已经做好继续受虐的准备!
不得不承认,在指挥专业方面,坦克学院在装甲兵院校中具有绝对的教学优势,以及无可匹敌的霸主地位。
绝大部分上了年纪的教员,都参加过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以及后来近十年的防御作战,属于那种经历过战火硝烟,看到过流血牺牲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坦克的使用以及坦克兵战术有着极为深刻的体会,那种历经生死的体验,炉火纯青。
这帮老教员脾气乖戾、性格暴躁,平时呢,都大大咧咧的,高兴了骂娘,不高兴了还是骂娘。但只要上了坦克,脸就一直绷着,对我们每一个动作的要求都一丝不苟,稍微出点差错,那肯定就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问候下母亲算是轻的,有时候连祖宗十八代都不放过。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那么极少部分情况,骂着骂着,这帮老头子自己却流下了眼泪,跟孩子一样。
最初,学的是单坦克射击,主炮、并列机枪、高射机枪、航向机枪的构造、原理、操作,从理论到实践,从使用、校正到维修,林林种种的,反正都得学。
理论课简单,无非是听听、记记、背背。
实践第一个科目,是某型坦克7.62毫米并列机枪的分解结合。
第一次课,我们到的时候,教员早就到了,是矮墩墩的,很壮实的一个半老头,皮肤黝黑。
我偷偷瞄了一眼,讲台上放着一堆药棉、酒精、纱布,还有创可贴,要不是每人面前的课桌上都摆着一挺乌黑发亮的并列机枪,我还以为这是要上战伤救护课呢。
课上,教员结合课件、挂图及实物,介绍了7.62毫米并列机枪的基本构造原理,边讲解边示范了一次分解结合,然后就让我们开练了,而且声明接下来的7天下午,全是这个科目。
不过,教员说了,我们之中要是有人觉得练得可以了,欢迎找他PK,只要能赢他的,以后的课就都不用来了,爱去哪玩去哪玩,而且保证成绩评定给优秀。
说完,这厮居然还非常挑衅地看了我们一眼。
告诉各位,以后但凡有人对你放出这种话,千万小心点,只要脑子还没坏掉的,敢说这样话的,要么就是兜里有几两米的,要么就是手上有几趟活的,要么就是背后有几个人的,切记啊。
但当时我的真实想法是,奶奶个腿,不就拆个枪、再装个枪嘛,能有多难,还真就不信弄不过你了,而且我敢发誓当时抱这种想法的哥们绝对不在少数。
哎,年少气盛,冲动是魔鬼啊!
闲言碎语不要讲,正式开练,卡笋前推,打开受弹机盖,掀起受弹机座,取出取弹机,然后是复进簧、扳机装置、枪机框、装填拉柄以及拨弹板、防尘盖,最后,将压固定栓卡笋并向左拉到底,握住枪管提把,从机匣内取出枪管,最后再照相反顺序装上。
反正是拆了装、装了拆,一直练,不停练,各种练。教室里,一片机械碰撞的声音,嘁哩喀喳,噼里啪啦……
老教员找把椅子,往讲台旁边一坐,抱着个超级大的、茶垢超级厚的茶缸喝茶,笑嘻嘻的,却并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走下讲台,巡视一圈看一看,顺便指导指导。
应该说,我们还是沉得住气的,练了整整一下午,没有人提和教员PK的事。快下课的时候,许诺问我怎么样了,我冲他笑笑,自信满满地说:“九阳神功第十重!”
“何解?”
“已经超越第九重了呗!”
“彼此彼此,我的一阳指也差不多了!”
“那明天还来不来?”
“不想来,上吧?”
“一起上!”
于是,我们举手打了报告,被一起煽动起来的,还有十几位同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哥们。
讲台上,教员收敛了笑容,放下那个超大号的茶缸,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块黑布,把自己的眼睛给蒙上了,边蒙边说:“你们练的时间毕竟短,别说我欺负你们!”
随着一声开始的口令,我们立即着手开始分解枪支,总体还算比较顺利,特别是许诺,动作那是相当的潇洒飘逸啊,帅!
然而,怪事发生了,就在我取下防尘盖的那一刻,听到讲台上的教员喊了一声“好”,随即扣动扳机,完成了击发!
我们十几个人都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因为已经没有意义了。
抬头望去,看到老教员已经解下了蒙眼的黑布,静静地望着我们,而一挺已经结合完毕的并列机枪静静地躺在讲台上。
好吧,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就好比温州的动车事故,官方已经宣布不再有任何生命迹象了,结果小伊伊不还是被救出来了?
无法相信,却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只能用奇迹去解释!
虎子并没有参与此次PK,因此他看到了教员的全部表演。那次,我看到张大嘴巴的虎子,眼睛里满是崇拜,用虎子自己的话说,那就是太漂亮了,炉火纯青、行云流水,完全是一种艺术的欣赏。
说实话,很难得从虎子嘴里听到这种文绉绉的话,特别不习惯,顿时,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望着我们不解的眼神,老教员面色渐渐凝重起来,低头默默收拾起那些药棉、酒精、创可贴,许久,才抬起头,却已是眼睛通红。
“同学们,拆个枪,再装上,确实不难!可是,战场抢的是时间,每一秒钟,都要拿战友的性命去换。”老教员的声音哽咽了,一颗浑浊的泪珠滚出了眼眶,接着说:“就在25年前,有一个坦克兵,学艺不精呐,着急忙慌地排除完故障,装枪却还是慢了一步,结果成群结队的越南鬼子摸了上来,一颗火箭弹随即击穿了侧翼装甲,一车人呐,就活了他一个。”
我们都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再后来,他倒是过得挺滋润,提了干、结了婚、有了儿子,却老是梦见过去,梦见那几个满身鲜血、支离破碎的战友,真的对不起他们呐,如果他们还活着,儿子大概也有你们这么大了吧……”
教员提着包走了,我们却坐在那愣了很久。
虽然教员没有明说,但我们猜得出来,故事里的那个背时的坦克兵肯定就是他本人,否则,他不会如此地泪流满面。
那以后的6次课,我们不再抱怨,更不敢懈怠,偶尔有人发两句牢骚,也会马上被同学鄙视的眼神堵上嘴。大家默默地练习着,先睁着眼练,再蒙着眼练,先各顾各练,再相互比着练,边练边谈谈体会,交流交流经验。
偶尔,也撺掇着教员再示范一次,仔细观察,想着找找教员拆装的窍门,偷学点技术,但却从未发现过。
机枪毕竟是钢铁的,磕了、碰了、划道口子什么的,都很正常,弄伤了就自己到讲台上拿药棉蘸着酒精擦一擦,贴上创可贴,口子大的拿纱布包一包,继续练。
等到那堆药棉、酒精、纱布、创可贴都消耗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也算是出师了,虽然速度还是拼不过老教员,但达到《军事训练大纲》的优秀标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事后,许诺总结了一句话:“无它,唯手熟尔!”
我们不是“卖油翁”,但道理显然是一样的。
因此,我觉得,许诺是对的!